相信未來,老有所依
陳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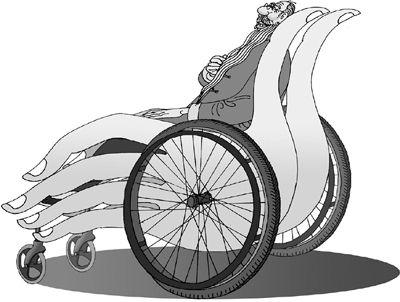
泰戈爾說:“生如夏花般絢爛,死如秋葉般靜美。”然而,死亡在中國是個沉重的話題。要達到靜美,必須在生命的最后一程走得輕盈安寧。
中國早在1999年就已進入老齡化社會,目前60歲以上老年人占總人口的12.5%,占全球老年人口總量的1/5。中國社科院指出:2011年以后的30年里,中國人口老齡化將呈現加速發展的態勢;到2030年,中國65歲以上人口占比將超過日本。這對中國的社會保障體系將是嚴峻的考驗。
誰都不會永遠年輕,都會迎來人生的落幕——夕陽落下后是璀璨的星空還是無邊的黑暗,都在于今日的建設和創想。
“空巢”之痛
2010年年初有條驚悚新聞:廣東省中山市某小區的物業公司強行打開了一戶業主的房門討要說法,因為年邁的業主欠繳7年的物業管理費,一直無法聯系上。門開了,一副完整的白骨赫然呈現,驚嚇眾人。因物業公司沒有老人子嗣的聯系方式,新聞無法后續。
另一位河南老人王桂華(化名),3個子女都事業有成,給她在老家蓋了大樓房,請了貼身保姆,但逢年過節都不回家。老人病危之際,子女遲遲不歸。臨終時老人淚流不止,一旁的保姆都心酸長嘆。
老人寂寞離世的例子并不鮮見。民政部及中國老齡委的數據顯示,中國城市老年家庭的空巢率已增至49.7%。這意味著:100個城市家庭中,就有近50個家庭的老人守著孤燈,盼望親人“常回家看看”。
孤獨啃噬生命。經濟發展,城市化大潮帶來了人口流動,年輕人或出國,或打工,而老人們據守原地,情感缺失,只能想盡辦法“抵抗孤獨”。
“家里有只蚊子我都舍不得打死,因為除了我,家里就它是活的了。”
“我88歲征婚,要求不高,就想和對方通個電話,說說話。”
“我每天都在樓下的公交站等車,坐上整整一圈再回來,感受一下人氣。”
……
獨生子女政策下的“4-2-1”小型家庭(即一對年輕夫婦要照撫4位老人和一個小孩),使“80后”一代力所不及,也導致空巢老人激增。
中國農村家庭的空巢率已達38%。生活難以自理的農村老人,有些甚至選擇在柴房、山洞、荒坡或樹林悄然結束生命。加拿大人費立鵬研究中國自殺問題已經10余年,他表示,“農村老人自殺率高于城市老人5倍”。
究竟為什么要小孩
從北京等大城市到小村落,耶魯大學陳志武教授曾向無數中國家庭詢問這個問題。源自“愛”的,北京市有61.8%,農村只有20.5%。很多農村孩子的誕生是為了滿足“養兒防老”和“傳宗接代”的需求。陳教授認為,金融服務水平在中國城鄉發展很不均衡,當社會保障體系很不完善時,老百姓沒有辦法浪漫,只有“養兒防老”。
改變無法避免。中國傳統的“居家式養老”富含親情味,卻因“空巢”時代而變成“無情可依”。儒家文化提倡“孝道”,卻不能保證“孝道”。不孝子女常有,也都是父母含辛茹苦養大的。
如今,“居家式養老”功能日益下降,中國迫切需要完善的人性化養老服務供給機構,從“養兒防老”過渡到國家、社會、家庭多方養老,給老人更多的選擇、保障、溫暖和尊嚴。
偏見和傲慢
不少人仍會懷著偏見抵制養老院。除開生活習慣、經濟因素等等,還有傳統觀念的禁錮。有位剛退休的大爺說:“你們這一代進養老院是正常的,而我們子孫一大群卻被送進來,寒心!”還有位離異的單親媽媽,工作繁忙,實在無力照顧半身不遂的母親,在眾人的勸說下把老人送到養老院,她哽咽難言:“我實在不孝,但沒有辦法。等狀況好轉,馬上把您接回來!”
一面是傳統老人的“偏見”,另一面則是養老市場的“傲慢”。
據調查,中國老人仍然首選居家養老,只有5%的老人有入住養老機構的愿望。即使只有5%,對應的養老床位缺口仍然有百萬之巨。民政部公布:截至2009年年底,全國有各類老年福利機構38060個,除了以社區為依托的托老所、家庭式養老院,還有公立或私立性質的普通養老院、高檔老年公寓等等,床位共266.2萬張。65歲以上的老人每1000人擁有的床位數是23.5張,而發達國家的這個比例在50~70張。
公立養老院常常一床難求。居住在北京宣武區的楊紅老人,已經向附近的一家養老機構提出申請3個月了,仍然無法入住。“只能走一個,進一個。”廣州的養老院也是供不應求,在中心城區,即使收費高昂,老人們也得排隊等待。
硬件缺,軟件更缺。優秀的專業護理人員往往有傳奇般的經歷。
79歲的臺灣老人黎秋林2010年7月在臺北過世。老人臨終前立下遺囑,將折合人民幣175萬元的現金,作為遺產贈送給廣州某醫院的女護工何英(化名)。這位孤寡老人來大陸旅游時突發急病,住進了這家醫院,得到了何英無微不至的照顧,老人回臺北后仍然感念不盡。39歲的何英因此改變了命運。
此外,發達國家用不同的保險金融產品,如人壽年金、養老基金等,來替代人格化的養老,讓老人有了更多保障。中國社會養老保險的制度及模式仍在探索、發展中。
從“社會統籌”“社會統籌和個人賬戶相結合”到“社會統籌和個人賬戶分立”,中國養老保險制度已經經歷了3個階段。據中國養老金網報道:“由于養老保險制度的變遷以及各級政府長期的挪用,本來是參保人個人財產的個人賬戶,有90%以上的資金長期處于‘空賬運行的狀態。就連全國實施養老保險個人賬戶做試點的13個省,‘空賬規模亦已達1.6萬億元。”
1.6萬億元,讓人嘩然。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烏日圖表示,必須盡快解決“空賬”的歷史拖欠問題,通過改革和不斷完善,逐步做實個人賬戶。同時,加快提高社會養老保險的統籌層次,社會保險基金才能更好地統籌互濟。可惜,目前真正實現養老保險省級統籌的省市屈指可數。
我們都會變成“老小孩”
英國記者馬丁·佩興斯的文章《中國感受老齡化之痛》中提到:“人們根本不愿意談論如何照顧那些即將告別人世的老人,因為他們認為這會帶來壞運氣。在這個國家,大多數人甚至不寫遺囑,因為寫遺囑也被看做是朝死亡之門近了一步。”
中國被看做是一個忌諱談論“死”的國度,我們無須辯駁,而應該在各種聲音中加速成長。不管是傳統的“居家式養老”,市場經濟下催生的養老院,還是不斷完善的養老保險制度,都需要人與人之間最溫暖的關懷和愛。
不能不提北京的松堂關懷醫院,這是中國成立的第一所臨終關懷醫院,致力于“讓死亡也變得有尊嚴”。院長李偉(又名“李松堂”)是松堂醫院的創辦人。第一個病人是他的鄰居,乳腺癌晚期,每天接受化療,痛苦不堪,病者的家庭因此趨于崩潰。李偉勸她愛人:“她特別需要心理關懷,送到我們那里去吧。”4個月后她走了,嘴角帶著微笑,這讓李偉覺得釋然。
至今中國已有臨終關懷機構百余家,但與美國2000余家的數字相差甚遠。
“每天擁抱死亡,我的生命質量很高。”李偉謳歌靜謐、美好的離去,然而有如此豁達胸懷者,世間寥寥。關懷醫院的發展遇到了無數困難,搬家就搬了7次。護工們曾被社區的群眾堵在車里面,不讓放下病人,因為那些人覺得每天社區都要“死人”,太晦氣。也遇到很多好人,比如一位的哥聽到車上護士在哭,義憤填膺,義務幫著醫院搬家,一趟又一趟,搬完就悄悄走了。
李偉說:“到現在我也不知道這個好心司機的名字,但我在心里面會記他一輩子,這些老人會記他一輩子。”
通過20多年對萬名臨終病人的調研總結,松堂關懷醫院發現:人類的臨終期并非約定俗成的6個月,而是10個月,約280天。一個生命在媽媽的子宮里被呵護、關懷,從而誕生;當他老了時,發白齒搖,就變成了“老小孩”,同樣需要呵護和關懷。
“他不能再回到媽媽的子宮里,他需要和諧的社會營造出社會的子宮。在這個‘子宮里,在醫護人員的幫助下,他減輕了肉體上的痛苦;在心理醫生的關懷下,他消除了恐懼和遺憾——在這樣的氛圍里,生命完成最后的成長。”接受魯豫的采訪時,李偉這樣說。
葉芝有一首詩《當你老了》:“當你老了,頭白了,睡意昏沉,爐火旁打盹,請取下這部詩歌……”這般溫柔的愛意,贈與父母,也給予終將白發的我們。
相信未來,老有所依。
(黎 青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