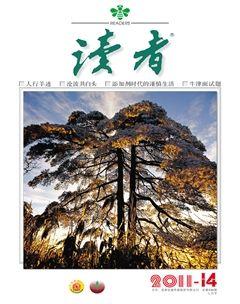沙漠里的水手
姜欽峰
一
鄱陽湖素有“候鳥天堂”的美譽,每年秋后,會有大批候鳥來這里越冬。為了心中的天堂,它們成群結隊,晝夜兼程,依靠太陽和星辰辨別方向,不遠萬里而來。不法盜獵分子卻架起“天網”,“歡迎”這些遠方的客人,把天堂變成地獄。假如沒有這些陽光下的罪惡,也許黃先銀仍可以過普通人的生活,每天看著大雁從頭頂飛過。
黃先銀的家在南昌市郊,緊鄰鄱陽湖大堤。這個黑黑瘦瘦,年逾不惑的莊稼漢子,從小對鳥兒有著特殊感情。只要鳥兒從頭頂飛過,他不用抬頭,光聽叫聲,就知道是什么鳥。然而,不知從何時起,湖區沼澤地豎起了一張張“天網”,有的綿延達數十公里,讓他觸目驚心。
一只天鵝在黑市上能賣到數千元,在暴利驅使下,一些不法分子不惜鋌而走險。每年冬季來臨之前,他們先用船把大網和竹竿運到鄱陽湖腹地,在空中架起“天網”,待枯水期來臨,再去網上摘取獵物。每年冬季,天還沒亮,黃先銀就會被轟鳴的馬達聲吵醒,成群結隊的摩托車,從他家門口呼嘯而過,那是去湖區盜獵候鳥的隊伍。他的心在滴血,卻感到無能為力。
幾年前,一個偶然的機會,黃先銀在湖區救下兩只被困的白鸛。送到野生動物保護站時,白鸛已奄奄一息,由于傷勢過重,最終死去。他親眼目睹,一只白鸛在臨死之前,兩滴眼淚從眼角滑落,順著嘴巴流淌下來,然后閉上了眼睛。這一幕在腦海中始終揮之不去,他說:“我看到鳥兒在哭泣!”從此,他走上了義務護鳥之路,拆毀天網,解救候鳥。一個人的力量有限,他又開始向主管部門和媒體舉報,呼吁社會力量保護候鳥。他的呼聲受到越來越多人關注,猖狂的盜獵分子不得不有所收斂。
臺灣一位名嘴說過一句話:“我這一輩子罵人無數,得罪人無數,卻從未遭到報復,因為我從來不斷別人的財路。”黃先銀的舉動,恰恰是在斷別人的財路,因此遭到瘋狂報復。他原來以養鴨為生,一夜之間,2000只鴨子忽然全部丟失,就連田里的水稻也被人鏟平。有時,他獨自進入湖區巡查,會莫名其妙遭人毆打。平靜的生活被打亂,威脅和恐嚇,反而讓這個倔強的漢子橫下一條心,發誓要跟他們斗到底。
這些年,為了保護候鳥,黃先銀四面樹敵,在村子里幾乎沒法立足。記者去黃先銀家采訪,發現他家的房子已經空了兩年沒人住,妻子走了,兒子交給了年邁的父母撫養。他幾乎眾叛親離,鄰居對他避而遠之,老母親罵他不務正業,自作自受。記者問他為什么要保護候鳥,他似乎講不出太多大道理,只是反復地說:“它是一條命,我們也是一條命。”為了鳥兒的命,他可以不要自己的命,難怪別人都當他是“精神病”。
媒體上有許多關于黃先銀的報道,他被譽為“孤膽英雄”“鄱陽湖斗士”。然而,在附近的多數村民眼里,他卻是個不可理喻的另類分子。身邊的熟人這么評價他:“他這個人就是一根筋,扳不過來,我們做事是為了生活,他做事是為了不生活。”“小家都顧不好,還考慮大家,要是我們都像他那樣,一家子早就完蛋了。”“人做事總得圖點什么,我想不通,他到底圖個啥?”許多人想不明白,他做這些到底為了什么。
二
張正祥被譽為“滇池衛士”,曾是“2009年度感動中國人物”獲獎者,當地人送他外號“張瘋子”。滇池位于云南昆明西山腳下,數十年來,為滇池和西山不遭受污染破壞,他四處奔走呼告,先后告倒160多家排污企業,40多家采石場。而他得到的回報,卻是終身殘疾,妻離子散。
對于大自然,他有著超乎常人的親近感。1948年出生于滇池邊的張正祥,童年接連遭遇不幸,7歲就成了孤兒。沒媽的孩子像根草,村子里的孩子都欺負他,一氣之下,他躲進了深山老林,過了7年野人般的生活。餓了吃野果,渴了喝山泉,困了就住在溶洞里,他一個人在山上過得逍遙自在,快樂無比。這成為他童年最美好的記憶,也讓他對這片青山綠水產生了母親般的依戀。
上世紀80年代,西山豐富的礦產資源吸引了大批人前來開山采礦。一時間,炮聲隆隆,塵土飛揚。正當人們為找到致富新路而歡欣鼓舞時,張正祥卻站出來反對,認為這樣無序開采會破壞山體,污染滇池。然而,他微弱的聲音很快淹沒在轟鳴的機器聲中,根本沒人理睬。換成別人,盡力而為也就算了,他不。從此,孤身一人,開始了長達數十年的戰斗。動機很簡單,用張正祥自己的話說:“滇池、西山是我的母親,我現在長大了,一定要回報她。”
張正祥買來照相機,實地拍照取證,不斷寫材料反映情況,漸漸引起有關部門關注。礦主們再不敢小瞧這個農民,不得不騰出精力來對付他,先是收買,在兩條香煙盒里塞進20萬元,給他送去,他不要。收買不成就威脅、恐嚇,有一個礦主曾放言:“誰把他撞死,我來出錢!”他不怕,繼續舉報。威脅利誘不奏效,又改為毆打,見面就打。他一個人走在路上,常常被幾十個身強力壯的大漢圍住,一頓拳打腳踢,而他連被誰打的都不知道。張正祥說:“我被他們打的次數,數都數不清。”他被打得遍體鱗傷,牙齒、脖子、肋骨、手腳全身都是傷痕,右手粉碎性骨折。最危險的一次,頭頂被人用石頭狠狠砸中,鮮血從眼睛、耳朵、鼻孔里同時流出來,他的右眼因此嚴重受損,幾乎失明。
人被打殘,好好的一個家也散了。張正祥曾是遠近聞名的養豬大戶,是農村最早的一批萬元戶,生活富足,家庭美滿。自從他走上環保之路,家境每況愈下,兒子由于受到驚嚇精神失常,常住精神病院。家人無數次哀求他不要多管閑事,惹火燒身,他不聽,倔強得像塊石頭。傷心絕望的妻子不告而別,兩個女兒不肯原諒他,出嫁后都不愿跟他來往。張正祥的舉報行為,斷了礦老板的財路,也讓附近村民的收入受到損失。他甚至遭到村民的驅逐,被迫數次搬家,如今孤身一人住在破敗的房子里,有時兩個饅頭就是一頓午飯。他每天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背起挎包,手拿照相機和望遠鏡,繞著滇池行走,發現污染立刻舉報。孤苦伶仃,踽踽獨行,年過花甲的張正祥依然在戰斗。
三
黃先銀守在鄱陽湖畔,張正祥守在滇池邊,兩個人遠隔千里,互不相識,命運竟如此相似。他們做著同樣的事情,經歷著同樣的遭遇,眾叛親離,妻離子散,一個被稱作“精神病”,一個被稱作“張瘋子”。我曾捫心自問,假如自己處在那種境地,能否堅持到底?答案令我汗顏。到底是什么在支撐著他們一路走來,我似乎無法走進他們的內心世界。直到前不久,我在阿拉爾海遇到那名水手。
阿拉爾海位于哈薩克斯坦和烏茲別克斯坦之間,曾經是世界第四大淡水湖。由于環境嚴重惡化,在短短幾年內,烏茲別克斯坦境內的湖區徹底干涸,昔日碧波萬頃的湖面,已變成沙漠。大大小小的船舶殘骸,依然保持航行的姿態,靜靜地躺在原地,仿佛在向人們訴說凄涼。這里成了船舶墓地,吸引著世界各地的人前來旅游觀光。我在那里參觀,遇到一位老人,他年輕時在這片水域當水手,幾乎每天都要來這里看看。老人愛聊天,談起當年的湖區盛況,渾濁的雙眼立刻放射出異樣的光芒。他張開雙手向我們比劃,“就在這里,以前能抓到這么大的魚!”我說:“水都沒了,您還守在這里干嗎?”老人傷感地說:“你沒做過水手,不會明白水手的心情,總有一天,魚兒還會回來的。”
時常想起老人的話,想起那張神情落寞的臉,忽然就理解了黃先銀和張正祥——做一名水手,哪怕是在沙漠!
(李 晨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