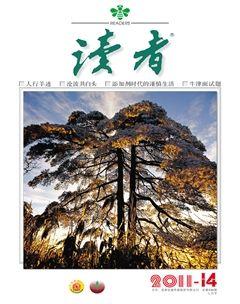樂趣,是幸福的真意
〔美〕米哈里·契克森米哈賴
談到改善生活的經(jīng)驗(yàn),大多數(shù)人第一個(gè)就聯(lián)想到享樂:山珍海味、和諧的性生活以及金錢買得到的一切享受。我們也常會(huì)夢(mèng)想到異國(guó)旅游、與風(fēng)趣的人為伍或購(gòu)買昂貴的商品。如果我們沒有能力負(fù)擔(dān)五花八門的廣告慫恿我們?nèi)プ分鸬哪繕?biāo),至少也會(huì)安于端一杯酒,在電視機(jī)前靜靜消磨一個(gè)夜晚。
享樂是意識(shí)中的資訊告訴我們,已經(jīng)達(dá)到生物程序或社會(huì)制約的要求時(shí),所產(chǎn)生的一種滿足感。饑餓時(shí),食物的味道令我們愉快,是因?yàn)樗徍土松砩系牟黄胶狻M黹g一邊被動(dòng)地從媒體吸收資訊,一邊用酒精或藥物麻醉因工作而變得過于亢奮的心靈,有助于放松自己。
享樂是高水準(zhǔn)生活重要的一環(huán),但享樂本身并不能帶來幸福。睡眠、休息、食物與性,都屬于恢復(fù)“均衡”的經(jīng)驗(yàn),它們并不能帶動(dòng)心靈的成長(zhǎng),也不能增加自我的復(fù)雜性。換言之,享樂雖有助于維持秩序,卻無法在意識(shí)中創(chuàng)造新秩序。
一般人想要進(jìn)一步充實(shí)自己的生活時(shí),不但會(huì)想到享樂,還會(huì)想到雖然與享樂重疊,但必須用不同字眼表達(dá)的另一種經(jīng)驗(yàn)——樂趣。所謂樂趣,是指一個(gè)人不僅需求和欲望得到滿足,更超越既有制約,完成了一些意料之外的事。
樂趣具有向前發(fā)展的特性,并蘊(yùn)涵新鮮感和成就感。如在網(wǎng)球賽中險(xiǎn)勝,用通過考驗(yàn)證明自己的能力,就是一種樂趣。閱讀一本書,發(fā)掘新觀點(diǎn);在談話中發(fā)表過去甚至不自知的觀點(diǎn),都是樂趣橫生的事。談成一筆競(jìng)爭(zhēng)激烈的生意,或做好任何一份工作,樂趣自在其中。這些事在進(jìn)行的過程中,都談不上什么享樂,但事后回想起來,我們情不自禁要說:“真好玩!”而且盼望一切能重演。經(jīng)歷過有樂趣的事,我們感覺自己有了改變,自我有了成長(zhǎng);在某些方面,這些經(jīng)驗(yàn)已使我們變得更復(fù)雜、更豐富。
享樂的經(jīng)驗(yàn)也能帶來樂趣,但這兩種感受截然不同。舉個(gè)例子,吃喝對(duì)每個(gè)人都是一種享受,但從中得到樂趣卻比較困難。唯有在吃喝時(shí)投入夠多的注意力,分辨各種不同口味、佐料之間細(xì)膩差別的人,才會(huì)跟美食家一樣,覺得這件事樂趣無窮。從這個(gè)例子可以看出,享樂不需耗費(fèi)精神能量,但樂趣必須運(yùn)用高度的注意力。換言之,享樂可以不花力氣,只要大腦特定中樞受到電擊或藥物的刺激,就可能產(chǎn)生享受的快感;但是打網(wǎng)球、看書、談話,若不全神貫注,就會(huì)覺得索然無味,毫無樂趣可言。
也正因?yàn)槿绱耍順返钠藤亢黾词牛荒軒?dòng)自我成長(zhǎng)。復(fù)雜性卻要求把精神能量投入具有挑戰(zhàn)性的新目標(biāo)。從孩子身上很容易發(fā)現(xiàn)這種過程,每個(gè)小孩一開始都是小小的“學(xué)習(xí)機(jī)器”,每天嘗試不同的新動(dòng)作、新詞匯。當(dāng)孩子學(xué)會(huì)一種新技能,臉上那種專注的喜悅充分說明了樂趣的真諦,而每個(gè)充滿樂趣的學(xué)習(xí)經(jīng)驗(yàn),都使孩子不斷發(fā)展自我。
不幸的是,成長(zhǎng)與樂趣間自然的關(guān)聯(lián)會(huì)漸漸消失。或許因?yàn)槿雽W(xué)以后,學(xué)習(xí)就變成一種外來的負(fù)擔(dān),掌握新技能的興奮因而不見了。一般人很容易自囿于青春期發(fā)展成形的狹隘自我中;太過于自滿的人往往要求附帶報(bào)酬,才肯在新目標(biāo)上投注精神能量,以至于無法再?gòu)娜松橙∪魏螛啡ぃㄒ坏姆e極經(jīng)驗(yàn)只剩下享樂了。
另一方面,許多人會(huì)繼續(xù)努力從所做的事情中尋求樂趣。我在那不勒斯破敗的郊區(qū)認(rèn)識(shí)一個(gè)老人,他經(jīng)營(yíng)一間家傳的古董店,生意清淡,只能勉強(qiáng)維持而已。一天早晨,一位看來很高貴的美國(guó)婦人走進(jìn)店里,瀏覽了一會(huì)兒,便詢問一對(duì)巴洛克式木制小天使的價(jià)格。那種圓胖的小天使是幾百年前那不勒斯工匠最偏好的創(chuàng)作題材,如今也還有不少藝術(shù)創(chuàng)作者相當(dāng)偏愛。老人隨口報(bào)出一個(gè)高得嚇人的價(jià)錢,那婦人不假思索便掏出皮夾,準(zhǔn)備買下這對(duì)藝術(shù)品。我屏住呼吸,心中暗自替我這位朋友的好運(yùn)道稱慶,但我對(duì)老人的了解顯然不夠。他的臉頓時(shí)漲得紫紅,慌亂不安地把客人請(qǐng)出門外:“不行,不行,夫人,真對(duì)不起,我不能把這對(duì)天使賣給你。”他一遍又一遍對(duì)那目瞪口呆的婦人說,“我不能跟你做生意,你明白嗎?”
那個(gè)觀光客走了以后,他心平氣和地解釋自己方才的行徑:“如果我在挨餓,我一定會(huì)收下她的錢。但我沒挨餓,何苦做一筆一點(diǎn)意思也沒有的生意呢?我喜歡討價(jià)還價(jià)時(shí)的機(jī)智往來,兩個(gè)人互相想占對(duì)方便宜,各出心機(jī),唇槍舌劍。但她連考慮都不考慮,她什么都不懂,甚至連假設(shè)我會(huì)占她便宜的起碼尊嚴(yán)都不給我。如果我把那對(duì)東西用那么荒唐的價(jià)格賣掉,我就洗不掉騙子的罵名了。”
沒有樂趣,人生還堪忍受,有時(shí)甚至也還算得上愉快。但這種愉快不會(huì)持久,要靠運(yùn)氣和外在環(huán)境幫忙,所以必須學(xué)習(xí)從每天的生活中創(chuàng)造樂趣。
(周吉摘自中信出版社《幸福的真意》一書,喻 梁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