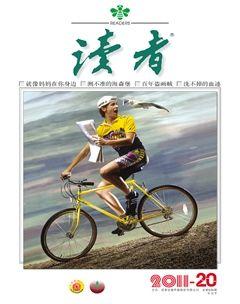一個指頭的問題
陳四益
毛澤東喜歡講一個指頭同九個指頭的關系。那是比喻,講缺點與成績,意謂成績大大,九個指頭;缺點小小,一個指頭,不能顛倒了主次。這里要講的不是比喻,而是實實在在一個指頭的問題。
已是幾年前的陳年老賬。那年,右腳大腳趾忽然隱然作痛。癬疥之疾,從不在意,未予理睬。不料疼痛日劇,舉步維艱,這才有點著急。因為指甲縫中有些紅腫,便掛了皮膚科的號。醫生是一位女士,三十尚不足,二十頗有余。
“怎么啦?”醫生不動聲色問了一句。
我趕緊脫下襪子,指著患處說:“這里好像有些發炎,很疼。”
她只遠遠地斜眼望了一下,也不問哪里疼,更不按一下痛處,開了消炎藥、消炎膏和碘酒,便打發我走了。到醫院前,為了不致討醫生嫌,特地重洗了腳、換了襪子,看來純屬多余。
按照醫囑,服藥、涂膏,一周過去,紅腫略退,疼痛依然,并有加劇之勢。于是,再次去了醫院。換了一位醫生,依然年輕,依然女性,當然,依然是隔得老遠瞄了一眼,說是不發炎了。我說疼得更厲害了。她說:那就再搽搽碘酒。
碘酒搽了一月有零,本不想再去醫院,無奈疼痛椎心,只好再度就醫。這回有高人指點,說可能是嵌甲引起甲溝炎,弄不好要拔指甲,拔甲要掛“普外”(普通外科)。這位醫生,雖然一樣年輕,卻是男性。醫生伸過頭來,看得略為仔細,但依舊沒有“零距離”接觸,手指也不碰一下患處,便約定過兩天拔甲。
居然要拔甲。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喜的是找到了病根,可以術到病除;懼的是十指連心,不知要忍受怎樣的痛苦。好在長痛不如短痛,把心一橫,按時到了醫院。不料約定的醫生有事不在,便另掛一號,請一位年近花甲的主任診治。主任畢竟不同。先是仔細看了患處,然后將腳趾各處一一按到。診畢,開言:“我看不要拔甲。如果你相信我,先去修修腳。修腳之后,過幾天再來,我給你一些指導。”不用拔甲,令我喜出望外,但修腳是否有用,頗存疑慮。我知道過去澡堂里都有修腳的,但從未嘗試。
抱著姑妄一試的心情,在網上找尋修腳的地方。時下滿街都是洗頭洗腳的場所,據說都能修腳,但我不敢貿然光顧。最后找到了一家腳病治療中心,據稱,用具都是一次性的,刀具都經過嚴格消毒。正規修腳師傅現在已有了行業技術職級,以大夫相稱,不過許多人仍習慣于叫“師傅”。替我修腳的師傅姓王,是腳病治療最高的專家級。聽我說原先準備拔甲,他輕輕回了一句“不用”。我問不拔甲能治好嗎?又是輕輕一句:“能。”治療只花了十分鐘。先用熱水泡了病腳,然后端坐沙發,腳擱在小幾上。王師傅一手握腳,一手不停更換不同的刀具削修指甲,嵌入肉中的指甲被他挖了出來。他指給我看一塊大約半厘米長的不規則形指甲:“就是這塊。”也怪,就這樣,痛了一個多月的大腳趾,不流血、不切口,竟霍然而愈。
“要敷藥嗎?”“不用。”“要包扎嗎?”“不用。過一個月再來看看。”接著,他向開票的說:“嵌甲,十塊。”當然,這是那時的價格。
來的時候,疑慮重重。走的時候,輕輕松松。沒想到中國傳統的修腳,有如此神奇的功效。中國人向來是重“道”的,所以幾部經書至高無上,直到今天還為人津津樂道,要小孩子也讀,而談“器”的書本來就少,又不被重視,修腳之類的技藝更屬下九流,如果當初有人寫下一本,傳至今天,該是一部治療腳病的醫學名著了吧,可惜沒有。就是到了今天,醫學院校也是不會將它列為教學內容的,科班出身的醫學家,有幾個能像替我看病的那位主任,毫無門戶偏見,向病人推薦“修腳”呢?所以,“腳病治療中心”依舊附屬于浴池,難登大雅之堂。
一個指頭的問題,糾纏了我幾近兩月,若因九個指頭完好無損,以為一個指頭無需重視,結果也會影響全般。解決一個指頭的問題,一樣要認真研究,略看形象便開藥方,大抵只能遷延時日而貽誤治療。及至病痛加劇,為求徹底而亂施手術,造成不必要的痛苦,是為過猶不及,弄不好還會引出其他問題。這也算我經此一事,格物致知的一點心得。
(金雁摘自《南方都市報》2011年7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