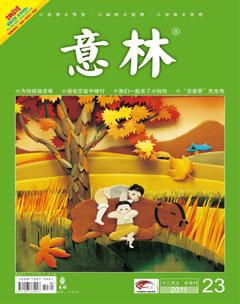手怨
蔓殊菲兒
小的時候我會不由自主地望著我的母親發呆,因為她的臉龐和身材,每一個角度都是那么柔和,沒有一絲缺憾的地方。而我,從鼻子往下就不像她了。很多人說我的母親很美,而我母親說外婆更美,可外婆又說我的老外婆還要美……我發現我的一切都不如我的母親——除了雙手,而母親和外婆有著一樣的手——也像我老外婆的手。“小蔓,你的手生得真美,可以做手模了。”同學們都這么說,是的,我們家族出眾的美色源于我的老外婆。百年之后,美人只留下了一雙素手得以傳世,我癡對鏡中的婉轉柔荑,恨不得用黑袍裹住所有,只留素手。除了寫詩,我也愛畫畫,但都是女子的小圖,上不了臺盤。不知為何,我總覺得自己難以畫出那柔若無骨的手的美態——因此所有的女子都長袖到腰,或空著手腕。
我于是想念她,直到摧肝斷腸,我渴望那個女子溫暖的懷抱,我渴望,她著一襲桃紅色繡花的長襖蹺起她妖嬈的蘭花指婉轉而唱。她可以抱我在懷里,說:“來,我的女兒,你想要什么?”我會快樂地說:“媽媽,我,要你所有的美貌……”
是的,我的老外婆,那個引起火拼的女子,讓幾十個男人橫尸街巷,她最終被一個最有力的男人所得,夾在臂間,在他飛馳的馬上隨風揚起她三尺如緞的青絲。紛爭破碎的年代,愛情可以如此壯烈而唯美……那個叫絹紅的女伶,剛剛從戲臺上下來,才除下外袍,披上紅色的繡襖,就有男子闖入,強抱她入懷,于是,長長的水袖,帶下粉盒彩碟,撒落一地艷紅的胭脂。絹紅,不光容貌秀美,而且有一雙潔如玉琢、情感千態的手,讓所有見過她唱角的男子為之失魂。男人帶她回去,兄弟們,已拉起了紅綾,順順利利拜了天地。
那天晚上,本是應完成母親布置的課業,可我又在偷畫我心目中的那個女人,束緞纖腰,秋水杏眸,正在羞答答地含情脈脈地唱著昆曲,不知是聽琴還是思凡,左腕伸出水袖。母親過來時,畫已完成,旁題了小詩,署為絹紅。母親奪畫在手:“為什么空著腕子?”“我畫不出來……”我怯怯地說。“以后不準畫我的外婆!”母親命令道,“你的技術再好,你都無法畫出那雙絕色的手。”
是的,那是我無法畫出的絕美畫面,因為母親的冷酷和嚴厲,我一直在為自己尋找一個溫柔的母親,那就是我從未謀面的老外婆,相傳她是一個極溫柔的女人。如果她在世,我絕不會受到任何責打。然而,這么想念和愛著她的我卻連給她燒紙錢的機會都沒有……在老外婆的舊宅,我捂住臉哭了起來,她早在我母親出生之前就已死去,我無比愛的,只是一堆再也找不到的白骨,我越發感到絕望。郊外的夜是安靜的,老外婆的木樓梯在深夜被我下樓的腳步踏得咚咚響,我從洗手間回來,經過一個老舊的穿衣鏡,我對著里面張了一張,在夜色下,橢圓的豎鏡里有一個女人——但不是我!我開始一驚,接著心狂跳起來,那個女人背對著我,著暗紅色的繡花大衫,如意領,盤花美到了極點的發髻,髻墜是精美的雙麒麟銀鈿,垂下一小排寸余長的銀桃兒流蘇。我不害怕,我真的不害怕,我知道是她,她坐在鏡子里面,而她也慢慢地轉過來了,是的,她比我的母親更美麗,她清秀得不含煙塵氣的面頰眉目若畫,美若天仙。我看著她望著我笑,我也笑,我高興得要暈了,我向她伸出手,她也迫近了向我抬起袖子來——然而,我在這一瞬看到了十六年來最令我恐懼的事情——老外婆沒有手!袖子滑落后,她只有一雙圓頭的光禿禿的手腕……像我畫的一樣,我只覺得眼前一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我病了,成天發燒說著胡話,只要見到鏡子就嚇得發抖,為了治我的病,外婆請出了所有的人,跟我一個人講了連我母親都不知道的埋藏了六十年的家族秘密——
老外公原來是跑黑道的,金盆洗手后卻沒有正當路子掙錢的本事,于是便靠暗里賭博作為進項。雖然運氣頗佳,很少輸錢,可后來不行了,只出不進。哪曉得最后短短三個月,輸得精光,房產和地契都賠了進去,這時候對方背后的那個人就走出來了,賭桌上一見,分外眼紅,就是為了爭奪絹紅死了二十幾個弟兄的那個男人。老外公心里發憷,想立刻走人,可對方把贏得他的所有東西都叫人給拿了出來,另加五千大洋,在賭桌上一邊堆成了小山,另一邊放著把無鞘的一尺刃的雕龍砍刀。老外公下死命地去賭這最后一次,可還是輸了。他一咬牙,提著刀就出去了——
“你知道你老外公這邊下的賭注是什么嗎?”外婆笑著,我心里已經清明了,頓得開朗,點了點頭,外婆于是自己接口答道:“就是你家老外婆的一雙手!”
(黃凱摘自《胭脂淚妝》二十一世紀出版社圖/陳明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