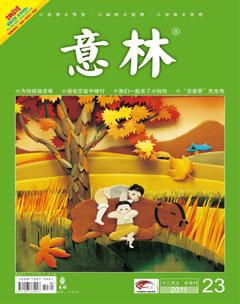情書
吳念真
偶爾他還是會想起60年代那種雙排對坐、黃色的臺北公交車,因為那種座位方式讓他和那個女孩有長達半年的“相親”時間,而那顏色根本就是他們愛情的象征。
那時候他在松山一家機械工廠當技工,晚上則在城內一家商工學校夜間部進修,高三那年的某一天,那女孩出現在他眼前。
他上車的地方是公交車的起站,所以通常都有座位,他習慣在上車之前買一個菠蘿面包當晚餐,在車內乘客逐漸增多之前啃完。
有一天,他看到對座出現一個好看的女生,也和他一樣,低著頭認真地吃著面包,不過是起司的。
那女孩之前沒見過,制服上頭的校名和學號顯示她念的是離他學校不遠的一個女子商業學校,同樣是高三。
車子逐漸進入市區,乘客逐漸擁擠,不過,透過搖晃的人縫,他反而可以比較放膽地去看她那好看的模樣。
之后半年,每星期有三四天,他們倆重復著這樣的路程,彼此知道對方的存在,通過她同車同學偶爾的呼喊,他甚至連女孩的名字都知道,但兩人卻連一個招呼、一個笑容都未曾交換。
寒假看不見的日子,他竟然會覺得失落,甚至會傻傻地想:那女孩呢?會不會跟我想她一樣想念我?
天氣轉暖后的某一天,在擁擠的車子里,他聽見那個聒噪的同學說:“啊!木棉花都開了!”然后他聽到那女孩說:“我好喜歡木棉花,覺得它好男人!”
那天晚上他翹了一節課,跑到仁愛路三段,趁路上沒人,也不管樹干粗糙刺人,他攀上一棵木棉樹,連花帶枝干折下一整段,然后坐出租車回到終點站等她出現;當他把花遞到她眼前時,她看著他,沒什么特別反應,只淡淡地說:“你好神經。”
第二天傍晚上車的時候,女孩走過來,遞給他一個信封,然后依舊沉默地坐在對座,慢慢地吃著她的起司面包。
教室里他迫不及待地打開信封,里頭是一張紙,但只貼著一個一塊錢的銅板,以及五個阿拉伯數字,一如天書。
同學罵他笨,說:“她叫你打電話給她啦!”
第二天他打了,是一家木材加工廠的總機,他說:“請幫我接×××小姐……”之后,總機竟然一陣沉默,然后是她的聲音。
幾年之后的婚禮上,他一字不漏地重述了那次電話里她講過的話;說當他聽到女孩哽咽地說寒假沒課竟然還跑去坐公交車,說“我就知道,我完了”的時候,電話這頭的自己一樣熱淚盈眶。
那時候他已經在三重跟人家合伙開了一家小小的工廠,合伙人管業務和財務,他只管技術。第三年春節后才開工不久,有一天工廠忽然沖進來一堆人拆機器、搶原料,原來合伙人開出去的支票陸續跳票。
工廠登記的負責人和支票出票人的名字都是他,所以因違反票據法進了監獄的人當然也是他;這不打緊,更可怕的是即便人都已經關在監獄里了,家里竟然還有人不時跑去騷擾、討債,房東受不了,要他太太搬家,而這一切,會客的時候,太太都不曾跟他說。
直到有一天接到太太的信,才知道她去了南部,說是以前的同事幫她介紹了工作,她要他忍耐、要他堅強,說“我和他都在等你回來”。
他是誰?第二張信紙上有答案,上頭貼的是一張超音波的圖像,以及太太簡短的說明:“醫生說,他是男生!”
出獄的時候,孩子已經兩個月大,他說他記得第一次抱著孩子和太太走在南部某個城鎮黃昏的小路時,路兩旁的木棉花正盛開,太太從地上撿了一朵給孩子看,喃喃地跟孩子說:“要記得,有這個……才有你哦!”
直到如今,他說偶爾他還會想起那天黃昏太太的聲音和表情。
之后十幾年他的事業超乎想象的順利,孩子國中畢業那年,他已經有能力在美國買房子,并且讓太太陪著孩子在那兒就學。二十多年過去了,木棉花一直是他生命里無法去除的……思念。
(劉振摘自《這些人,那些事》譯林出版社圖/張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