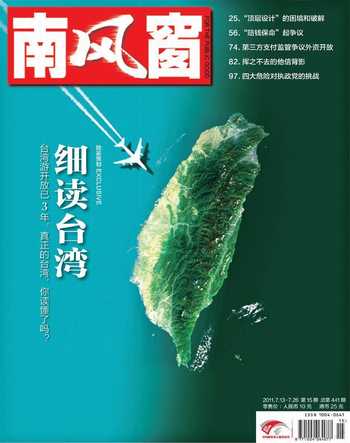蔣介石差點變成老憤青
丁學良
中國人從19世紀上半葉開始與西方國家打交道,此后是一個漫長的矛盾期。《劍拔弩張的盟友:太平洋戰爭期間的中美軍事合作關系(1941~1945)》一書中,也記述了蔣介石與西方國家交往的諸多細節。蔣介石本身留學日本,并非土老包,他的夫人宋美齡更是自小去了美國,深諳美國文化,國民政府也有許多海歸派官員,即便如此,蔣介石與西方國家的關系亦常常處于波濤洶涌之中,到二戰將近結束時才基本調整到平衡狀態。
在抗戰時期的國際關系處理中,汪精衛完全站在民族的對立面,蔣介石則是站在傳統的中國立場,他希望證明,英美雖然是白種人,但會幫助中國戰勝日本。
據書中記載,即使抱著這樣的想法,蔣介石在同盟國關系中還是受到刺激。他在1941年12月11日的日記中記述,日本隨時可能進攻新加坡和香港,因此建議英國馬上與中國簽訂聯合防務計劃。但不久后發現,英國、美國和荷蘭早在6個月以前就做出了遠東地區的共同防務安排,根本沒有告知中國。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對我輕(把中國看得無所輕重),國際關系以利害為主,沒有國家會為了他國利益做出犧牲。如果把這種國家間的利害關系看作異常的怪現象,就是發癡了。
在國與國之間的摩擦難以避免的客觀現實之下,美方的軍事顧問史迪威的個人作為更加深了中美兩國的矛盾。除了史迪威,另一個使蔣介石感到憤怒的是英國駐印度部隊總司令Wavell上將。Wavell上將要求中國政府把美國援助的存放于緬甸和印度交界處的戰略資源無條件提供給英國使用,這些資源相當于中國的生命。對這個狂妄的要求,美國將軍馬格魯德也感到不可忍受,他提醒Wavell上將,現在大家是同盟國,不應該把中國撇開。蔣介石在兩天后,12月13日的日記中憤怒地寫道,英國的盜心、自私更甚于德國,英國之所以蔑視中國,就因為我們是有色人種。
加入同盟國以前,蔣介石四面八方尋求支援,想盡一切辦法拉攏盟友,極具孤獨和凄涼之感。然而加入同盟國以后,卻常常要面對西方國家的不禮貌和不公平對待。印度的甘地曾反問蔣介石,白種人不會以平等的態度對待印度人,你們相信西方國家會讓中國進入英美參謀長聯席會議嗎?蔣介石對此感到憂慮,他在日記中說,在戰時,西方盟國需要中國,尚且如此,到了和平時期,西方盟國不再需要中國時,將會如何對待?
但在中美關系中,還是有一些明白人的。齊錫生給予最高評價之一的美國國務院負責政治關系的官員Hornbeck,就是其中一人。Hornbeck曾提出警告說,雖然蔣介石沒有與日本談和的打算,但在當時的中國,沒有一個人的權力可以決定一切,仍然存在許多主張與日本談和的力量。如果西方對中國的援助有名無實,只會令蔣介石一派的力量潰敗,導致同盟國不愿意看到的結果。然而,如Hornbeck這樣的明白人的言論,并不能完全影響美國政界和軍界。蔣介石寄希望于兩次入緬戰爭,希望打通緬甸通道,讓同盟國對中國抗戰后方西南地區的援助順利進來。他最大的擔心,并非日本軍事上的侵略,而是各個地方的割據勢力活活把中國撕破。
事實上,只差半步,蔣介石就邁到老憤青的立場上了。在蔣介石看來,英國人、日本人比德國人還要壞,他最信任的是美國總統羅斯福。但羅斯福的注意力集中在歐洲戰場,對中美之間的交往并非事事過問。據齊書記載,在1944年的9月30日至10月1日,中美關系走到關鍵時刻。蔣介石在日記中交底,說“如果美方仍然如此狂妄與愚昧,我們接受它的援助就毫無意義”,“美國這樣對待中國,與當年日本和俄國企圖把中國變成附屬國有什么區別?我們絕不會重蹈覆轍”。蔣介石向美國攤牌,如果美國不把史迪威召回,寧可斷掉同盟關系。蔣介石在1944年10月10日發表講話說,現在在地球上,沒有任何人幫助我們了,中國人必須爭氣,抗戰到底。幸虧在最后一刻,羅斯福親自過問此事,把史迪威召回美國。不久后,美國戰時生產局局長Nelson以美國總統私人代表身份率團訪華,并對中方表示,羅斯福總統已下定決心幫助中國工業化,使中國成為亞洲強國,以遏制日本擴張,幫助中國也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此后,中美同盟關系慢慢走向互信。
從書中可看到,太平洋戰爭爆發前,中國獨立抗擊日本,蔣介石最大的愿望是恢復到“九一八事件”以前的狀態,從來沒想過打敗日本,更沒想到一舉把西方列強趕出中國。到二戰結束時,可以看到建立同盟關系的好處超過了預期,中國不僅抗戰勝利,還收復了臺灣和東北三省,贏得了國際尊重。加入同盟國,可以說是從明清兩朝至二戰結束,中國領袖在處理國際關系中做出的最明智決定。
蔣介石幸好沒有成為老憤青,而是在關鍵的問題上保持了理性的判斷和思考。如果蔣介石跨出那半步,今天就與汪精衛站在一起了。今日的憤青們,可引以為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