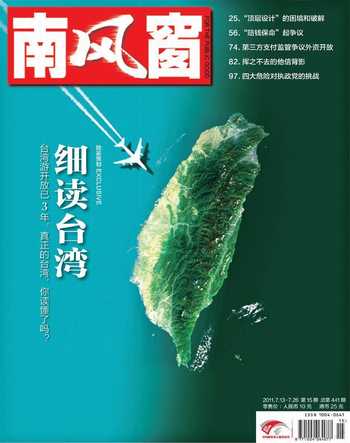吳為山:我的野心很大
章劍鋒

吳為山有著強烈的自我認同感。他視自己的談吐如同字字珠璣。是以入座30分鐘之后,他突然喃喃著跑出去找人把攝像機架了起來,“我很珍惜我自己的生命,我自己的聲音得留存著。”
倘若你知道,吳為山一手雕琢的孔子像早些時候曾被大張旗鼓地安置在東長安街口,與天安門比鄰呼應,就不難理解這位雕塑家如此喜歡自己不是全無理由。一尊孔子雕像為他自己、也為傳統工匠作業且地位一度落寞至無名傳世的雕塑界兌現了不少主流價值,更令他豪情盈懷。
吳為山已經不止一次確證了自己的能干和一切如何不成問題。正是在這推力作用下,他憑著一手技巧嫻熟的歷史文化人物塑像,一步一步接近公共視野,終至衣錦加身。現在吳為山一人獨踞中國藝術研究院美術所所長和中國雕塑院院長兩把椅子,位在雕塑界頭排。
“他是能夠駕馭這個社會的人,他是個行動者。”首都師范大學教授尹少惇說,“他不怵這個社會,很多東西他敢去做,敢去嘗試,敢去接觸。所以他最后能如魚得水。”
“我的野心很大,我想讓我的作品遍布全世界。”吳為山說。
無爭議,不藝術
孔子像將吳為山推向了一般人不可超越的高度。在參觀自己的作品時,吳為山竟落淚了。
妻子吳小平說,“我們開著車,帶著朋友,晚上在月光底下看孔子像,我覺得對他而言是個高峰。”
可是滿城風雨隨即襲來。那個不可超越的高度,只得以維持100天即告了結。輿論關注下,國家博物館將之遷入西庭院。潮起潮落瞬息之間。
為免節外生枝,他們夫妻夜不能安眠,討論出來的對策是緘聲不語。稍縱即逝的機遇,于他們而言已經變成一只燙手山芋,必須放棄。
有形的高度雖已被削去,無形的高度在吳為山那里卻依舊存在。他身邊一些人甚至強調這件作品并非時人所能置喙,其評價權應遺諸后世,因這件作品本屬于歷史。
“作品已經很好地展示過了。只是說放的地方有一些爭議。移到里面還是挺好的。西方很多好的雕塑,都在盧浮宮里面啊。關鍵是人們能從作品里看到更多的文化內涵,得到更多的藝術感動。”
其實,這種爭議對吳為山來說早就不是頭一遭。
2005年,吳為山為南京夫子廟前的秦淮河碼頭設計一組“秦淮流韻”浮雕。他不只將歷史上與秦淮河有沾帶的帝王將相、才子名流裝將進去,又讓李香君、柳如是等脂粉佳人一并入墻。一反傳統的“秦淮八艷”所產生的視覺刺激立時受到口水反彈,被斥為有失體統。
“文化就是要爭論,所有東西都是從爭論到不爭論的。”他頗為不屑地說,“藝術家看待問題,應該用歷史的眼光來看待歷史,不能跟普通老百姓一樣。”
眾聲喧嘩,吳為山據此做了一次標新立異的藝術實驗。當年寒微,他曾將家中僅有不過2000元的積蓄拿去北京大學進修心理學,不能說這與他對于社會受眾心理好似盡在拿捏的表現不存關系。某些時候,對吳為山而言,爭吵有如工具。
“任何一種爭議只會把我推向前,不會難倒我。”
以前的吳為山并不如此。1999年,南京博物院提出要為吳為山設立個人雕塑館,那時候他的表現就不太有底氣。
“我問他能不能做一個江蘇文化名人園。他當時吃了一驚,他說好,回答我的感覺不是很理直氣壯的,有點膽怯。”時任南京博物院院長的徐湖平說,“南博是個藝術天堂,我們是全國三大博物院之一啊。我是覺得他這樣年輕,對藝術有追求,有思想,可以雕琢。”
那一年吳為山35歲,在南京大學任雕塑所所長,聲名尚不如今日炙手。“我當時想我的作品以后會進博物館,但我沒想到那么早。我們把博物館看得很神圣,一個朝代一個藝術家的作品能有一到兩件放到博物館就了不起了,你一個30多歲的年輕人。這肯定不符合中國國情。”
這又是一次爭議,反對意見被徐湖平力壓下去。
“很多人反對,我當時就說,如果你們有更好的作品拿來,我也歡迎。這句話震倒了很多人。”徐說,“這個事只能激發他更加勇猛前進,你說我不行我就要更行,這就是他的個性。不然他就不會有今天了。”
南京博物院這個公共舞臺,讓吳為山平生第一次有了一扇自我展示的對外窗口。只是小巫見大巫,不想這期間他面對的根本就是“小吵小鬧”,真正的口水漩渦已在12年后的天安門廣場上恭候。
“北京的信息量很大,做什么事都能驚天動地。他懂得自我展現,絕對懂得。”徐湖平說,“爭議是個好事情。你越爭,名氣越大。沒有爭議就不叫藝術家了。”
雕塑家發跡
為文化名人塑像讓吳為山發跡。
1990年代,走在雕塑道路上,身雖泛泛的吳為山已很懂得尋找門路。通過關系,他向油畫家周昭坎借上了一臂之力。周當時在民盟中央工作,帶著他出去轉了一圈,費孝通、冰心、吳作人、沈鵬,逐家拜望,結果讓周昭坎反欠下一屁股債。
“當時都答應做了,以后送給人家,結果就做了一個費孝通,一個吳作人,其他人都沒有做。”周昭坎說,“從此以后就發跡了。”
那時期,吳為山經常是背著個破包自費在北京與南京兩地奔走。1995年,當他為費孝通塑像,老人家歡喜異常。后來去江蘇視察工作,特別到吳為山位于南京師范大學的工作室探望。
“這一下不得了,副委員長到他工作室去看,驚動了學校,驚動了民盟江蘇省委。”周昭坎說,“如果是資本的話,這就是不可估量的政治資本,這對他后來的發展,從政治上起了很大的作用。”
周昭坎建議吳為山加入民盟。“他聽了回去就加入了,以后就走得很快了,掛了民盟的職務,有更多機會接觸一些文化界名人。”
入盟后的吳為山,由民盟江蘇省盟員一路攀至民盟中央委員和全國政協委員,藝術能力與社交能力也雙雙嶄露。人脈漸次豐富,他的文化名人雕塑亦橫掃政經、科教、文史各界,作品中不乏楊振寧、陳省身、季羨林這樣名動一時的學術大家。
“你要有一定的話語權,有一些文化影響力,才能做更大的事情。”跟隨吳為山20多年的哲學博士尚榮說,“他現在就是有了一些平臺,他很多致詞里都會寫上感謝這個偉大的時代。”
10多年功夫,草芥無聞時期的異想天開,至此悉數得以實現。
回望17歲那一年,高考落榜,吳為山屈身前往無錫學習泥人捏造,追求批量生產工藝品的學校,向不鼓勵學生好高騖遠去當什么藝術家。他亦視此行當低賤,內心厭惡。
“我心中有一個很大的理想,就是走出泥人的天地,我要走向一個更大的藝術空間。”他說,“真沒想到,今天我的作品在世界很多博物館都有,很多重要的地方都有我的作品。但我覺得現在還不夠優秀。”
向上伸展的生命力一發而不可收,機會再次臨幸于他。
2006年,吳為山在中國美術館舉辦個展,中國藝術研究院的負責人請他夫婦二人吃飯,席間力邀他出任即將籌組的中國雕塑院院長。此時的吳,是南京大學美術研究院的院長,扎根在江蘇地方。
“到北京我不是很喜歡,原因是覺得在大學里,象牙塔似的,很自在,尤其是做個名教授。但是我阻攔不了他。”吳小平說。
2008年,中國藝術研究院那位負責人擢升副部長,不僅聘吳當了雕塑院長,還讓他同時出任中國藝術研究院美術研究所所長。
“給我打電話,很高興,說我現在當所長了,副局級了。后來我跟他說,你到這兒來是沒好果子吃的,北京這邊排外很厲害。他說他能把它搞定。”周昭坎說,“他很會做人的工作,這就是他跟別人的區別,有的時候機會和我們就擦肩而過了,但他很快就能抓住。”
上位如此神速,好似命運事先排定。雕塑家自己于中感觸,竟也不無精妙。
“將軍趕路,不打兔子,向一個既定目標不斷前進,不要顧及生命里的小事情。在路上如果碰到有驢有馬有車,能搭一段的你就搭一段,這叫抓住機遇。碰到一個貴人正好開個車,說小伙子你累了上我車,你就上他車,幾十公里就下去了。”
又是一次錦上添花。到了北京,他更被推上全國城市雕塑指導委員會副主任的位子,儼然中國雕塑界的“帶頭大哥”。要知道,在這上面坐過的,原是主持過人民英雄紀念碑創作的著名雕塑家劉開渠。
欲步先輩泰斗后塵,吳為山的路徑一直遵循這樣一個脈絡延展。他工作過的南京大學,出了徐悲鴻;他出掌美術研究所,乃因王朝聞和黃賓虹曾任職于此。他為他們搞一出題為“任重道遠”的展覽,溯往及今,用意也就盡在不言中了。
“羨慕忌妒恨”
假如吳為山偏安于南京一隅,手眼不高,則未必能在藏龍臥虎的北京取得為國家博物館塑造孔子的機會。功夫在詩外。如他周遭之人所承認,這又一筆資本被納入囊中,無可估量其價額。雖然此路數與傳統作風格格不入。
“傳統藝術圈里,院派里面,有誰這樣干,大家都瞧不起他,覺得他在利用藝術以外的一些事情在炒作。”中央美院教授王中說,“藝術家是干嘛的?最終無非是讓自己的思想影響更多人的思想,那就要講策略,要會借助很多力量平臺甚至一些機遇來做。”
如是輿論,在吳為山長驅直入的一路上屢有發作。當年他還是南京師范大學不名一文的講師,因做了幾尊文化名人雕塑,背上一個傍名人上位的壞名聲。樹未大已招風。34歲旅歐期間,又受邀為荷蘭女王塑像而轟動,風頭甚健,為工作遺下不快。論資格,職稱早該晉為副教授,沒有實現。他所出掌主任的學校雕塑教研室,也遭撤銷,令他發愁到失眠。不合則去,最后只好揮手作別,改棲南京大學。
“本單位的人總是看你小孩子成長起來的,他們不知道我的內心世界,也不知道我到達的高度。”吳為山說,“羨慕忌妒恨,我可以講我沒有敵人。別人把我當敵人我沒有辦法。”
話雖如此,然而雕塑家眼神綻露鋒芒,性格好強。當他一旦夠得上硬度,爭議就不免升級為爭執。
2005年,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紀念館擴建,官方將主題雕塑委托給吳為山創作。主體建筑則由中國工程院院士、日后設計上海世博會中國館的建筑家何鏡堂負責。其間就有一次不可開交的齟齬。
吳為山拿出一組受難者雕塑方案,于主體建筑面前一字擺開,而且整個建筑的外墻也被他設計的殺戮情景的浮雕所染指。
“基本上雕塑都把人家建筑包起來了,像個銅包的戰艦一樣。作者本人嘛,肯定是不希望有人來搶風頭的。”尚榮說,“我們剛開始也沒有考慮別人的。”
反對聲中,浮雕取消,可是爭執仍在。擺在外面那組雕塑中,有一尊高達12米的人像主雕。這高度也遭到反對,讓吳為山好不惱火。
“他不是管他的建筑,他是管我雕塑,不允許我的雕塑高于他,我就正式跟南京市的副市長講,我不做了。我把電話掛掉了。我不是鬧情緒,是要堅持我的真理。”
數番協調,高度降至9米,吳為山究竟是咽不下這口氣,要求相關方面寫出一個備忘錄,講明事實與他本人初衷如何不相符合,以致最終無力回轉,將這樁遺憾鑄下。雕塑落定之日,他又在下面加上一個底座。這人為一手,維持了原來想要的高度。
這組雕塑的關鍵所在,乃是自此奠定吳為山在雕塑界的地位。“原來從來不知道這個人。不管作品怎么樣,至少這個人冒出來了,占據了一個重要的領地。”周昭坎說,“就跟現在國博放一個孔子像,盡管大家覺得莫名其妙,但他占了,整個社會都知道了。”
眼看自己一手提挈的吳為山站在聚光燈下蹁躚獨舞,光鮮撩人,周昭坎卻無一絲悅色。他眼中的吳為山,已經套加了不少光環。周擔心他陷入一種怪圈,因為他親眼見到另外一些被自己發掘出來的大師級人物,紛紛在功名負重下無限膨脹,以致淪陷了自己。
“今天社會給予他這么重要的位置,他不再是當初那個只是為了個人發展的青年,而是要推動整個雕塑事業和美術事業。”周說,“最好低調,我覺得他頭上的桂冠太多了,再往上抬,將來是害他。”
并不是沒有人當面提醒過吳為山這一點。去年春節,徐湖平與登門拜年的吳為山專門談話一次,建議他盡量少參加社會活動,多追求自己的藝術,務必明白“老虎豹子沒有長壽的,烏龜壽千年”的道理。
“我總覺得學無涯,藝術家到這個程度以后應該到深山老林里靜下心來做藝術。他聽進去了,但做不到。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徐說,“北京是什么地方啊?它既是一個偉大的舞臺,同時也是很大的陷阱,他絕對危險。”
而在吳為山看來,箭才上弦、弓未拉滿,又怎能就此勒馬收韁?
“到北京來,賣茶葉蛋的都不認識我,我在南京走到哪里人家都知道我。我喜歡挑戰。一座山爬過以后要爬另一座山。人是不斷要向上爬的,必須去奮斗,冒險也得去。”這位雕塑家躊躇滿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