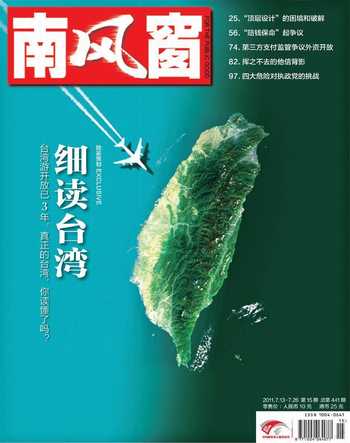第三方支付監管爭議外資開放
邢少文
2011年5月26日,中國央行公布了第一批非金融機構支付業務許可證,27家企業獲得了牌照。正當牌照獲得者歡欣鼓舞之際,中國最大的第三方支付平臺——支付寶股權爭議事件亦甚囂塵上,支付寶事件將行業監管新規中一個“潛伏”的話題引爆:第三方支付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影響國家金融安全?
外資身影活躍于中國互聯網支付企業中,是這一行業的背景之一,而監管新規對外資規定的模棱兩可,引發了中國金融開放程度的爭議和行政監管與市場準入的矛盾,同時凸顯出制度因素影響下的企業家道德風險。
自由生長
2010年6月14日,中國中央人民銀行頒布了《非金融機構支付服務管理辦法》(下稱《管理辦法》),這是中國互聯網支付行業的首份行政監管法規。此時,中國非金融機構互聯網支付業務發展已頗為壯大。
互聯網支付包括了金融機構的網絡銀行支付和非金融機構的第三方支付。1998年,招商銀行首開網絡銀行支付先河,次年,首信易支付則宣告了中國第三方支付的誕生。
所謂第三方支付,是指非金融機構在收付款人之間作為中介機構提供的轉移服務,包括網絡支付、預付卡的發行與受理、銀行卡收單,以及中國人民銀行確定的其他支付服務。
隨著互聯網應用,特別是網絡購物的興起,第三方支付服務真正發力于2005年,依托阿里巴巴的淘寶網,支付寶將這一便捷的網絡支付服務推廣。自該年起,第三方支付規模每年增長在100%之上,業界亦將2005年稱為“電子支付元年”。
根據咨詢機構發布的統計數據,2009年全年中國第三方支付交易規模達到5808.4億元;并預計到2012年,第三方支付市場的規模有望達到1.2萬億元。目前,國內登記備案的第三方支付企業已達390多家。
在互聯網支付的發展過程中,商業銀行由于體制、機制及對市場認識的緩慢,因此第三方支付這一因應互聯網上交易付費便捷、安全需求的服務被非金融機構占領了先機,雖然各大商業銀行紛紛調整推出了網絡支付產品,但時至今日,民營企業為主的互聯網公司,仍然在產品創新和客戶體驗上領先。
第三方支付雖然是一種金融創新手段,但仍然必須依賴于傳統金融機構,在技術流程上,是用戶先注冊支付賬戶,通過登錄支付賬戶完成銀行、信用卡賬戶資金的代交代付,第三方支付平臺則通過與合作銀行的網關、后臺或閉路循環完成網絡賬戶與銀行賬戶資金的轉接。第三方支付的贏利主要通過向注冊用戶和合作客戶收取費率,并與合作銀行分成。
這也注定了,第三方支付與銀行之間,是一種既合作又競爭的關系。
作為一種創新的支付清算模式,第三方支付11年間并沒有相對應的行業監管法規,基本處于自由發展的階段,依靠的是第三方平臺的信譽保證和貼近客戶的產品服務。
“中國的互聯網環境是非常復雜的,個人資金需要安全保障,加上第三方支付的備付金運轉處在金融體系之外,因此進行監管是有必要的。”招商銀行軟件中心一位人士對本刊記者說。
自由發展難免會出現灰色地帶,曾有第三方支付平臺因為涉嫌賭球資金轉移,引起了監管層的注意。“為了規范,也因為第三方支付本身和金融機構是一種競爭關系,從利益的角度出發,也需要進行約束。”上述人士如此理解。
監管新規
為解決第三方支付的“灰色發展”,2005年6月,央行第一次發布了《支付清算組織管理辦法(征求意見稿)》。2009年4月,央行宣布對第三方支付企業進行登記備案。2010年6月,央行以2號令方式公布了《管理辦法》,2010年12月,央行再出臺《非金融機構支付服務管理辦法實施細則》。
《管理辦法》從征求意見到正式出臺,歷時5年,其中也歷經爭議。2005年征求意見稿甫一出臺,即招來支付業界廣泛質疑。質疑點主要集中在幾方面,即:注冊資金的高門檻遏制創新、業務層級管理不明、支付清算定義不清、資金管理方式存在漏洞等等。
“拖了這么長時間才出臺,一方面客觀上和第三方支付的發展還不是很成熟有關,都在邊做邊看,另一方面和利益也有關,第三方支付和銀行是競爭關系,中國的銀行對此并不是很樂意的。”從事第三方支付的人士劉濤(化名)對本刊記者說。
“存在要不要監管,誰來監管,誰牽頭主導的問題。監管部門之間的協調也是一個原因,比如央行和證監會、保監會,由于第三方支付開展了基金代銷等業務,涉及證券公司和基金公司,也需要證監會批準,保險業務也需要保監會批準。”艾瑞咨詢集團產業研究部分析師程善寶對記者說。
在諸多爭議中,對外資的開放程度也曾是爭議的一部分,但并不是重點。
據悉,在此前的征求意見稿中,曾討論過第三方支付平臺中外資股權比例,最初設定為50%,后認為可參照目前外資進入銀行業金融機構的股權單一比例不超過20%,外資股東股份比例合計不超過25%的辦法。
“在外資比例限制上的爭議主要反映出商務部和人民銀行之間的分歧。”國家開發銀行研究院副院長、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支付清算中心主任曹紅輝對記者說。二者對支付清算領域對外資開放程度的意見并不盡相同。
在最終定稿的《管理辦法》中,則對這一問題進行了“擱置”——“外商投資支付機構的業務范圍、境外出資人的資格條件和出資比例等,由中國人民銀行另行規定,報國務院批準。”
從央行的《管理辦法》來看,既沒有排斥外資進入第三方支付行業,但同時也沒有對外資投資做出明確的安排。
在外資投資規定沒有明確的情況下,第一批牌照于5月份有些“倉促”地進行發放,在名義上,這批牌照是完全針對100%內資企業發放的。
實際上,由于中國互聯網企業中,外資自始至終參與其中,成了諸多企業得以生存發展的上帝之手。現時占據了第三方支付市場份額50%的支付寶,也依賴于雅虎和亞洲軟銀這兩個外資股東的資金投入而得以成長。
鑒于中國在外商投資目錄中對支付行業的限制,這些外資大部分采取了協議控制的辦法,這一方式在中國互聯網公司也是常見的方式。
所謂協議控制,即成立中資持股的公司持牌,以符合中國政策的規定,同時通過一系列的商業協議(資產運營控制協議、借款合同、股權質押協議、認股選擇權協議、投票權協議、獨家服務協議)安排,將持牌公司利潤以服務費、特許權使用費等方式轉入外資持股公司。
“央行對這一問題看起來并沒有完善的處理方式,本身也不是很清楚,或者說并沒有明確認識到。”程善寶對記者說。這也為后來的支付寶爭議埋入了伏筆。
2011年5月底,支付寶事件曝出,阿里巴巴集團CEO馬云及其管理層股東在未經集團董事會同意的情況下,終止了支付寶的協議控制,將支付寶轉為完全內資控制。馬云此舉引起阿里巴巴集團兩大外資股東美國雅虎和日本軟銀的不滿。外界有相當部分聲音指責馬云違背了商業契約。
支付寶從內外資共同控制變更為內資完全控制的原因,阿里巴巴管理層解釋為央行要求第三方支付公司應為內資,如果有外資股份,需上報央行另行規定,并報國務院批準,這將對支付寶進入首批牌照名單造成巨大的風險。
但支付寶此舉反而造成了外界對監管法規排斥外資的印象。
除了支付寶,銀聯商務也采取了清退外資以獲得首批牌照的辦法,銀聯商務等“銀聯系”公司通過談判清退了外資,軟銀亞洲信息基礎投資基金出售了銀聯商務近7%共3500萬股。
“外資的持股比例問題,也并不是因為支付寶存在協議控制而引發的,應該說是因為阿里巴巴集團三大股東的股權控制爭議所引發的。”劉濤認為這也是為什么《管理辦法》出臺之后央行才要求企業上報協議控制情況的原因所在。
馬云同時表示,央行首批牌照發放要求企業全內資控制,“我第一次對國家央行有對未來國家安全考慮而敬重。”這使得第三方支付平臺是否真涉及國家金融安全,保護國家金融安全是否應通過內資完全控制來實現成為了監管新規中的一大爭議焦點。
外資與金融安全
事實上,在監管法規出臺的過程中,存在外資持股比例的爭議,但自始至終并沒有完全排斥外資。
中央人民銀行支付清算司司長歐陽衛民曾在2010年11月公開指出:“實際上對電子支付產業的發展,我們要鼓勵競爭,要對內、對外都開放,只要符合辦法的規定都可以按照程序來申請取得支付業務許可證,成為合法的支付服務機構。”
他同時指出,“實際上我們也知道2001年9月,美國就影響電子支付服務的一些問題向中國提出了WTO的磋商請求,認為中國違反了服務貿易協定中做出的一些承諾。但事實上就我們掌握的情況來看,通過去年(2009年)的登記,在第三方服務組織中,現在有37家都是有外資性質的,有一些是全資的,有一些是合資的,當然還有一些是港澳臺的資金、港澳臺的資本,所以說總體來看,我們在電子支付市場當中,一直還是堅持了對外開放的原則。”
事實上,在首批獲得牌照的企業中,并不乏外資通過協議控制的企業。“肯定不是個案。”劉濤說。他認為馬云的“全內資控制論”反而將協議控制擺上了令人尷尬的境地。業界還因此風傳央行收回了一些存在協議控制方式的企業牌照,央行后來對此進行了否認。
“從目前監管層的態度來看,對這一問題實際采取了默認的態度,協議控制的爭議估計也就不了了之。”一位受訪人士認為。
對于《管理辦法》中對外資的另行規定,劉濤認為這也是銀聯和VISA之間爭議的延續,是在保護銀聯的利益,至今國外銀行卡支付清算組織VISA和銀聯之間關于如何開放銀行卡支付市場的爭議還在等待WTO的仲裁。如果明確承認外資投資第三方支付清算組織,雖然有別于銀行卡支付清算,但從道理上有利于VISA獲得WTO仲裁的勝利,順利進入中國市場。
至于外資參與第三方支付平臺,是否涉及國家金融安全的問題,在業界也出現了不同的爭議。
“嚴格來講,第三方支付平臺及銀行卡結算組織在國外并非受中央銀行監管,說明其未納入中央銀行的支付結算體系之中,而是作為銀行零售支付體系的補充,提供支付結算服務。因此,在它對銀行支付結算體系形成實質性調整之前,對支付結算體系的穩定性和安全性的影響都是有限的。”曹紅輝說。
有央行內部人員在接受媒體采訪時也認為,第三方支付平臺不涉及銀行賬戶信息,所有的資金和賬戶信息都在銀行。央行已經建立企業和個人金融征信系統,與之相比,第三方平臺搜集的支付數據只對企業自己有一定價值,對社會而言意義有限。更何況,中國金融業對外開放多年,商業銀行本身早就引入了外資,談不上國家金融安全。
中國金融業目前的政策是對外資“有限開放”,銀行、證券、保險和基金公司,都已經向外資開放,上述行業的外資持股比例上限分別可達25%、33%、50%和49%。
“有些法規你也說不清楚是不是合理,比如國內的麥當勞、肯德基都不讓刷銀行卡,你覺得這是考慮金融安全嗎?”劉濤則打了個比方。而招商銀行軟件中心人士則說:“在技術上沒有很好的保護手段,最干脆的做法就是不讓外資持股,這也是一種很懶的做法。”
而從理念上來說,保護國家金融安全一般通過資本賬戶管制、增加本國貨幣國際結算力度、保持本土大型金融機構的主導地位、在匯率、利率政策上保持國家控制等辦法來達到。
不過,曹紅輝同時指出,第三方支付對金融安全的影響主要反映在它為基于一些非法資金來源的跨境流動提供了便利和可能,比如恐怖活動資金、跨境賭博資金、腐敗活動所獲資金等造成的洗錢活動。“至于它所掌握的客戶信息,肯定要大于單純的銀行卡結算組織,甚至大于銀行,如果不對其在客戶信息的使用方面加以約束,就完全可能造成客戶信息的濫用,甚至構成金融安全方面的隱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