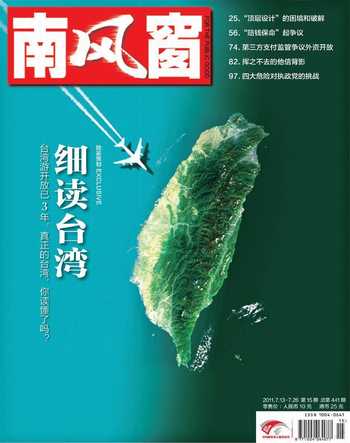財經資訊雙周盤點
“豬周期”又來
“大師兄,二師兄又漲價了。”在網絡上,有人如此描繪過去10周以來的豬肉價格持續上漲。
根據國家統計局7月4日公布的“50個城市主要食品平均價格變動情況”顯示,6月下旬豬肉價格與5月下旬相比,漲幅達到15%,豬后腿肉價格已經突破每斤15元。因為豬價持續上漲,包括湖北、廣東、山東、吉林在內的多個地區均出現“搶豬潮”。
豬肉價格占CPI權重達4.29%,通脹環境下,豬肉價格飛漲無疑給政策制定又添了煩惱。
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不斷地在進行信心喊話,7月3日在遼寧本溪考察期間表示,“最近豬肉價格貴了,得把這個周期過去,再過幾個月就下來了。”
所謂“豬周期”,是從中國改革開放開始,生豬生產和價格在1985年、1988年、1994年、1997年、2004年、2007年共經歷過6次明顯波動,主要標志是價格年環比增長超過10%,其中,有3次大波動,價格年環比增長超過50%。
在往年,政策都曾試圖用行政調控的辦法刺激養豬,但最終是越調越亂,動用財政補貼刺激之后又是價格的急劇下跌。
今年的豬周期除了生豬生產規模化、產業化的水平較低的因素之外,生豬飼養各種原材料的價格上升也是疊加因素,而這是整體通貨膨脹所造成的。如今看來,中國通脹的消退勁頭仍未見端倪。
在稍早一些時候,溫家寶曾在英國《金融時報》上撰文表示,“對于中國能否控制住通脹并保持快速發展這個問題,我的回答是肯定的。”受益于此喊話,中國A股止跌反彈。
但喊話終歸喊話,話音未消,7月7日,央行再次將一年期存貸款利率上調0.25個百分點。
不斷上調存款準備金率和加息,是中國金融貨幣政策自去年年末到今年以來的主旋律,被稱之為穩健的貨幣政策難壓持續的通脹指數。喊話之余,溫家寶也表示,今年將CPI控制在4%以內的目標實現很有壓力。
雖然目前一年期存貸款利率已經達到3.5%,但相對于5月5.5%的CPI指數來說,仍然處于負利率狀態。6月CPI破6看來也沒有懸念,在這樣的情況之下,關于加息已到尾聲的預測似乎并不太靠譜。
對于中國貨幣政策執行者來說,大幅的加息面臨著兩難,倒并不在于會給中小企業形成緊縮資金壓力,而在于大量的國有企業和地方融資平臺,大幅加息對其債務償還將會增添壓力,進一步放大風險。
暫停批準“綜改區”
7月5日,國家發改委體改司副司長徐善長向外表示,除非遇到特殊情況,在目前10個國家級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創造出好的做法經驗之前,“不會再批建新的試驗區”。
從2005年上海浦東新區成為全國第一個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以來,全國很多省市都上報了各類申請綜合改革試驗區的項目。截至目前,國家發改委批準了10個國家級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而據統計,全國已有21個省市先后設立了70多個省級各類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其中大部分是未通過國家級審批,降格為省級的。
在表態暫停批準的同時,國家發改委也對山西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提出了公開的批評。發改委體改司負責人說,《山西省國家資源型經濟轉型綜合配套改革試驗總體方案》原計劃于6月底上報國務院,但卻因內容與發改委的期望差距較大而未能按時上交。
雙方拉鋸的焦點在于改革力度。發改委認為方案過多涉及對于資金、政策、項目支持的索取,而在改革方面卻“沒有真的動作”。“資源經濟轉型需要改革來突破,必須有真的動作,如果沒有涉及這方面內容,這個方案就沒有意義了”。
事實上,在過去的兩三年中,一些地方上報的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搭上了拯救金融危機的順風車,其目的無非是在國家擴大投資和財政支出的熱潮中爭項目、爭貸款、爭優惠措施。
中國改革開放已經進行了30多年,按道理,如今各地的改革政策都已相差無幾,“劃一個圈”搞經濟的時代已經過去。不管是經濟政策還是行政改革政策,都應形成一致的標準。而各地仍然熱衷于上報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目的也無非是希望在土地政策、金融政策、稅收政策、財政轉移政策上得到中央的特殊照顧,利用各種優惠政策進行政府投資,獲取GDP的政績。
以山西為例,山西改革試驗區申請的也無非是土地審批政策優惠,以及“先試先行”煤層氣開采、財政返還等政策支持。
據稱,山西省直部門與縣市領導曾連續4天開專門會議討論改革方案。可改革哪兒會是閉門開會能研究出對策來的?
在中央部委層面上,將這樣的審批權力留在自己手中,也無非就是以審批權享受地方“跑部錢進”所帶來的利益回報,各種部委之間,常常會設立各種各樣的試驗區、新特區、區域經濟發展區的名頭,吸引地方政府的競相爭取。
這種政府設計的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并不一定符合資源配套的最優選擇,在政府主導的情況下,反而會造成巨大的資源浪費和產業結構扭曲。過去幾年中,各地政府熱衷的產業集群式的發展模式,如今也已呈現其弊端。
所謂改革,行政管理體制的改革應擺在首要的位置。
監管央企海外投資
央企海外投資巨虧題材一直不缺少新聞,中鋁是近期的主角,有消息稱,中鋁集團在澳大利亞投資鋁礦4年虧損3億多(除特殊說明,單位均為人民幣),然而現在央企海外投資巨虧,學費要自己掏腰包了。
6月24日、27日,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先后發布了《中央企業境外國有資產監督管理暫行辦法》(以下簡稱《境外資產監管辦法》)和《中央企業境外國有產權管理暫行辦法》,兩文件自2011年7月1日起施行。
《境外資產監管辦法》共7章40條,《境外產權管理辦法》共20條,中央企業及其各級獨資、控股子企業在境外(包括香港、澳門)以各種形式出資所形成的國有權益均受此兩個文件約束。這兩個文件最大的亮點在于,其明確央企為境外國有產權管理的責任主體,相關責任人要為海外投資失誤負責。為推行問責制,文件在明確責任主體的基礎上,提供了具體操作方向,對外經營中普遍存在且易引發國有資產流失的個人代持股權、離岸公司監管、外派人員薪酬等特殊業務提出了規范要求。并特別點出禁止央企以套期保值為由進行投機。
從更細微的操作層面看,在近年日盛的輿論壓力下,國資委此次的手段可謂犀利。在投資過程、操作流程、風險控制等主要企業運作環節,文件都有字眼苛刻的規定。舉個例子,根據《境外資產監管辦法》,境外企業出現包括違規出借銀行賬戶、越權進行投資、有賬外業務和賬外資產等七大情形,就將追究有關責任人的責任。只要操作過程中涉及違法違規的問題,即使境外企業沒有任何損失甚至最終獲得利潤,相關責任人也要被追究責任。實際上,國資委隱含文件中的思路是通過嚴格控制企業的運作程序,尋找虧損的源頭。
文件一經出臺,在業界引起極大關注。畢竟上一次事關境外央企投資的文件是1999年頒布的《境外國有資產管理暫行辦法》,配套設置已嚴重落后于央企境外投資現狀。業界期望通過新的條文和管理體制改變央企海外投資“只花錢不算賬”,“拍腦袋投項目”等種種困境,但不少業內人士對目前條文的效果存有疑問。如文件懲罰條文缺乏細化,對于責任人的認定有待進一步明確化,懲罰措施語焉不詳,如監管部門重疊,互爭頂牛。
更為重要的是,有人認為文件為控制而控制的監管思路有失偏頗,“海外投資,既要保障過程的合法性,又期望實現結果的盈利性。那么如果程序合法但結果虧損,這個責任由誰來承擔呢?”治理海外投資巨虧還在體制改革,建立一套真正的企業運作規則,可這是一個老生常談且呼而不應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