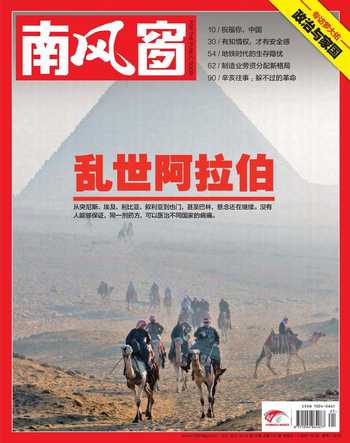亂世阿拉伯
2011-05-30 10:48:04謝奕秋
南風窗 2011年21期
謝奕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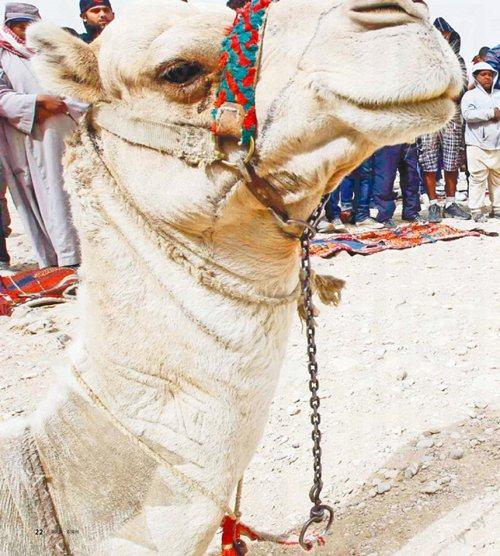

一個二戰后爆發了10多場國際戰爭和無數內戰的地區,2011年再度映入世人眼簾,這次,它給人的直觀感覺還是“亂”,但亂得不僅讓一些人絕望,也讓更多人懷抱希望。
那些令人難忘的場面——齋月里首都被攻占,法庭上前總統“籠中對”,總統禱告時被炸傷……諳熟中東歷史的人、覺著像薩達姆倒臺場景的人也會少見多怪。曾幾何時,納賽爾動了一條運河,霍梅尼動了幾塊油田,英法美就花容失色,這次,奔突在埃及、利比亞等國的野火,居然僅燒著了以色列的一點皮毛,而法英首腦,居然被起義者簇擁走在戰后的黎波里的大街上。世道變換,年輕人取代了軍官和教士,成為“亂世出英雄”的最新代表。
然而,潛伏的危機足以消解上述光鮮的圖景,在敘利亞、在也門,甚至在巴林,僵持還在繼續。沒有人能保證,同一劑藥方可以醫治不同國家的病痛。即便在除舊布新的國度,遠未理順的各階層、各部落關系,在政經發展道路上的缺乏共識,都會毀掉到手的幸福。
“動蕩之門”一旦開啟,無法斷言何時結束,哪怕是被視為“穩定之錨”的阿拉伯君主國,也可能朝不保夕。當民意擺脫了“一致對外”的窠臼,或許只有票箱才能將其馴服。
有人說,中國跟上了全球化的列車,而伊斯蘭文明掉隊了,我們要幫助它。也有人說,海灣阿拉伯國家的現代化不比中國差,甚至局部還有超越。其實這并不矛盾,多面的阿拉伯,足供中國多方位鏡鑒。我們與阿拉伯世界的傳統友誼,不會因幾個“老朋友”的離場就舉座不歡。亂世阿拉伯的教訓,對中國如何走好自己的路,是一種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