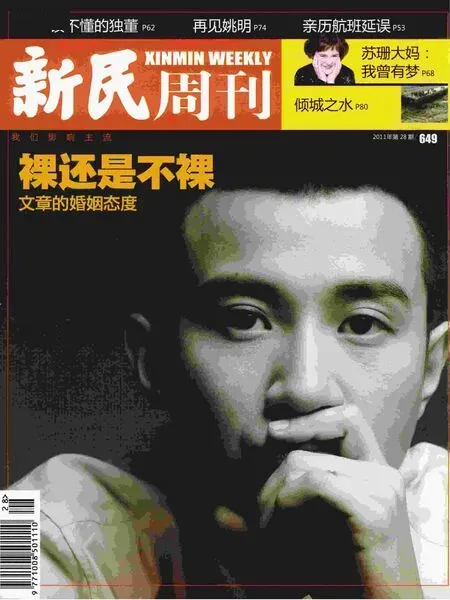從“生源大戰”看大學改革
葉志明
又到了高考招生季節,幾十年來“千軍萬馬過獨木橋”的景象,似乎正在起變化,隨著高等教育普及,考生之間的競爭不再是新聞的焦點,反倒是學校的招生競爭,到了前所未有的激烈程度。在國外大學、港澳(即將還有臺灣地區)大學的競爭壓力下,內地大學不得不放下身段,彼此競爭,才能吸引優秀人才前來就學。這是我國高等教育發展史上的重大轉變,對大學的未來影響深遠。
招生環節的競爭壓力,正向人才培養環節傳遞。生源大戰逼著有抱負的大學校長不得不考慮:什么樣的氛圍,才能吸引優秀的年輕人?什么樣的教育理念,才能培養出優秀的人才?什么樣的培養方式,才能真正讓學生終身受益?這些問題是大學教育的真問題,是決定一所大學在招生時有沒有競爭力的決定性因素。
每每想到這些問題,我就會想起“錢學森之問”。2009年,錢學森去世,他生前提出的一個問題震撼了所有人——“為什么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杰出人才?”
我也常常想起教育改革一線的同行。南方科技大學校長朱清時先生在改革中遇到的問題,被媒體稱為“朱清時之困”。“朱清時之困”有大學辦學自主權的問題,同時也有培養模式的問題。有人說,“朱清時之困”使“錢學森之問”以更加清晰的方式呈現出來。大學改革,必須直面“錢學森之問”,破解“朱清時之困”。
去年7月,“三錢”中唯一健在的上海大學校長錢偉長去世,舉國唏噓。有教育界的同行說,如果大學校長能追隨錢偉長校長的做法,“錢學森之問”的問號就有拉直的希望。我常常想,錢校長的教育思想,對破解大學教育的困境,有哪些啟迪呢?
錢校長曾經講過一段話:我們培養的學生首先應該是一個全面的人,一個有文化藝術修養、道德品質高尚、心靈美好的人;其次,他才是一個擁有學科專業知識的人,一個工程師、專門家。他認為大學教育的目標,是培養能獨自到未知領域去工作的人才。這種人才最重要的素質就是有創造力和創新精神,而要有這種素質,就要學會自學。
這段話勾起我留學時代的一個困惑:美國學生入學時,數學水平普遍不如中國學生,為什么最有創造力的人才卻更多集中在美國?現在想來,我們的大學側重專業知識的傳授,教師注重教什么,忽視了怎么教,其實很多所謂的知識是與時代脫節,與實際需要脫節的。而美國的大學在怎么教中解決了教什么的問題,因此對學生側重于學習等各方面能力的培養,只要掌握了方法,學生可以終身學習。后者顯然更善于培養“能獨自到未知領域去工作的人才”。即便從教育主管部門提出的口號中,也可見中美教育差距甚大——我們常提“終身教育”,而美國提倡的是“終身學習”。
我的目光所及,一流的大學有一些共同特征,比如,學生有機會獲得最好老師的指導,自學成為追求和時尚;學生有機會接觸最新成就、前沿學術和科學方法;通識教育與專業教育并重;以學生為本,自由選課,完全學分制,運行制度多樣化,多種人才培養模式共存并良性競爭;學校高度國際化,生源多樣性,思想多元化;學校具有良好的批判性的創新氛圍,不迷信權威,追求真理是師生共同追求的價值取向等等。這些特征,無不是為了培養學生的學習能力而形成的。
我有一些同學、朋友和學生,大學畢業后出國留學,后來留在國外工作。他們在學術領域發展得很好,但還未有人在國外的大學里擔任校長,連擔任學院院長的也極少見。他們自認為這與之前接受的教育不無關系:一個人能走多遠,決定因素往往不是專業知識,而是他受過的通識教育。
今年招生時,上海大學有一個很大的變化:招生不分專業,只分成三大類:理工、人文社科和經濟管理。學生入校后一年內也不分專業,接受通識教育和基礎課程教育。學校鼓勵名教授們給一年級學生上研討課,講他們最熟悉的東西或正在思考的東西,鼓勵他們小題大做,和學生進行開放式和探究式的學習。我們不要求教師給新生一個答案,而要讓他們學會獨立思考。
教師的考核機制、學校的行政管理乃至基礎設施,也要為這個目標服務。我們準備在三大類里開三個試點班,以讀書班的形式學習。新生不分院系,在住處構建社區學院,為他們提供服務。甚至連教室里的課桌椅,也要從固定在地面上的形式,擺放成圓桌形式。
上海提出過大學教育的發展主題:“為了每一個學生的終身發展”,錢校長則說,“我們的學生畢業的時候,如能帶著‘一肚皮問題離開學校,那我們的教育就成功了”,說的都是這個意思。大學教育只有圍繞“培養學習能力”這個核心展開,才有可能回答“錢學森之問”,破解“朱清時之困”。(作者為上海大學教授、副校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