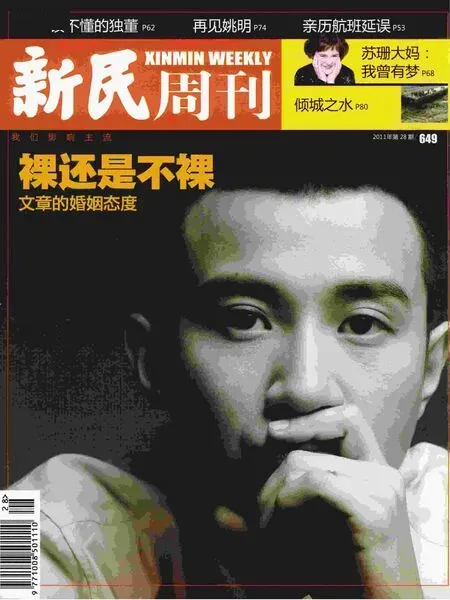潑濕歐洲的一團水墨云
沈嘉祿


旅歐畫家姚逸之最近回到故鄉上海,趁美術界慶祝建黨90周年之際重審一次70年代以來主流美術的面貌,在參觀了好幾個畫展后若有所思地對我說:所謂經典作品不是由畫家吹成的,而是要靠時間來證明。紅色題材的作品今天來看仍然涌動著激動人心的力量,除題材本身的崇高與厚重外,還要靠畫家的時代意識與扎實的基本功。中國的繪畫經過改革開放30年以來對西方美術的主動吸納,已經喚醒了現代意識,但要真正通向世界藝術的堂奧,尋找更廣大知音,還須更多的語匯。比較難的一點不在技術層面,而是在擴大影響的同時,要努力去消弭負面的東西。
那么,什么是“負面的東西”?姚逸之略作沉思后慎重表示:“在這30年里,不少代表中國文化的書畫展覽在歐洲亮相,但并非一流水平,平庸之作很多,也很容易被西方人士誤讀成草率與輕狂。國內有些報道也不盡準確,記者不懂,光聽畫家自己吹得天花亂墜,將外國人的客套話當作真實的評價。其實國外的報道有時是聰明的,只作客觀報道,不作任何導向性的評價,但給的篇幅也不小,這陣勢嚇嚇外行倒很能奏效。那么再加上國內一報道后,有些人就以為是真的了。這對中國文化的傳播是有殺傷力的,也可能對國內正在成長的青年藝術家產生誤導。”
姚逸之有這個資格說這番警世之語。但這種消弭并非某個畫家個人之力可能完成的。不過姚逸之的話也道出了一個令人尷尬的事實。大江東去,難免泥沙俱下。閃光的倒是留在沙灘上的貝殼,里面有珍珠。
他的創作歷程與不少畫家相仿,插過隊,吃過苦,憑借著天賦,以業余身份殺進擁擠的畫壇。他曾被借調到江西人民出版社任美術創作人員,同陳丹青一起搞連環畫創作,這為他日后成為一名畫家打下了扎實的基礎。海晏河清之際,全國恢復高考,他敏感地發現機會來了,遂以優異成績考入上海師大藝術系。此時,他向上海多位大師叩學,比如程十發先生對他就提攜有加。畢業后,他精心創作的佳作獲得美術界的好評,他的作品曾獲上海美展創作一等獎和二等獎,還有作品入選全國美展,在當時,這個初生之犢很是讓同行吃驚的,于是很快成為美協會員。1991年,姚逸之揮別故土,去比利時留學。說起比利時,中國美術界是懷有敬意的,在中國第一批油畫家的簡歷中,可以經常看到這個國家的影響,不少負笈比利時的畫家歸國后,在草創的美術學院中擔任西方美術的忠實信使。
姚逸之在比利時國家高級美術研究院攻讀碩士學位,不久使獲得這個學院的藝術家大獎,這也是華裔學生唯一得到的殊榮。
姚逸之對記者說:二戰以后的歐洲美術界,各種思潮與流派此伏彼起,交相輝映,織就了一部絢麗多彩的當代美術畫卷。但是也應該看到,西方美術驕子對傳統技法的遺棄決心過于堅決,對當代藝術的各種新手段過于迷戀,藝術市場及媒介宣傳的選擇過于偏執,那么他們就似乎有了輕視技巧的理由。
事實上,西方哲學中的弒父命題在當代藝術中表現為更強烈的反叛實踐,那么在歐洲吮吸狼奶的中國藝術家,倒可能在空白處留下東方的色彩與思考。不過姚逸之沒有用油畫證明這一點生存之道,他選擇了獨具中國精神的水墨。他憑借豐富的中國精神與中國風格,手執毛筆,給西方美術注入了東方的墨韻,使許多老外從墨暈與線條中重新評價中國人的語言與思維。
近年來,姚逸之在作為歐洲美術重地的意大利、法國、比利時、荷蘭等國舉辦的個展很多,獲得的榮譽也不少,比如20世紀亞太藝術大賽銅獎、美國亞太藝術研究院的20世紀貢獻獎勛章、歐洲功勛藝術家協會最佳作品獎等。但他最難忘的倒是與老師程十發在比利時舉辦的師生展,他以這種方式向外界表明他是尊重傳統的。
老外是服他的。現在歐盟許多著名政要和博物館、藝術機構都收藏了姚逸之的作品。比利時報紙稱他是“閃耀著藍鉆石光芒的東方藝術家”,具體的點評也是很到位的。藍寶石的光芒,應該就是水墨在藍眼睛中的光澤吧。難怪中國美協主席劉大為先生在歐盟看到姚逸之的作品極為贊賞地說:畫家是用情在潑,用心在畫,大山大水,云霧縹緲,有開有合,天地合一。劉大為還認為姚逸之的作品極富有空間感和立體感,給人強烈的視覺沖擊力和心靈的震撼力,并邀請他回國和藝術界的同行多交流新的創作理念。
在國內,他的知名度也有點出口轉內銷的味道,越來越響,他應北京釣魚臺國賓館之請創作了好幾幅巨作。2006年他回上海,在劉海粟美術館辦過個展,不少觀眾從他的作品中看到了中國水墨畫在歐洲恣意潑灑的可能性。
姚逸之的作品若以純技術的角度分析,離傳統并不遙遠,是屬于大寫意一路,但基本的形象是立得住的,接近于無標題音樂的境界。他的作品看似隨意性很強,但有其內在的思想邏輯與表現層次,背后有深厚的中國傳統文化支撐。他筆下的水墨暈染,層次非常豐富,流動感極強。他的水墨沒有色彩,用墨分五色來比喻恐怕也不夠窮盡,老外看出的色彩是超過數碼相機的。他畫的人體也體現了自己的風格及中國水墨神韻,骨骼與肌肉都取沒骨畫的方法,但有一種黑白照片時代負片的感覺,飽滿而具有張力,深受西方藝術界的認可,其作品在歐洲市場廣受好評,足以體現畫家自身在歐洲藝術界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