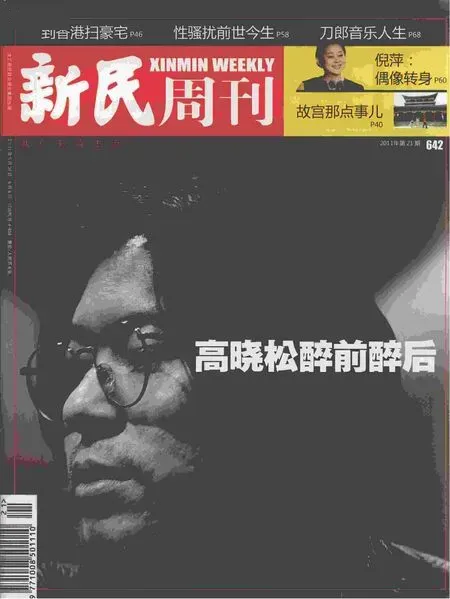特供那點事
沈嘉祿
前幾天趕一飯局,喝茅臺——等級號稱特供,但入口后特沖。有個樣樣都懂得一點的爺說:群眾都知道,茅臺有特供,但特供的口味并非最佳。何也?因為做假酒的知道有人好這一口,而且喝起來直接灌進胃里,酒再好也是大江東去,故而閉著眼睛大量勾兌。
一幫吃貨面面相覷,頻頻點頭,低頭夾菜。
最近,《南方周末》有一篇文章將特供話題再次挑起,群眾議論頗多。我兒時雖然懵懂,也知道特供這檔事。比如在四川北路上就有一家副食品店,門楣上用紅漆涂著“特供”二字。牛肉絕對血淋帶滴,龍蝦個兒倍大,營業員對路人惡聲惡氣賽過鎮關西。在物資供應匱乏的年代,特供二字具有無比強“撼”的象征意義,群眾只有一邊仰觀一邊咂嘴的份。那時候群眾的覺悟就這樣,認為生活待遇上,官家與草民、家奴與外賊就該有區別,否則偉大領袖在三年困難時期表示不吃肉,億萬群眾在傳頌時熱淚盈眶,就不好理解了。
特供在某種情況下,動靜還相當大。說個故事,上世紀70年代初,中國人民的老朋友西哈努克親王外出訪問時家里被人搞了政變,走投無路時中國政府叫他回家吃飯,還安排他四處走走,參觀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成果。親王來上海,在城隍廟吃飯,由南市區飲食公司操辦。我有個朋友是親歷者,據他回憶:“工作人員都要事先政審過,民兵在廚房里人盯人,防止壞人投毒。我是做點心的,芝麻、瓜仁要一粒粒揀過,還有一道雞鴨血湯,師傅三下南翔才找到正宗的本地草雞。這個雞卵是附著在腸子里沒有形成雞蛋的卵,才黃豆那么大小,配玉白色的雞腸和深紅色的雞血,賞心悅目。但不是每只雞都有,開膛一看,沒有,這只雞就白犧牲了。總共殺了多少?傳說是108只。但是當天親王跟莫尼克公主打網球,打到興起不來了,第二天再啟駕。為了這碗湯,又大開殺戒。”
從這碗雞鴨血湯可以想象中國一般情況下的特供是如何操作的,享受者又有何種感覺。如果說親王一餐關涉外交,在亂云飛渡之中體現了三個世界劃分的大局觀,那么在推行市場經濟的今天,特供衍變為可計價的商品,有錢人嘯聚于廳堂之上圖一時之快、顯一時之威,比清末花錢捐個候補道臺還便宜。再從民間話語考察,中國人對特供性質的“規定動作”總津津樂道,商家以此為廣告宣傳的用意居然也“瓜瓞綿綿”。今天連一瓶醬瓜、一盒豆酥糖上也會寫上“貢品”二字,編排出慈禧太后金口品嘗的軼聞趣事,表示特供歷史悠久。那么老佛爺吃得,我等也可吃得。理解了這個背景,從賓館的總統套房,到建福宮的會所,似乎就水到渠成了。其實市場經濟啟動后,神州大地上很多國賓館就對社會開放了,比如釣魚臺、劉莊、從化溫泉等。杭州劉莊一號樓是毛澤東當年下榻之處,留有遺物甚多,前些日子裝修,毛澤東用過的東西一古腦兒搬到康山一亭子里。我對遺物與環境分離的做法提出異議,管理方回答非常坦然:活人比死人重要!
現在群眾又發現:北京順義設有特供蔬菜基地,圍墻和鐵柵欄環繞,保安站崗,俗稱“海關大棚”,而且各省市也都在前些年辟建了特供食品基地。我個人對特供比較理解,有關方面為確保領導身體健康、中樞機關正常運轉而實行特供無可厚非,同時我也像老百姓一樣夢想能吃到接近特供水平的食品。但有個問題想不明白,領導在享受特供時,費用怎么算?如果按生產成本加商業利潤核價的話,估計也會心疼吧。我在某區政府食堂蹭過幾次飯,量足質佳,收費撐死也就七八元,有天然鮮香味的蔬果來自郊區某農業基地,這是20年前政府為解決市民吃菜難而興建的菜籃子工程項目。朋友說:“區政府是有補貼的,當公務員也就這點好處吧。”
香港大概是沒有特供這一說的,前幾天公布公務宴請的菜單,公務宴請一般六道菜,人均消費450元封頂,吃不完打包。我還聽說,首任特首董建華來上海公干,常去徐家匯附近一家小飯店打牙祭,對麻醬腰片、糖醋小排等贊不絕口。后來董太每次來上海也要專程去這家店大快朵頤,并買多一份回香港讓夫君解饞,所幸沒叫董特首拉肚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