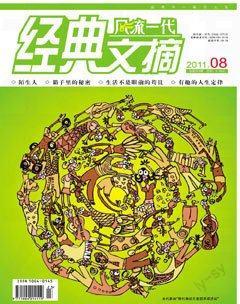箱子里的秘密
2011-05-30 10:48:04王鼎鈞
風流一代·經典文摘
2011年8期
關鍵詞:上海
王鼎鈞
大約在我出生前一年,父親到上海謀職。當時上海由一位軍閥占據,經人推薦,父親做了那個軍閥的秘書。
那時上海是中國第一大埠,是謀職者心目中的金礦寶山,父親能到那里弄得一官半職,鄉人無不稱羨。可是,據說,父親離家兩年并沒有許多款項匯回來,使祖父和繼祖母非常失望。
大約在我出生后一年,那位軍閥被國民革命軍擊敗,父親在亂軍之中倉皇回家,手里提著一只箱子。這只箱子是他僅有的“宦囊”。
箱子雖小,顯然沉重,鄉人紛紛議論,認為這只隨身攜帶的箱子里一定是金條,甚或是珠寶。上海不是個尋常的地方啊,伸手往黃浦江里撈一下抓上來的不是魚是銀子。鄉下小販兜售的餅干,原是上海人拉出來的大便!
可是,我家的經濟情形并沒有改善,依然“緊張”,遣走使女賣掉騾子,把靠近街面的房子租給人家做生意。鄉人駐足引頸看不到精彩的場面,也就漸漸地把那只手提箱忘記了。
我初小結業,升入高小。美術老師教我們畫水彩,我得在既有的文具之外增添顏料和畫圖紙。這時,父親從床底下把那只箱子拿出來。箱子細致潤澤,顯然是上等的牛皮。
他把箱子打開。
箱子里全是上等的白紙!
那時候我們使用兩種紙,一種叫毛邊紙,米黃色,纖維松軟,只能用毛筆寫字;還有一種就是今天的白報紙,那時叫新聞紙,光滑細密,可以使用鋼筆或鉛筆。那時,“新聞紙”已經是我們的奢侈品。
父親從箱子里拿出的紙是另一番模樣:顏色像雪,質地像瓷,甩手撫摸的感覺像皮,用手提著一張紙在空氣中抖動,聲音像銅。……
登錄APP查看全文
猜你喜歡
國家教育行政學院學報(2022年9期)2022-10-10 10:02:28
散文詩(2021年24期)2021-12-05 09:11:54
環境衛生工程(2021年5期)2021-11-20 05:45:36
少先隊活動(2021年5期)2021-07-22 09:00:02
環境衛生工程(2021年3期)2021-07-21 05:34:40
環境衛生工程(2021年2期)2021-06-09 09:11:16
家庭影院技術(2020年11期)2020-12-28 01:22:42
上海質量(2019年8期)2019-11-16 08:47:12
小主人報(2018年24期)2018-12-13 14:13:50
電器工業(2017年1期)2017-04-11 10:00: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