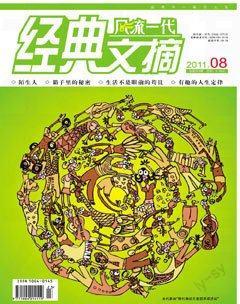從蟻到神
2011-05-30 16:28:06高緯
風流一代·經典文摘
2011年8期
關鍵詞:想象力
高緯
女作家尚德蘭曾經給詩人顧城當過法文翻譯。她曾回憶當年的顧城:那是1993年的一天,顧城給她寫了兩幅字,一幅是“魚在盤子里想家”;另一幅是“人可生如蟻而美如神”。尚德蘭回憶說,那天下午,詩人顧城先是在廚房里磨了很長時間刀,那專心致志的樣子令人發怵。他給尚德蘭寫這兩幅字時,情緒激動;寫完了,如釋重負……一年之后,詩人顧城自殺了。
看過一個外國電影:一個干壞事進了監獄的男人,在監獄里,他和獄長一起看電視。電視上正播放著懸賞百萬尋找救人英雄的一個新聞節目,男人對獄長說,那個人就是我啊。獄長給了他一耳光,說,若你是英雄,那么這里的每個人都是總統——事實上,電視上尋找的那個英雄真的是這個犯人,他救了好多人,但是卻盜用了其中三個被救之人的信用卡去買了東西,他因此而進了監獄。影評家王書亞曾說,“一個人的美德并非是他英雄行為的動機,一個人的卑微也不是他錯誤的必然根源。”
從蟻到神,這其中需要多大的想象力?
我時常把自己的靈魂撤離出來,看著具象的我。我自己就是一個排。她們列隊站著:女人;母親;妻子;寫詩的我;社會的我;人群中的我;會場我;私下我;好我;壞我;小我;大我;統一我;分裂我;外在我;內在我……是的,我自己就是一個排,從蟻到神。我紛紛出場,在不同的場合,出現在不同的崗位。更多的時候我必須戴對面具,不然我就會把生活之戲演砸了。我不知道命運將在哪個拐角處使用哪一個我?
登錄APP查看全文
猜你喜歡
小學生優秀作文(低年級)(2021年6期)2021-07-17 09:22:08
少兒美術(2020年6期)2020-12-06 07:37:22
傳媒評論(2019年5期)2019-08-30 03:50:04
少年漫畫(藝術創想)(2019年1期)2019-05-09 03:13:22
中國記者(2014年6期)2014-03-01 01:39:50
七彩語文·低年級(2012年19期)2012-04-12 00:00:00
課外生活(小學1-3年級)(2010年23期)2010-12-31 00:00:00
中學生博覽·文藝憩(2009年6期)2009-07-23 01:48:18
百科知識(2009年4期)2009-03-07 03:07: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