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當代小說流變史》:缺乏誠意之作
○張羽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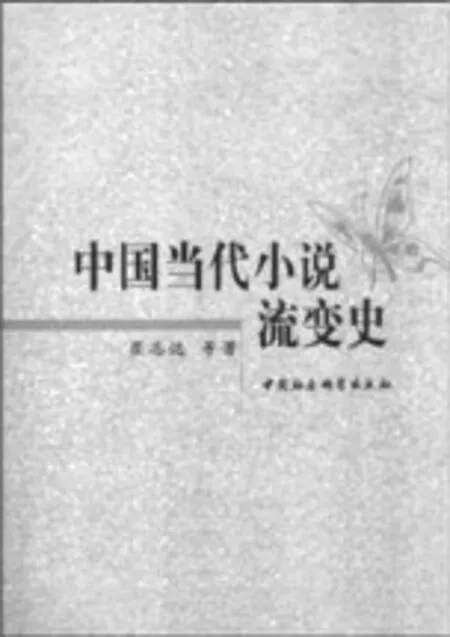
《中國當代小說流變史》,崔志遠著,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年版
閱讀是當今社會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隨著媒介文化的發展和傳播,圖像時代已進入我們的視野,紙質文本正在讓位于電子文本,但并不意味著紙質文本就要被消滅,相反,紙質文本也正在與以電子傳播媒介的較量中維系著自己的市場份額和讀者心目中的閱讀期待。紙質文本的裝幀質量以及編輯者所體現出的編輯素養和文本透視出來的藝術質地就顯得尤其重要。這也就要求著書者以及編輯者付出巨大的勞動和責任,當然也更承擔批評的風險。
我曾拜讀了崔志遠的不少專著,從中受益匪淺。近日又拜讀了崔先生和他的學生共同完成的專著《中國當代小說流變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年版),我想在此負責任地探討和診斷一番該著作的藝術價值。
王慶生在該書序言中說:
總的來說,《中國當代小說流變史》是一部主旨鮮明、視野開闊的書,也是內容翔實、頗富有創意的書。為了寫好這部書,崔志遠教授艱苦跋涉,鍥而不舍,傾注了自己的心血。僅從書中引用的資料來看,理論著作有一百多種,涉及的作家作品就更多。著者不僅要占有這些資料,還要從眾多的資料中爬梳搜求,梳理辨析,去粗取精,去偽存真。這些都非一日之功,它是著者長期積累、縝密思考的結果,體現了潛心治學、嚴謹求實的學術精神。我認為,這種學習精神不僅值得我們學習,而且需要大力提倡,特別是在當今浮躁之風盛行,功利化、物欲化影響文壇的“文學娛樂化”時代,更需要呼喚和弘揚這種“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做半句空”的嚴謹治學精神。
此話雖言過其實,但也透露出這部著作的實在之處。實際上我對這部著作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并不感興趣,一些陳舊的理論闡釋、背景資料的繁述和史料的堆積顯得異常僵化和生硬,沒有能很好地整合,然而更讓我失望的是在這部《中國當代小說流變史》中,正因為“僅從書中引用的資料來看,理論著作有一百多種,涉及的作家作品就更多”,造成了作者的竊喜過甚和編輯者惶惑不安心態,才出現書中的很多低級性錯誤。首先我要說明的是,我并不是故意在書中挑出這些錯誤,我始終是抱著學習求知的態度來拜讀這部大作的,之所以要在這里指出所發現的錯誤,是感嘆于當前學術界、編輯者對讀者那份無形的羞辱和欺騙。一本定價42元的書應該說是值得掂量的,這里花錢不說,還浪費了讀者時間、眼神和思緒。說實在話,這些很常識性的錯誤出現在著述頗豐資歷深厚的教授和資深的出版社編輯的手里實在難以想象。為此,我把值得商榷的地方標明如下:
在該書的第93頁引用了一段話:
他們的戀愛是不談戀愛的戀愛,是崇高的戀愛。她不是以一個美貌的姑娘身份跟蕭長春談戀愛,也不是用自己的嬌柔微笑來得到蕭長春的愛情;而是以一個同志,一個革命事業的助手,在跟蕭長春共同為東山塢的社會主義事業奮斗的同時,讓愛情的果實自然而然地生長和成熟……(周立波《山鄉巨變》)
這段話明顯是引自由北京華齡出版社于1995年出版的浩然長篇小說《艷陽天》第一部的第433頁和434頁,并且在引用段落的第一句話前面還有一句“他們開始戀愛了”。
在該書第122、123、143頁分別提到戴厚英的長篇小說《人啊,人!》,而前兩處標的是《人啊,人》,后一處是《人啊!人》,標號顯然不合乎原著。
該書第131頁原文是:張一弓《魯班的子孫》,而實際上《魯班的子孫》的作者是王潤滋;第35頁,把李準短篇小說《不能走那條路》寫成《不能走哪條路》,“那”和“哪”不分;第37頁,把現代作家李劼人寫成“李頡人”,第270頁第三行,把“王宏圖”寫成“于宏圖”,竟然把姓氏寫錯了。
在附錄綜論茅盾文學獎部分,第320頁和第321頁兩處分別是這樣表述的:
除了《抉擇》外,其他三部作品均顯現了濃厚的地域文化色彩。《長恨歌》中國際大都會上海的繁華溫柔,《塵埃落定》中邊遠西藏的廣袤神秘,《茶人三部曲》里杭州水鄉的流水茶香,都在著意描寫特定地域文化熏染下的人物命運。
《塵埃落定》不僅大量展現了西藏的風土人情,還展現了一種與現代生活完全相反的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它與自然更為接近,充斥了對神而不是對科學的信仰。
我想,只要看過阿來這部小說的讀者,都不會說故事發生地點是西藏。
另外在該書中,我個人覺得還有一些尚需商榷之處就是引文出處的明確問題。比如,在引論的第3頁論述“‘悲涼’的現代美感特征”時,談到:
悲涼的美感意識常包裹兩種不同的色彩:理想化的激昂和冷峻的嘲諷。前者著眼于民族的新生的輝煌遠景,如郭沫若的《女神》;后者著眼于民族靈魂再造的艱巨任務,如魯迅的《吶喊》、《彷徨》。
而后面緊接著引用的一句話作為段落結尾:
也有這樣的歷史時刻,那是冷嘲被“激昂化”而變成一種熱諷,激昂被“冷嘲化”而變成一種感傷,于是兩者相互削弱、沖淡,使得一種嚴肅板正的“正劇意識”浮現出來成為美感色彩的主導。
從兩段的話語前后銜接來看,后一句話顯得狗尾續貂,同時也并沒有標明引用的出處,像這種例子書中不止一處。另外在第169頁第四個注釋沒有注明“是傳統文化的丑陋性、原始性與老而不死的象征”這句話在王鐵仙等《新時期文學二十年》的具體頁碼。在第215頁第二段的最后一句引文出處的注釋沒有寫明引用文章作者和該文題目,正確為:童慶炳、陶東風:《人文關懷與歷史理性的缺失——“新現實主義小說”再評價》,《文學評論》1998年第4期。還有從第266頁到272頁引用的所有期刊出處沒有標明具體是哪一期,而是寫出年月,但是標出的時間也是錯誤的。以第270頁第一個注釋為例:原引文為“謝有順:《奢侈的話語——‘文學新人類’叢書序》,《南方文壇》1999年5月”。我查閱了這篇文章,結果作者完成這篇文章的落款日期是:1999年7月4日。因此,正確的應是:謝有順:《奢侈的話語——‘文學新人類’叢書序》,《南方文壇》1999年第5期。
在時間的書寫上也比較模糊,顯得不夠規范,如“20世紀40年代末至70年代末”、“20世紀70年代末至80年代前期”、“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20世紀90年代以來”、“20世紀40年代”、“20世紀80年代初”、“20世紀八九十年代”等。
另外還有邏輯的連貫性問題,比如在這本書的第123頁倒數第二段寫到“此間,一些非歷史的純粹的感情追求不免出現偏頗,《妙清》(李英儒)、《人啊,人》就激起了討論和批評”,照理說,在“《人啊,人》”后面應該注明作者(戴厚英)。在第37頁第一段第8、9行,認為楊沫的長篇小說《青春之歌》表現土地革命戰爭也值得商榷。
在第162到163頁中,有一段話:
尋根小說還是改革小說的深化。改革小說由蔣子龍模式發展為高曉聲模式,作家關注的現實由改革英雄面對的“外障”轉變為自己的“心魔”,改革的障礙并非站在對立面的幾個反對者,而是漫長的農業社會形成的廣大民眾的集體無意識,如高曉聲“陳奐生系列小說”揭示的皇權意識,《魯班的子孫》開掘的傳統義利觀,《人生》揭示的安土重遷意識等,如此,面對現實的改革小說卻與面對過去的民族文化心理的開掘奇妙地結合在一起。
我們很明顯看到“尋根小說還是改革小說的深化”是一句病句,亂用關聯詞,說高曉聲“陳奐生系列小說”揭示的皇權意識,未免肯定,還有在高曉聲“陳奐生系列小說”后面所舉的兩部著作“《魯班的子孫》、《人生》”,到底是高曉聲所作還是分別為王潤滋和路遙所作?從句法上講未免引起歧義。
作為讀者,很有必要對文學文本認真深入閱讀,作出必要的審美和癥候式剖析,但作為該書的編寫者和編輯部的編輯者,更應該對讀者負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