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無對證
一
一大早,趙心亮就把卡車從車隊開出來,停靠在工廠大門的一側等著我。正是早上七點半鐘上班的高峰期,一群又一群職工匆匆忙忙地朝著工廠大門走過來,有一眼無一眼地沖著卡車亂瞅著。趙心亮沒有心情與熟人打招呼,上身趴在方向盤上裝睡覺。這是一輛解放牌卡車,顯得很破舊,泥頭爛腦,車頭一團黑,車廂一團黑,四只車輪更是一團黑。我遠遠地看見這么一輛破卡車,心里猛然地一“咯噔”,預感到這趟差不會太順利,最起碼卡車在半路上拋錨是正常的。趙心亮說他是個老司機,莫說一輛卡車,就是一輛架子車都能在馬路上開著跑。趙心亮的修車技術在車隊是數一數二的,要不然車隊也不敢派他開著這輛破車出這趟差。我拉開車門,一屁股坐在副駕駛位置上說,趙師傅,我倆走吧!趙心亮不說話,伸手擺弄車檔、油門什么的,日輪,日輪輪,日輪輪輪,發動機一聲怪叫接著一聲怪叫,就是不能正常運轉。趙心亮丟失顏面,破口大罵卡車,像是罵一頭犟驢,你說你個小舅子的干活不干活?你說你個小舅子的上套不上套?就是這么一聲罵,發動機“日輪”一聲正常工作起來。趙心亮得意地瞟我一眼,點上一根香煙,狠勁地猛吸一大口,輕輕地噴出一團煙霧,掛上車檔,踩下油門,卡車哐里哐當,晃里晃蕩,醉漢一般向著大門外面的公路跑過去。
我倆此行的目的地是省第三監獄。我倆此行的任務是接黑頭。黑頭是一名刑滿釋放的勞改犯。
說起來,去監獄接黑頭跟我倆一點相干都沒有。趙心亮是廠車隊的一名維修工,我是廠團委的一名干事,都是與黑頭非親非故的。黑頭出獄,他的家人去接,或者街道居委會去接,就算落實到廠子里,還有廠里的保衛科,偏偏老宋一手把這件事攬過來。老宋是廠團委書記,我的頂頭上司。俗話說,名不正則言不順。老宋向我派遣這份工作的時候,說話有些結巴,理由有些勉強。老宋說,黑頭以前是團員,我們不去接、接、接誰去接?我覺得可笑,心里想一名勞改釋放犯不要說以前是團員,就是黨員,也早被開除啦?我大學畢業分廠團委工作一年,知道老宋經常去黑頭家。黑頭父親早些年在礦上出事故死去,家里只剩下黑頭母親一個人。老太太年歲不大,身體卻不太好。老宋去做一些老太太做不了的重活。聽人說,老宋家跟黑頭家是老鄰居,他倆起小一塊長大。這么一分析,接黑頭跟廠團委也是沒關系。可老宋偏要當作廠團委的一項工作去處理。
前一天下午,老宋領著我一起去車隊找車子。隊長王懷禮一聽說老宋去找車也是很詫異,問老宋,你怎么會想到來車隊要車呀?老宋說,我總不能找廠長要小車吧?王隊長苦笑一下說,黑頭那是不夠這個檔次。監獄離廠子一百多里路,在一片山窩里,不通長途車,不去車子接,黑頭自己哪能走出來。趙心亮正好在車隊修理這輛破舊的解放牌卡車。王隊長就把出車的任務交給他。趙心亮也是不樂意接受,說車子下午修不好。王隊長說,下午修不好,你連夜修。趙心亮問,不能派別人的車?王隊長說,其他車出去拉貨晚上回不來。趙心亮說,這輛破車怕是跑不了這么遠的路。王隊長說,壞半路你修好接著跑。其實我能看出來,王隊長同意派車,趙心亮最后不得不出車,都不是看老宋的臉面。黑頭原先就是車隊的維修工,因為盜竊輪胎而趕上“嚴打”被判刑五年,刑滿三年提前釋放出來。王隊長、趙心亮聽說黑頭出獄,一點驚訝的表情都沒有,這說明他們倆也是知道黑頭出獄這件事。老宋跟趙心亮說,明天早上曹干事陪著你一起去。趙心亮問老宋,你不去?老宋說,明天上午我要去市里開會。其實老宋不想去接黑頭,說開會是一句托辭。趙心亮看了我一眼,嗡聲嗡氣地說,明天早上七點半鐘我在廠門口候著你。
在這里需要特別地交代一下這部小說的時代背景。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期,公檢法聯手在全國范圍內進行過“嚴打”活動。所謂嚴打,就是從重從快地打擊各種刑事犯罪分子,拉網式的,地毯式的,迅速集結上百萬人發配到新疆、內蒙古等邊遠地區的監獄里。黑頭因偷盜車隊的輪胎,受到過廠里處理,遇上嚴打重新處分坐牢。跟別人相比,黑頭留在省內監獄服刑,已經是不幸中的萬幸了。邊遠地區環境惡劣,不少犯人活著去,死著歸,一把骨灰都不知道拋撒在哪里。黑頭是個怎樣的人物,我很想去了解。一路上,趙心亮一句話不說,像個啞巴。我感到老宋、王懷禮、趙心亮他們三個人像是共同保守著一個秘密。這個秘密是屬于黑頭的,也是屬于他們大家的,只是我一點也不知道。
我問趙心亮,黑頭原先跟你在一起修車嗎?
趙心亮不搭理我,卻是拼命地開車。
我問趙心亮,黑頭偷幾只輪胎被判刑五年呀?
趙心亮依舊不搭理我,卻把車速調到最高,油門踩到最大。
路面狹窄,坑洼不平,卡車一路吼叫,一路狂奔,一路蹦跳,發動機像是要爆炸,車廂像是要散架。我倆像是一對被別人追趕著的亡命徒。
我說趙心亮,你不說話沒關系,也沒必要把卡車開得這么快嘛。
趙心亮總算說出一句話,——早去早回!
原來需要兩個半小時的車程,不到兩個小時就到了。藍天與白云,晴空與太陽,高墻與電網,哨兵與槍支,犯人與鐐銬,逃跑與死亡。我站在藍天下高墻外,鐵門前,除去聯想這些與監獄有關或無關的詞匯,高墻里面的什么情況都是看不見。四周空曠而安靜。氣氛陰森而恐懼。相對一個外人來說,監獄原本就是一個不能親眼看透的地方,原本就是一個不能親身體驗的地方。趙心亮留在卡車上,我手里拿著單位介紹信去找監獄值班室。那年月,人們外出做任何事情,都要挾帶一張單位介紹信,證明你的身份,說明你此行的目的。一個姓賈的監獄管理干部接待我。他說,你們單位一個姓宋的團委書記已經打來過電話。我說,那就不用我多說了,要是馬建軍辦理好出獄手續,我們現在就帶他回去。馬建軍是黑頭的名字。

盧西安·弗羅依德作品-1
賈干部說,83085號自己走了。
在監獄里每個犯人都有一個代號。馬建軍的代號是83085號。
我急忙問,有出山的車子嗎?
賈干部說,83085號自己步行回去。
我問,你沒跟他說我們來車接他嗎?
賈干部說,83085號說他不想麻煩你們,我打電話去你們單位,你們的卡車已經來了。
一般情況下,犯人出獄都是自己走出,翻上幾座山,走上四十里山路,有一個鎮子。鎮子上有長途汽車路過。賈干部五十來歲,穿一身藍色制服,說話很隨和,不像我想象中“橫眉立眼”的監獄管教干部。
賈干部說,單位派車來接出獄人員,我工作這些年還是第一次遇見。
我說,我也是第一次帶車來接出獄人員。
我想黑頭肯定是一個特例,單位不可能派車來接每一個刑滿釋放人員。
賈干部進一步介紹說,83085號在服刑期間表現比較好,一個人能干兩個人的活,刑滿后想留下來,沒想到上面今年批的名額少,沒有他。
犯人表現好,刑滿后繼續留在監獄工作,一方面是監獄離不開這個人,另一方面這個人也算暫時有了一條就業門路。黑頭在監獄里表現好,想減刑,想留下來。黑頭為什么不想回家呢?
賈干部繼續說,一個年輕人留在這里還是不能算做一個事情,我聽說他就一個老娘在家里?賈干部說話有些假腔假調的。
我點頭說,他母親身體不好需要他回去。
賈干部說,回去請轉告你們單位領導,要多多關照83085號。

盧西安·弗羅依德作品-2
我打一句官腔說,我們會盡量地關照他。
回頭的時候,卡車出現異常,任憑趙心亮怎么擺弄,發動機就是運轉不起來。卡車異常的原因出在趙心亮身上。我看見趙心亮神色不安,一頭大汗,想點燃一根香煙,火柴在手上顫抖半天就是擦不著火。黑頭為什么不坐廠里的車子呢?黑頭知道開車來接他的是趙心亮嗎?突然,趙心亮丟下手里的火柴香煙,丟下手里的油門鑰匙。有那么兩分鐘,趙心亮兩眼空洞洞的,呆愣愣的,什么也不去做,像一條晾曬在河岸的干魚。我知道趙心亮是個懶刺頭,也就不去亂說話,耐心地坐在一旁等候著。反正不用接黑頭,晚點回去就晚點回去吧。沒想到趙心亮會跟我說,曹干事你去打一個電話,讓老宋跟車隊說一聲,派一輛車把這輛車拖回去。一百多里路,就是車隊派車也得兩個小時吧。我問,車子不能修理啦?趙心亮說,修不好。我說,你不修怎么知道修不好?趙心亮說,這輛破車我已經修三天啦。
說來真是趕上了,車隊沒有一輛閑下來的車輛。老宋回電話說,你跟趙心亮就呆在那里等著吧,車隊什么時候有車什么時候去接你們。我從監獄值班室打過電話回頭來,趙心亮竟然趴在方向盤上睡著了,鼾聲如雷,像是卡車發動機已經正常運轉起來。
難道趙心亮昨天晚上一夜沒有睡覺?
二
真正見到黑頭是半個月過后。
黑頭出獄有意無意地影響了老宋的生活,也影響了老宋的情緒。原先老宋每天上班都要從黑頭家打一頭,看一看老太太有沒有什么事情需要做一做。要是需要買個米,買個面,買個蜂窩煤什么的老宋下班先去街上買到手,而后再去黑頭家。黑頭娘沒工作,黑頭大(爸)是工傷,廠里按月支付黑頭娘生活費。要是不夠花,老宋也貼補一點。比如說買油五塊錢,老宋說三塊錢;買米十塊錢,老宋說八塊錢。那時候工資低,老宋想貼補多也拿不出。好在老宋是單身沒成家,父母不需要他養活,一個人的工資一個人花。老宋年歲不大,剛過三十,可在全市團委系統相對來說,年歲就大了。廠里的一幫團員青年,老宋老宋地喊他有幾年了。老宋跟廠黨委提出,選拔一個更年輕的擔任廠團委書記。廠黨委書記老高說,你小宋才多大年紀呀,接著干兩年再說吧。老高是一個接近退休的老同志,老宋在他面前自然是小宋。我在大學是系團支部書記,廠里安排我去團委工作,有接老宋班的意圖。老宋需要去黑頭家照顧老太太,常常遲到早退,看管辦公室的任務就落在我頭上。我住廠里的單身宿舍,在廠大門外面不遠,更多的時候我連晚上都泡在辦公室,看書學習,跟一群團員青年聊天。老宋與黑頭之間的一些事情,我就是從他們嘴里聽說的。但他們畢竟比老宋小幾歲,不屬于同一個年齡段,只能說一說表皮,想往內里一說,他們也是不知道。
黑頭回來,老宋不用再去照顧黑頭娘。能看出老宋每天坐在辦公室里心不安。更能看出,老宋跟黑頭的關系也不再是哥們了。這一點從老宋派我去監獄接黑頭,黑頭不買老宋賬,就可以看出來。按照道理說,我跟趙心亮去一趟監獄沒接著黑頭,事后其主要產品。總廠下設七個分廠,十幾個黨總支單位,每個黨總支相應地都有團總支。黨總支書記是專職的,是正科級,團總支書記沒級別,是兼職的。陶瓷生產需要的原材料多種多樣,有的是從外地購買,有的自己生產。煤炭與粘土,都有自己的礦井。廠里有三條六七十米長的隧道窯,都是吃煤的煤老虎。窯爐燒起來,幾輛卡車整天不歇息地拉運煤炭才能供應上。粘土是陶瓷生產的主要原料,它是煤炭的伴生物,也就是說扒粘土與扒煤炭差不多,只不過煤炭埋藏在地下深一些,粘土埋藏在地下淺一些。粘土礦、煤礦分散開,屬兩個單位。兩個礦都很遠,煤礦有五里路,粘土礦有十多里路,都不通公交車。往常要去那里,都是他們派車接。兩礦各有一輛客貨兩用車,礦領導上下班使用,外出辦事使用。
我問,粘土礦幾點派車來接我倆?
老宋說,今天我倆騎腳踏車去。
我心虛地問,今天要不要下礦井?
老宋堅定地說,下!
上次檢查團總支工作,他沒下礦井,我也沒下礦井。按照老宋的計劃,這一次我倆由遠及近,先去總廠外的團總支,后去總廠內的團總支。粘土礦最遠,安排在第一站。
兩個礦井都不是好下的。煤礦井深500米,沿45度角的斜井往下走,一個石階連著一個石階,不說別的,下一趟上一趟,都得兩個小時吧。要是沒有下習慣,猛然地下一趟,沒個三五天,腰酸背痛都緩不過來勁。粘土礦淺,四十多米深。正是淺,才改斜井為豎井。光禿禿的一個黑窟窿,一根坑木挨著一根坑木四四方方地券出來,直上直下靠著一只筆直的木梯,老宋應該跟我做一些解釋。因為黑頭不要車子接,老宋接著賈干部電話先知道。要是像現在通訊這樣發達,人人手里都有一部手機,趙心亮我倆就不用跑那么一趟冤枉路。反過頭來說,要是像現在到處都是修車廠,也不用等著車隊去車拖。最起碼我能搭一輛順便車早回頭。那年月,在這么一處地方,墻內是監獄,墻外也跟監獄差不多。我跟趙心亮只好老老實實地呆那里,一直等到晌午后。這期間趙心亮一個勁地睡覺,連晌午飯都不吃。趙心亮不吃晌午飯肚子不餓,我不吃晌午飯肚子“咕咕”地亂叫喚。我去監獄值班室討吃的。賈干部說,83085號虧得沒坐你們的卡車。我說,他要是坐我們的卡車,說不定車子就不會壞了。賈干部說,你們的車子出毛病跟83085號有什么關系呀?我說,肯定有。晚上八點半鐘,車子拖著車子回廠里。廠團委辦公室亮著燈,老宋等著我。我進去,老宋瞟我一眼,算是一種歉意,算是一種問候,一句話沒說欠起身走掉了。
一晃過去半個月。這一天早上,老宋跟我說,從今天起我倆去各個團總支檢查工作。按照年初制定的工作計劃,去各個團總支檢查工作的時間應該是年底。檢查、評比放在一起做,放在年底做,去年就是這樣安排的。老宋突然更改工作計劃,顯然與黑頭從監獄回來有關,顯然與老宋這些天情緒不穩定有關,顯然與老宋上班坐在辦公室里心神不寧、什么都不能做、做什么事都做不好有關。
我問,今天先去哪個單位?
老宋說,粘土礦。

盧西安·弗羅依德作品-3
我們廠是個職工家屬上萬人的大廠,以生產陶瓷產品為主,日用瓷,衛生潔具,釉面磚,耐火磚,是上下井就是從這只木梯爬上爬下的。四十米長的一只木梯,有十三層樓房那么高。這么長的一只木梯,沒有任何保險裝置,礦工整天徒手爬上爬下,肯定存在一定的危險性。這種豎井最原始,人類最初開礦就是這么一點點地掏下去,下到地球深處去。粘土礦的這種原始豎井,下一次,就能牢記一輩子。
去年大學畢業剛分到廠子里,進廠的第一件事就是集中學習,接受廠情廠史教育。其中有一項內容就是下粘土礦,要讓大學生親身體驗,礦工扒上來的每一噸粘土都是多么不容易,更加說明廠里的每一分錢都是來之不易的。老宋帶著我們幾名大學生去粘土礦。老宋說他腳上有傷,不能下井,礦上派幾名年輕礦工帶著我們大學生一起下。老宋說他腳上有傷我不信。我跟他一起待了許多天,沒發現他腳上有毛病。老宋作為領隊沒必要非下井不可,說這話是不想下井。幾個大學生每人領出一套工作服,一雙膠靴,一根皮帶,一頂膠殼帽,一盞礦燈。應該說,上述這些東西就是一個沒下過礦井的人,憑常識也能說出來。跟別的礦井不一樣,在這里我們每個人還多領到一根繩子,兩米多長,一端拴在我們的腰上,一端拴在礦工的手上。這是我們的保險帶,保險的責任交在礦工手上。在這里每一個新礦工下井都是這樣“保險”的。你腰間的繩子一端交在誰的手上,誰個就是你的師傅。在這里師傅不僅要教會你勞動技能,更要教會你安全意識。師傅天天牽著你上井、下井,直到一根繩子從有形到無形,從肉身到精神,直到一根繩子拴牢在你的生命里,再離開繩子你就不用害怕了。領我下井的師傅姓耿。耿師傅交待我說,你低著頭,頭頂的燈光照著兩腳,眼睛看著兩腳,不用驚慌,不用害怕,一只腳站穩后,另一只腳再往下移動。我問耿師傅,礦上有沒有礦工失過手?耿師傅說,下礦井你最好集中精力,一句話不要說。耿師傅避而不答我的問話,是有意回避,還是不好回答。兩人一組,相隔十來米,上面一組人萬一失手,下面一組人也好有時間往旁邊躲閃。旁邊就是一排排券井的坑木,上下井礦工交匯就是一個礦工躲閃一旁讓開另一個礦工。木梯上都是泥水,手扒著又濕又滑,腳踩著又濕又滑,一步一步往下挪,真是提心吊膽的,生怕有個什么閃失“撲通”一聲,掉進深不可測的黑洞里。好在下面一團漆黑,四周一團漆黑,就算我的兩眼不是緊緊地盯著腳下的木梯,看上面,看下面,看四周,也是一團漆黑什么都看不見。人們說,無知者無畏。身處危險境地,看不見危險,不知道危險,一步一步挪下十幾米過后,也就不知道害怕了。試想一下,要是在地面上,要是在大白天,沿著一座高樓的拐角,豎著這么一只木梯,誰敢這么爬上爬下的?光亮有光亮的好處,黑暗有黑暗的益處。整個豎井不足兩米見方四十米深挪到底,抬頭一看,上面的井口,方形變圓形,很像一輪滿月懸掛在漆黑的天空。猛然一下,恐懼像是四周的黑暗,緊緊地包裹住我的身心,我的兩腿發虛,兩手發軟,一點力氣都沒有了。

盧西安·弗羅依德作品-4
這口豎井,算是主井。主井旁邊還有另一口豎井,算是副井。副井上方架設著三腳鋼架,頂端安裝著一只天輪,通過鋼絲繩吊掛著一個鐵斗。井下需要的材料,通過鐵斗吊下去。井下扒出來的粘土,通過鐵斗提上來。可以說,中國最原始最落后的礦井莫過于這種粘土礦。記得那一天我從粘土礦的豎井爬上來,不僅有一種重見天日的感覺,更有一種劫后余生的感覺。回到廠團委辦公室。老宋問,你下粘土礦害怕不害怕?我說,害怕。老宋問,你的兩腿發抖不發抖?我說,發抖。在那一刻,我覺得說假話、唱高調是可恥的。我反過頭來問老宋,你第一次下粘土礦害怕不害怕,你的兩腿發抖不發抖?老宋說,我沒下過粘土礦。
相隔一年,老宋領著我又一次去粘土礦。這一次不一樣,老宋要下粘土礦。礦領導說,拍照片你讓曹干事一個人下去就可以了——老宋和我帶著照相器材,要挨個單位去拍攝青年團員具體的工作學習場景,為下一步布置宣傳櫥窗做準備。多下一個人,礦上就得多派一個人,多下一個人就要多出一份危險。一般情況下,粘土礦不愿別人亂下礦井。老宋很固執,說這一趟無論如何要下井。礦領導依著老宋,派出三名年輕的礦工跟著我倆,其中一個礦工專門負責背著照相器材——照相機、閃光燈、三角架。我跟老宋手里都領到一根兩米多長的繩子。老宋不愿系繩子。
老宋說,你們下礦井不用系,我也不用系。
礦領導說,我們每天下井習慣了。
老宋說,我也是下井習慣了。
礦領導問,你什么時候下過粘土礦,我怎么會不知道?
老宋說,在夢里我已經下十五年。
我說,我是第二次下井,也不用系繩子。
礦領導說,上個月我們招收一批新礦工,第一次下井也是不系繩子,誰害怕誰不下,自動回家去。
這里的礦工多是從農村招收的臨時工。技術工,帶班的,才是正式工。
我問,他們第一次下井不系繩子,出事沒出事?
礦領導聽見我的問話也是當作沒聽見。后來我知道,在礦上忌諱說“出事”這種話題。
我們五個人下礦井的次序是,一個年輕的礦工走在最前面,老宋走第二,另一個年輕的礦工走第三,我走第四,背著照相器材的年輕礦工走在最上面。看似不分組,實際上還是兩人分一組,組與組之間,相隔七八米。一路上,我看不見老宋,老宋也看不見我。但我知道老宋在前面走得很慢,很艱難。走在我前面的礦工不斷地對我說,走慢點,走慢點,我們離下面的一組人太近了。有過第一次下井經驗,第二次下井就是不系繩子,心里也從容許多,腳下也沉穩許多。老宋是第一次下粘土礦井,可以想見他心里的恐慌與腿上的顫抖。老宋為什么非要執意下礦井呢?老宋為什么非要執意不系繩子呢?老宋的執意與黑頭到底有哪些關聯呢?
老宋先下到豎井底,我后下到豎井底。老宋坐在一塊大石頭上歇著。四十米木梯走下去,消耗的不僅是體力,更是精神上的緊張與恐懼。燈光一照,我看見老宋的臉色煞白,汗水順著膠殼帽子的帶子往下滴。我看不清自己的模樣。我想自己的一副模樣大概比老宋的也好不到哪里去。一扇地獄之門,我第二次踏進,老宋第一次踏進。
就是這一天,我在豎井下面看見干活的黑頭。黑頭是個彪形大漢,黑臉,黑手,黑身子。巷道狹窄,潮濕悶熱,礦工干活,脫光上身。人人身上長滿肌肉,流滿汗水,抹滿泥土。老宋摸進一個巷道,走近一個黑臉大漢說,馬建軍,我來看看你。馬建軍是黑頭的大名,這我是知道的。我呆愣愣地看著眼前的鐵塔漢子,一瞬間他的臉上露出一片驚慌與不解。老宋說,曹干事,你替我倆拍一張合影。老宋靠近黑頭,伸手去摟黑頭的肩膀。黑頭身子一閃晃,老宋搭在黑頭肩膀上的一只手滑下來。黑頭不說話,走出巷道,不知他要去哪里。老宋不覺得尷尬,沖著黑頭后背說,我今天下豎井,沒有系繩子。黑頭帶著一團黑影走遠了。我趕緊按下手上的快門,閃光燈一亮,拍下一張黑頭遠去的背影。
三
一場十五年的噩夢結束了。老宋開口跟我這么說。
那一年,老宋十五歲,黑頭也十五歲,兩人同班同學,學校停課鬧革命,一群孩子整天在家東溜西逛。陶瓷廠緊挨著一家國有大型煤礦。煤礦緊挨著農村。他們去煤礦的塌陷區逮魚摸蝦——塌陷區的水塘里有魚有蝦有蛤蟆;他們去附近農村打群架——郊區農村的孩子在煤礦中學上學,陶瓷廠的孩子也在煤礦中學上學,他們自然地分成不同幫派;他們去煤礦的矸石山拾塊炭——塊炭三分錢一斤,賣錢能買不少好吃的。有一天,一個孩子在矸石山撿著一塊東西,像是一塊松香,卻比松香色澤褐紅。最奇怪的是這塊東西里包裹著十幾條奇形怪狀的蟲子。這種東西孩子們不知道是什么,大人們卻知道,它的學名叫琥珀。有識字的礦工查閱過字典解釋說,琥珀是古代松柏樹脂的化石。數萬年前,茂密的松柏生長在地面上,樹上分泌出大量的樹脂,生長著我們不知道名字的各類蟲子。一只只蟲子聞著樹脂的香味爬過去,或飛上去,粘稠的樹脂粘住它們的翅膀及四肢。一朝地殼震蕩,樹木覆蓋地下數萬年過去,樹干變成煤炭,松脂變成琥珀,蟲子變成琥珀的一部分。不變的是蟲子最初融入松脂的掙扎形狀。得到這塊琥珀的是個農村孩子,跟老宋他們不是一個幫派,可以說是死對頭。琥珀人人喜歡是收買人心的好東西。這個孩子狠手砸碎琥珀,一只蟲子收買一個孩子的人心,很快就把黑頭老宋他倆孤立出來。他倆去塌陷區逮魚摸蝦遭人打,他倆去矸石山拾塊炭遭人打,足不出戶成了他倆唯一的選擇。造成這一困境的原因,是別的孩子撿到一塊琥珀,他倆沒有。琥珀是從煤礦下面扒出來的,他倆要是能去煤礦下面走一遭,豈不是想要多少琥珀就要多少琥珀嗎?
他倆要下一趟礦井。
大礦的礦井四周圍著鐵絲網,主井、副井孤零零地立中央,像日本鬼子的碉堡一樣。煤礦的大門口有持槍的民兵把守著,煤礦的礦井也有持槍的民兵把守著,說是防止階級敵人搞破壞活動,說是實施無產階級專政鐵面無私。黑頭膽子大,老宋膽子小。黑頭敢說敢為,老宋敢說不敢為。他倆像游擊隊員似的偷偷地鉆進鐵絲網,慢慢地靠近礦井(這些都是跟那時的抗戰電影學習的)。大白天,礦井四周無遮無攔。他倆匍匐地面,一點點地爬向礦井,還沒有靠近礦井,就被持槍的民兵抓住了。民兵把他倆帶進值班室,分開審訊。黑頭倔強著,一副寧死不屈的樣子。民兵問什么話,黑頭都說不知道。
你叫什么名字?

盧西安·弗羅依德作品-5
不知道。
你倆進煤礦干什么?
不知道。
是誰指派你倆的?
不知道。
啪,啪,啪。黑頭連著挨了三皮帶。老宋牙口松,民兵問什么他答什么。
你叫什么名字?
宋衛國。
你倆進煤礦干什么?
找琥珀。
是誰指派你倆的?
是馬建軍指派我的。
啪,啪,啪。老宋照樣挨了三皮帶。
老宋問,我什么都交代,你們還打我干什么?
民兵說,這是規矩。
老宋說,早知道有這樣的規矩,我一句話不會說。
民兵說,不老實交代,三皮帶抽死你。
黑頭的三皮帶重,老宋的三皮帶輕。民兵審訊他倆,扒光他倆的褲子。黑頭的屁股留下三道血口子,老宋的屁股留下三道血棱子,輕重差別還是很大的。民兵左看右看眼前的兩個毛蛋孩子不像搞破壞的階級敵人,就放掉他倆。
黑頭問,你交代什么沒有?
老宋說,我一句話沒說。
黑頭說,那就奇怪了,你什么沒有交代,怎么會放掉我們倆。
老宋說,他們八成會派人跟蹤,想查清楚我倆到底想干什么吧?
黑頭說,有可能。
他倆不敢直接回家,繞一個很大的彎子,繞一條很遠的路線,一下子繞到十多里路遠的粘土礦。
老宋問,我倆來粘土礦干什么呀?
黑頭說,下豎井找琥珀。
黑頭不下礦井不死心,不找到琥珀不死心。老宋說他不知道粘土礦的豎井怎么下。黑頭說他知道。他倆的父親都在粘土礦下井。黑頭跟著父親來玩過,老宋沒來過。粘土礦跟大煤礦不一樣,沒有大門,四周不用鐵絲網,一口豎井空落落地丟那里,一個活人都沒有。工廠鬧革命停產,粘土礦跟著停產。職工瘋掉似的,天天上街去游行,扯著嗓子喊口號。他倆來到豎井旁邊,黑頭說你先下,我后下。井口黑咕隆咚的,像是一張巨獸的嘴張那里,老宋低頭看一眼豎井,兩條腿顫抖起來。黑頭看出老宋害怕,說要不我先下,你在后面跟著我。老宋說,下面漆黑一團,我倆下去什么都看不見。黑頭說,下面有一盞亮燈,難道你看不見?一盞燈在遙遠的井底亮著,像是一個冤屈的鬼魂。黑頭慢慢地轉過身子,臉面朝著木梯,兩只腳站在木梯上面,兩手扶著木梯準備往下下。老宋的兩腿顫抖,身子顫抖,牙齒顫抖,整個人都在顫抖。黑頭說,直到你看不見我的頭,就跟著下去。老宋不說一句話,轉身拔腿就跑開。黑頭問,你跑哪里去?老宋朝著家的方向一個勁地跑,一個勁地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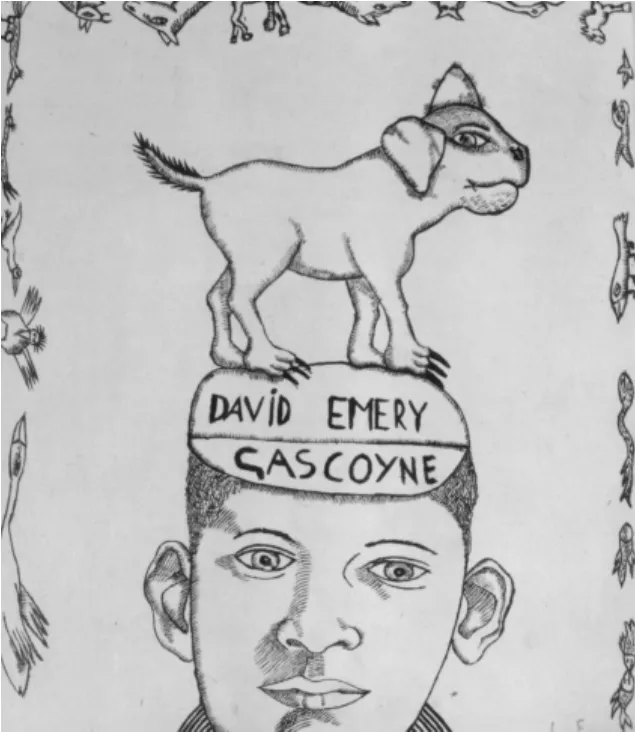
盧西安·弗羅依德作品-6
就是從這天起,老宋就不再去找黑頭一起玩了。黑頭沒有說老宋什么不好。是老宋自己把自己當作一個膽小鬼。是老宋自己覺得自己沒有臉面再跟黑頭一塊玩。他們兩家住前后兩排房子里,老宋不去找黑頭玩,黑頭過來找老宋玩,老宋也是不答應。老宋說,我在家做作業,沒有時間去玩。黑頭說,學校鬧革命,老師不上課,哪有作業呀?老宋說,我自己給自己布置的作業。那些天老宋哪里都不去,整天在家里做作業。課本上的例題挨個地抄一遍,課本上的習題挨個地做一遍,老宋就這么陽差陰錯地把學習成績提高上去,初中畢業考上一所高中學校,繼續上學。黑頭成績一直不好,初中畢業沒有考上高中,繼續在家東溜西逛的,逮魚摸蝦,找人打架。那時候,初中升學率不到百分之四十,大部分孩子初中畢業沒學上。這樣兩人間的差距越來越大,玩不到一塊去不說,老宋也沒時間去找黑頭一塊玩。老宋倒是經常地聽見黑頭大(爸)罵黑頭,打黑頭,說他整天東串西串不干正經事,說他惹事生非討人嫌。
老宋跟我說,黑頭大跟大多數礦工一樣,喜歡在家喝酒,喜歡酒后罵一罵老婆,打一打孩子。可黑頭大跟大多數礦工不一樣的是,我從來就沒見他喜歡過黑頭,黑頭像個別人家的孩子似的。
有一天,老宋聽見黑頭的家人哭。黑頭哭,黑頭娘哭,都是哭個呼天搶地的。老宋跟著四周鄰居圍過去才知道黑頭大在粘土礦的下面出事故,當場砸死了。那一天,老宋大拉肚子,擔心下井下不去,就讓黑頭大代替上一天班,算是死里逃生撿著一條命。兩家是鄰居,原本關系就不錯,黑頭大與老宋大都在井下做班長,要是班長不下井,一個班就沒有頭,井下就容易出亂子。活著的礦工說,這次井下出事故,就是因為井下干活的礦工不聽黑頭大的話,違規操作造成的。黑頭大是替老宋大去死的。老宋大照顧黑頭娘倆的生活變成一種良心債。黑頭娘不黑,雪白的一個女人,比老宋娘白凈,也漂亮。老宋大經常去那邊看一看,老宋娘有意見,兩口子沒來由地經常吵話。黑頭娘不傻,知道老宋父母為什么經常吵話,就悄悄地調一間公房搬往別處住。同是一個廠子里,黑頭娘拿兩間公房,換別人家的一間公房,人家當然很樂意。黑頭一家搬走,遠離老宋家,搬不走的是壓在老宋大心里的一堆良心債。就是這時候,老宋大開始喝悶酒,走向一條自殘路。上班一個人悶悶不樂地去上班,下班一個人在家悶悶不樂地喝悶酒,一口氣喝出一個肝癌來。老宋大臨死說出來的最后一句話,是對不起馬文年,對不起蔡春花,對不起黑頭這孩子。我害得馬文年早早地替我死去,我害得蔡春花早早地沒了丈夫,我害得黑頭這孩子早早地沒了大(爸)。馬文年、蔡春花是黑頭父母的名字。老宋大說過這句話便死去,死得依舊不輕松,兩只眼大睜著就是閉不上。
老宋大死,黑頭娘來過一次。黑頭娘跟老宋娘說,馬文年替宋傳江去死,那是我們家的馬文年命不好,該著他這么一死。宋傳江是老宋大的名字。黑頭娘繼續說,你們家的宋傳江是你害死的,你不該讓他喝這么多的悶酒,你不該懷疑他的做人。老宋娘不去反駁黑頭娘,抬起手“啪、啪、啪”地去掌自己臉,說是我害死我們家的宋傳江呀,我要遭報應不得好死呀。黑頭娘沒去拉老宋娘的手,四周也沒有人去制止。老宋娘變成一個世人譴責的女人。
這一天,黑頭跟著娘一起走過來,趴在老宋大的靈位前,磕了三個響頭,說一聲宋叔叔你走好,就離開了。老宋是孝子,披麻戴孝地一直跪在父親的靈位前面。黑頭過來,他倆沒有說上一句話。

盧西安·弗羅依德作品-7
兩年后,兩人長夠十八歲,黑頭接父親班去車隊做維修工,老宋接父親班進廠機關。
老宋說,我們那時候高中是兩年制,我接班能進廠機關是按人才使用的,先是做統計,后是做會計,再后來進的廠團委。
四
再一次見到黑頭是在淮河堤壩上。
八月里,淮河漲起一場大水。每年淮河都這樣,早一點六月里漲大水,晚一點十一月里漲大水。大水一旦漲起來,超過一個警戒水位,就需要派人駐守淮河大堤防汛了。這段淮河區域總的來說,淮河北邊是農村,淮河南邊是城市。淮河北邊的上堤人員是以鄉鎮為單位,淮河南邊的上堤人員是以廠礦為單位。我們廠分配三百米淮河大堤,上堤人員大約需要三十個人,按照黨總支單位,一個單位派兩個人,統一由廠武裝部指揮,廠團委只是一個協助部門。上堤人員一個個都是男的,大多數是基干民兵,青年團員,廠團委參與防洪有一定的必要性。堤壩上搭起帳篷,鐵锨、鐵鎬一應防汛工具,廠里準備得有;蚊帳、鋪蓋一應生活用品,廠里也準備得有。早、中、晚一天三頓飯,廠里派車從職工食堂送過來。要是不到洪水的危急關口,各個單位的職工爭搶著來上堤。老宋在廠團委看家,我上堤。我的任務就是負責早晚各點一次名。河水離壩頂差不多有兩米遠,不需要加揳木樁,不需要加固泥土,三十人分六組,一天二十四小時輪流在三百米長的堤壩上來來回回地巡視著。查看堤壩上面不要出現險情——水位離堤壩頂端早著呢,不會有險情;查看堤壩下面不要出現滲水——堤壩下面的莊稼連根砍出,無遮無攔,有沒有滲水一眼看出來。堤壩沒有險情,防汛人員沒有其他事干,除去巡視之外就待在帳篷里,打牌的打牌,睡覺的睡覺,閑閑散散,這哪里是防洪?簡直就是游玩,簡直就是療養。三十個人,白吃白喝,一晃半個月。老楊說,這叫養兵千日,用兵一時。他預言家一般地說,你們等著吧,今年肯定要有一場大洪水。老楊是副廠長,分管后勤、武裝保衛等工作,廠防汛指揮部負責人的帽子理所當然地落在他頭上。
前一段我在堤壩上沒見到黑頭。這么好的一樁美差,粘土礦不會派黑頭。
一場大雨下下來,一連下三天。雨水催促著,淮河水“噗噗噗”地往上漲,淮河堤壩一下就吃緊了,呈現搖搖欲墜的態勢。這可不是好兆頭,市防汛指揮部一聲令下,快點加固堤壩。揳木樁,挖泥土,扛袋子,三十個人按組分散開,各干各的活。所謂揳木樁,就是把一根一根兩米多長的木樁揳進堤壩外的泥土里,而后沿著木樁拉上鐵絲,一袋袋泥土才能壘上去。揳木樁要的是力氣,挖泥土使的是耐力,扛袋子拼的是體力。三十個人冒雨干活,腳下是滑的,身上是汗的,頭上是濕的。很快一個個防汛隊員就累倒了,整個防汛隊伍“嘩啦”一下就癱瘓了。辦法只有一個——換人。廠防汛指揮部要求各單位更換一些能吃苦耐勞的同志頂上來。防汛的要緊處往往就這樣,弱者下,強者上。老宋要過來替換我,我說我能撐得住。我撐得住的原因,是我不揳木樁,不挖泥土,不扛袋子,只做一些輕巧活。我每天的任務還是負責早晚兩次點名,再一個就是沒完沒了地寫匯報材料。防汛吃緊,各級領導干部都是不安分,輪流在防汛大堤上瞎轉悠。哪一級領導走過來,老楊都要從頭至尾地匯報一番。我每天晚上還有一項工作,就是去附近居民家看電視,重點是看市電視臺的新聞聯播。老楊跟我說,你白天注意看報紙,晚上注意看電視,這樣寫出來的材料才能與市防汛指揮部說話一個腔調。“與市指揮部說話一個腔調”是我寫材料的核心與靈魂。老楊文化程度不高,自己寫不好匯報材料,應付上面的材料都是我執筆。聽老楊說,他參加過解放戰爭的渡江戰役,別人是坐船渡江,他是游泳渡江。他說他的頭腦就是那一次渡江被江水泡壞了,現在一見河水就眩暈就嘔吐。他整天坐在帳篷里,不停地問,曹干事,水漲到哪里了?河水里豎著一根標尺桿,我跑過去,按照數字報一下。
曹干事,木樁揳下去好多了?
我跑過去數一下,回頭報上一個數。
曹干事,泥土袋子加上去好多了?
這一次我沒跑出去,順口報上一個數。
曹干事,你不去數一數,怎么能胡亂報數呢?
我知道你要問泥土袋子的數字,我上次出去一起數過了。
按照上面規定,兩米大堤揳一根木樁,三百米大堤一共要揳一百五十一根木樁(兩端多出一根木樁);一米大堤加固十只泥土袋子,三百米大堤一共要加固三千只泥土袋子。老楊說,我們的木樁揳密一點,多加五十根木樁;我們的泥土袋子加高一點,多加五百只袋子。老楊頭腦一熱,說出這么一句話三十個人多干半天活都不止。淮水滔滔,直逼壩頂市里的幾家報紙、電臺、電視臺記者云集過來,采訪報道老楊,說照你們這樣防汛,就算淮河水再漲兩米也不怕。面對一群新聞記者,老楊無限感慨地說看來我們需要打一場硬仗呀,必要的時候我會像當年渡江一樣帶頭跳進江水里,不、不、不,是河水里。
就是這一階段,粘土礦把黑頭換過來。這家伙黑頭黑腦,鐵塔一樣,走上河堤,掄起大錘就揳木樁。揳木樁,挖泥土,扛袋子,三樣活相比較,揳木樁最累人。一大錘揳下去,揳不實在,不用力氣,木樁肯定下不去。礦工在井下,經常地揳木樁。應該說揳木樁是礦工的老本行。粘土礦派來的兩個人,站在河堤上揳木樁。煤礦派來的兩個人,站在河堤上揳木樁。有了四位礦工,揳木樁的進度就快起來。但是礦工和礦工還是不一樣,黑頭一個人要抵他們兩個人。“咚——”,一大錘揳下去,“咚——”,一大錘揳下去,木樁像條泥鰍,“哧溜、哧溜”一個勁地往泥土里鉆。木樁揳齊拉鐵絲。鐵絲拉齊壘泥土袋子。別人搬運泥土袋子是上肩扛,泥頭泥腦地弄一身。黑頭搬運泥土袋子上手抓,單手一抓一提就走了。一袋子泥土少說有百十斤,兩只手抓住兩袋子泥土像是兩把大鉗子。干活就是干活,黑頭一句話不說像是一個啞巴。廠里許多人認識黑頭,知道他從監獄剛出來,知道他在粘土礦干的是一份臨時工。一個臨時工在河堤上這么賣力氣就有點令人不解,就有點受人懷疑。是不是有什么企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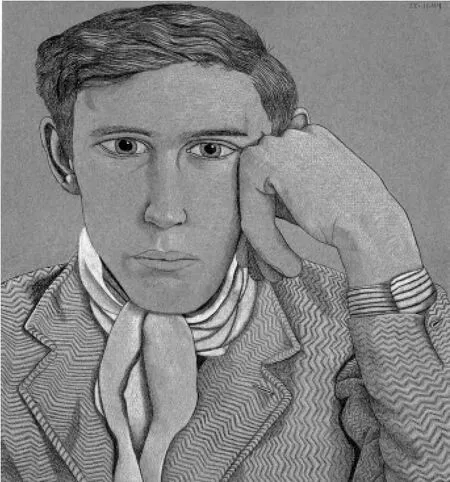
盧西安·弗羅依德作品-8
這種猜疑在今天看來很幼稚很可笑,可在那時候很正常很必要,算是文革階級斗爭的慣性思維吧。老楊聽到這種猜疑,一副坐立不安的樣子,一副大難臨頭的樣子,一副如夢方醒的樣子,要我趕快打電話跟粘土礦的領導說,讓他們派一個人把黑頭換回去。老楊十分氣憤地說,這個安書記呀,不知道安的是一顆什么心,這種人怎么能派他上河堤呢?安書記就是粘土礦黨總支書記安明財。這種捕風捉影的話讓我怎么好跟安明財去說呢?況且這里邊還牽扯到老宋。黑頭出獄,老宋出面找安明財,才安插黑頭去干一份臨時工。那時候,我們廠的用工情況很復雜,正式工,合同工,協議工,占地工,集體工,臨時工,各樣工種一一羅列出來差不多七八樣。其中正式工,還分干部身份和工人身份。干部身份,又分正式國家干部和以工代干身份。
老楊說,你就跟安書記說,這不是哪一個人的意見,這是廠防汛指揮部的決定。
我跟老楊說,這么多雙眼睛一齊盯著黑頭,他想搞破壞活動就那么容易嗎?
老楊說,候他真把破壞活動搞出來就晚了。
我問,黑頭在這里能搞什么破壞活動呢?
老楊說,炸大壩!
我問,他哪里來的炸藥呀?
老楊說,他們的反動組織提供。
我問,有這么一個破壞組織存在嗎?
老楊凝視著我,眉頭擰出一道麻花,眼里刮過一陣寒風。
老楊反問我說,你怎么知道沒有呢?
就是老楊這么一凝視一反問,我知道這件事不能感情用事,必須去辦。
我打電話給安明財。安明財在電話里很委屈地說,在粘土礦數黑頭干活最下氣力,我派他去是為粘土礦爭光的。每年防汛結束都要評比先進,安明財派黑頭來是要準備拿先進的。這種意圖安明財跟黑頭交待過,所以他在大堤上干活才這么賣力氣。我不知道怎么去跟黑頭說這件事,只能含糊其辭地說安書記打電話讓他回粘土礦一趟。黑頭一句話沒說,收拾起自己的包袱,就跟著我一起離開防汛帳篷。黑頭沒問我為什么要他回去,但他心里什么都明白。眼見快到吃晌午飯的時辰,讓黑頭就這么空著肚子回去我不忍心。
我說,你在這吃過飯回去吧?
黑頭說,我回家吃,下午上班能來得及。
我說,今天你可以休息一天,明天去上班。
黑頭說,我是按班次給錢的,缺班就缺錢。
我說,我打電話跟你們礦上說一聲,今天算你上過班。
黑頭說,不用,我喜歡下礦井。
我倆前后見過兩次面,攏共說話就這么多。
黑頭是從五臺泵坐小筏子離開的。十分鐘過后,我倆就一起出事。我活著,他卻喪失了性命。

盧西安·弗羅依德作品-9
這一段淮河堤壩外面是湯湯的淮河水,里面是湯湯的塌陷塘。塌陷塘與淮河相互滲透,淮河的水位上漲,塌陷塘的水位跟著上漲。這里安裝著五臺大型水泵,五根合抱粗的鋼管翻越堤壩,整天整夜地吼叫著把塌陷塘里的水抽回淮河。因而,這個地方人們就形象地稱它為五臺泵。前些天淮河的水位沒有漲起來,水泵就斷斷續續地打開抽水。塌陷塘里有野生的各種雜魚,水泵轟鳴著把魚攪拌得暈頭轉向,吸進渦輪,吐進淮河。幾個閑人手里拿著抄網,站在淮河邊就能把一條條暈頭轉向的魚抄出來。淮河堤壩是防汛重地,外人不允許靠近,幾個閑人也是我們廠的防汛人員。起初老楊反對去抄魚,覺得逮魚跟防汛一點邊不沾,有些不務正業的嫌疑。抄網網眼大,小魚不要,落進網里的最小半斤重。更大的魚,經渦輪攪拌,都是囫圇半個的。囫圇魚也是魚,新鮮,肥美,看著喜人眼。老楊屬貓,鼻子聞見魚腥味,嘴里流口水。老楊靈機一動,跟幾個閑人說,抄著的魚全部歸公,交給職工食堂。伙夫根據魚的品種紅燒、清燉或煨湯。這樣一來,等于自己想辦法改善自己的生活。天天吃魚肉,頓頓喝魚湯。一連好多天,我除去監督沿著淮河堤壩的巡邏人員外,還得安排閑人去五臺泵抄雜魚。
水泵轟鳴,魚肉飄香,是一種別處沒有的防汛景觀。
塌陷塘的水面東西綿延十里路,嚴重阻隔著交通,廠里運送防汛物資的卡車只得繞道走過來。每天早中晚三次飯菜,就乘坐小筏子直接穿越塌陷塘水面運過來。塌陷塘狹長,寬不足百十米。卡車把飯菜送至塌陷塘的對岸,小筏子搖呀搖呀的很容易就能接過來。小筏子屬于五臺泵,水泵屬于附近的一家國有大型煤礦。負責看管水泵的職工上下班就是乘坐小筏子。我們借用小筏子,不是白借,他們跟我們一起吃。我們借用他們的小筏子,吃他們水泵泵出來的雜魚,他們吃我們的飯菜,兩廂就算扯平了開頭淮河水位低落,時斷時續地開兩臺水泵抽水后來淮河水位上漲,五臺水泵滿負荷運轉。五臺水泵一齊開動,就是五條吸水的巨龍。水面上形成一個個漩渦,旋轉著,攪拌著,在水泵前面的不遠處鬼魅叢生,陰險出沒。這一天接送飯菜的小筏子遠遠地回避開,沒想到還是遭到暗藏漩渦的算計。突然地,沒有防備地,一個暗藏的巨大漩渦從水下躥上來,浮出水面的位置正好對著小筏子。小筏子一扎頭,一閃晃,沉進去。

盧西安·弗羅依德作品-10
當時小筏子上有三個人——我,黑頭,還有一個專門負責擺小筏子的人。對岸有跟著卡車一起來送飯菜的食堂職工,我可以去接飯菜,也可以不去接飯菜。黑頭不明不白地離去,我心里有一種說不明白的愧疚,想陪著他多走一段路,想去對岸拿一點吃的塞給他。我知道我的這些想法很幼稚,黑頭走出帳篷一句話不說,更不會接受任何吃的東西。“撲通”一聲,我一頭閃進水里,旋進漩渦里,一吸一吐,一瞬間我又被遠遠地拋出水面。我會鳧水,那一刻我本能地拼命地朝著岸邊游過去。小筏子遇見漩渦的地方離岸邊差不多十來丈遠吧。我聽見岸邊的人們拼命地喊叫著:黑頭——!黑頭——!我頭腦逐漸清醒,回頭看一眼,小筏子底朝天覆蓋在水面上,那個擺渡人在我前面朝著岸邊游,手里驚慌地拖著一只棹,唯獨不見黑頭在哪里。
黑頭——!
黑頭——!
五臺水泵一臺接著一臺停下來。岸邊的人們開始一個接著一個往塌陷塘里跳。我被兩個人架上岸邊,像一團稀泥癱軟在那里。那個擺渡人被兩個人架上岸邊,一只棹緊緊地抱在懷里,“稀稀溜溜”地哭起來。水泵停下來,大大小小的漩渦失去動力,不甘心消失,不甘心滅亡,在水面上胡亂地旋轉,胡亂地碰撞。幾個人游到小筏子旁邊,齊手翻過小筏子,小筏子下面空空的,依舊不見黑頭的影子。人們開始驚慌起來,紛紛地扎猛子去水下摸黑頭,卻不知道去哪里找黑頭,不知道黑頭在水面下的哪地方。
——黑頭在水泵下面!
——黑頭在水泵的渦輪下面!
喊話的是趙心亮。他站在塌陷塘的對岸。他站在那輛破舊的卡車旁邊。他每天都開著卡車來送飯菜。他每天都要在塌陷塘的對岸兩手掐腰站一站。今天不一樣,趙心亮拼命地喊叫著:——黑頭在水泵下面!——黑頭在水泵的渦輪下面!而后趙心亮鉆進那輛破舊的卡車拼命地開起來。
五
我開動那輛破舊的卡車瘋狂地跑起來。我要繞過去接黑頭。我明白我去接著的肯定是一具死尸,而不是一個大活人。黑頭上河堤我知道,上河堤半途回頭可不是一個好兆頭。我一眼看見他像一座鐵塔似的站在小筏子上,我就預感到要翻船。人的預感有時候是沒有道理的,是說不清楚的。只是我沒想到會是這么一種翻法。更沒想到小筏子一頭鉆進漩渦里,你會出來,擺渡人會出來,黑頭會出不來。黑頭為什么會出不來?那是因為黑頭……
——黑頭死后,趙心亮跟我說出不少他與黑頭之間的事情,說出不少他對黑頭的看法。
那一天,許多人下水都沒摸著黑頭。防洪堤壩上的活,整個地停下來。不算我,不算老楊,不算黑頭,堤壩上還剩二十九個人。二十九個人全部下水里,全部扎猛子,摸來摸去,就是不見黑頭的影子。塌陷塘水面寬闊,深淺不一,人手能摸著的地方畢竟有限,大多集中在翻船的附近水域。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黑頭生還的希望一分一秒地減少。甚至可以斷言,黑頭早就在水下憋悶死。
趙心亮跑過來。
他開著的一輛破舊卡車像一匹脫韁的野馬繞道從堤壩上跑過來。看見的人提心吊膽,生怕卡車翻到南邊的堤壩下面,或翻到北邊的河水里。
——黑頭在水泵下面!
——黑頭在水泵的渦輪下面!
趙心亮停下卡車,跑過來說出這么兩句沒頭沒腦的話。這么兩句話,是他在塌陷區對岸喊過的。小筏子翻沉的地方離開水泵幾十米,這么遠的一段距離,黑頭怎么會在那里?疑問歸疑問,水里的防汛隊員還是有意無意地朝著水泵的地方靠攏過來。趙心亮顧不上脫去身上的衣服,帶頭撲往水泵的地方。在防汛大堤上,老楊是總指揮。老楊命令水里的防汛隊員,快把趙心亮這個家伙給我攆上來。趙心亮聽見老楊喊話,不當一回事,像一只野鴨子,繼續往水泵的地方游過去。
這些天,趙心亮專門負責每天三次往返送飯菜。車隊王懷禮派趙心亮做這項工作走的是一招險棋。試想一下,趙心亮開著這么一輛破舊的卡車,要是把飯菜耽擱在半路上,防洪大堤上幾十人餓著肚子怎么辦?影響淮河防汛往小里一說,或許是一件小事情,往大里一說,就是一個大問題。弄不好趙心亮受處理,王懷禮也休想逃得掉。最起碼兩人的當月獎金要扣除吧。王懷禮走這么一招險棋,不說別人,老楊就意見很大,說往防汛大堤上送飯菜,不是去監獄接人,卡車壞那里就是壞那里,早一點、晚一點車隊派車去拖回來。我這可是三十多號人吃飯啊!我這三十多號人吃飽飯可是要揳木樁、挖泥土、扛袋子啊!王隊長回答說,車隊車輛緊,要保證廠里的生產,要保證防汛大堤的物資供運,哪里還有空閑的車輛去送飯菜呢。實際上王隊長就是想走這么一招險棋,表面上是針對防汛大堤上的三十多張肚子,其實是想對付趙心亮。這兩年趙心亮完全變成另外一個人,整天瘟頭瘟腦的,身上的手藝日漸荒廢。原本趙心亮可是一個性格開朗的人,修車技術在車隊沒人能夠比得上。趙心亮的修車技術是在部隊里學的,轉業來廠里的汽車隊。瘟頭瘟腦的原因趙心亮可以不說,王隊長也可以不問,但是技術荒廢,壞掉的車子修不好,是耽誤車隊的工作,是影響王懷禮的臉面。王隊長跟趙心亮說,你去送飯,車上帶上一副扁擔繩子。趙心亮問,我帶扁擔繩子干什么呀?王隊長說,車子壞在半路,你就自個擔著飯菜往淮河堤壩上送。趙心亮說,我一個人的一副挑子也擔不下這么多飯菜呀?王隊長說,一趟擔不下,你回頭再擔一趟。十天半月過去,這輛破舊的卡車一次沒有壞。不是車子通人性,是趙心亮不敢讓車子壞。空閑下來,趙心亮哪里不敢去,不時地圍繞著卡車搗鼓來、搗鼓去。趙心亮的老家在阜陽,離這里二百多里遠,老婆孩子丟那邊,一個人住在單身宿舍里。單位、食堂、宿舍,三點一線,我倆生活的軌跡差不多,經常碰面,卻很少說話。這一天,趙心亮開著一輛破舊的卡車像一匹脫韁的野馬,使勁地尥開蹄子,哪里會顧上車廂里的飯菜。飯菜翻倒,菜湯滴灑在道路上,飯菜殘留在車箱里像一灘稀牛糞。
老楊在岸邊不斷地叫喊著,你們把趙心亮給我抓上來!
趙心亮游到水泵的地方往水下扎猛子。抓捕趙這件事,說這是個別人的胡說八道,說這是少數人的別有用心。老楊說,我當時就在帳篷外面,親眼看見小筏子翻沉的那一刻,曹干事一下子被甩得遠遠的,黑頭一下子沉進漩渦里。在防洪大堤上,老楊說話就是定性,就是權威。老楊這么一說話,謠傳就失去方向性與真實性。現在的問題是,老楊真的在帳篷外面親眼看見小筏子翻沉了嗎?緊接著的另一個大問號是,翻船的地方離水泵幾十米,是一股什么力量把黑頭推過去?漩渦的力量有這么大嗎?水泵的吸引力有這么大嗎?黑頭的死是一團謎。
——啊,啊,啊。黑頭呀,師傅對不起你,那只輪胎是我偷的呀,你是替師傅蹲勞改,你是替師傅死的呀。
趙心亮這么一說話,老楊又是一愣一懵的。老楊武斷地說,這肯定又是一起惑眾謠言!
那時候,趙心亮在車隊做師傅,黑頭在車隊做徒弟,兩個人都是車隊里的維修工。車隊在陶瓷廠的東北角,隔著一道墻頭就是廠區外面。有一段時間,車隊里經常丟失東西,大到一只車輪,一只車胎,小到一塊廢鐵,一根電線。卡車偷不走,就屬小偷小摸的范疇。小偷小摸,事件小,影響大,車隊向保衛科匯報,查來查去,查不出頭緒。墻頭很高,不見翻越痕跡,賊是怎么把東西偷走的?可能性只有一條,排除外賊,懷疑家賊。誰是家賊?車隊幾十口職工,沒逮住手脖子,懷疑誰都是一件沒有憑據的事情。車隊沒辦法,只有加強值班,加強看管。廠保衛科沒辦法,只有加強巡邏,加強戒備。原先每天晚上,車隊只安排一個人值班,現在兩人一道值班。原先每天晚上,廠保衛科只巡邏廠區內,現在擴展到心亮的防汛人員跟著他一起扎猛子。塌陷塘的水面上、水面下一片混亂。
實踐證明趙心亮的猜測是正確的。黑頭就在水泵下面,一個頭、兩只胳膊都卡在渦輪的葉片里。要是水泵不停止,黑頭就會被渦輪肢解成大大小小的肉塊,吸入鋼管,越過堤壩,血糊拉拉地吐進淮河里。現在黑頭四肢完整著,卻早已經憋死在水下。老楊站在岸邊停止喊叫,呆呆地望著塌陷塘的水面。一群人抬著黑頭的尸體慢慢地上岸,像是抬著一截黑乎乎的鋼管。我坐在岸邊,兩眼空落落地看著眼前發生的一切,恍恍惚惚的,像是做著一場噩夢,一個驚飛的魂魄盤旋著,就是不肯落在我身上。黑頭的尸體擺放在我身邊,開始慢慢地發涼變硬,消亡后的生命正在進一步地消亡。趙心亮第一個發現黑頭,第一個抱起黑頭,上岸后一句話不說,卻一個勁地流眼淚。突然,趙心亮“撲通”一聲跪在黑頭面前,說黑頭呀我對不起你,是我害死了你呀。當時趙心亮不在小筏子上,不在黑頭身邊,他與黑頭的落水死亡會有什么關系呢?趙心亮說這話,別人聽不明白,我也聽不明白。很快地有一種謠言傳播開來,說黑頭是因為搭救我才死的。說小筏子扎進漩渦的一瞬間,我落在漩渦的正中心,黑頭落在我的身邊,那個擺渡人被甩在漩渦的最外面。黑頭伸手拉我一把,把我拉出漩渦中心,他自己掉進去。
——這是塌陷塘的岸上人看見的,迅速地傳播開來。當時我頭腦一片空白,小筏子是怎樣翻船的,我是怎樣掉進水里的,一點都記不清楚了。一件瞬間發生的事情,一件記不清楚的事情,我當時的態度是不去肯定,也不去否定。老楊卻立刻出面澄清廠區外。車隊附近的廠區外面是重點巡邏區域。

盧西安·弗羅依德作品-11
這一天晚上,就趕上他們師徒倆一起值班。
車隊有沒有懷疑趙心亮與黑頭不知道,反正黑頭是不會懷疑師傅的。趙心亮是師傅,為人正直,坦蕩,這是人所共知的。黑頭不去懷疑師傅,師傅更不會懷疑徒弟。因為事情都是他一手策劃出來的。從事情的結果看,車隊安排師徒倆一起值班,不去回避他倆的師徒關系,一方面可以理解成單位對他倆很信任,另一方面也可以理解成單位對他倆很懷疑。當然趙心亮理解的是前者,而不是后者。就是事發后,車隊的王隊長說他們懷疑的是黑頭,而不是趙心亮。師傅趁著徒弟睡覺,偷偷地拿一只輪胎在墻頭上,而后師傅跟徒弟說他去茅廁解大手,一去不復返。墻頭外面有一條臭水溝,趙心亮繞道去墻頭外面,拿一根棍子夠下輪胎塞進臭水溝里,就萬事大吉了。一條臭水溝沒人去注意,隔天晚上去里邊取出來,轉手就是一筆錢。以往都是這么做的,這天晚上還是這么做的。趙心亮的一個老婆、兩個孩子都住在老家農村,老婆的身子骨不好,生下的兩個孩子身子骨也不好。老婆常年吃藥,孩子常年吃藥,弄得趙心亮心力憔悴,人窮志短,逼良為賊。
這一次不同以往,墻頭外面埋伏著保衛科的廠警。他們先是看見有一個黑影晃過來,沒有當作一回事。廠警的責任是看管廠區內,廠區外即便出現小偷小摸的人,只要不是把廠里的東西偷出來,都不屬于他們管轄的范圍。待一會,他們看見這團黑影遠遠地站在墻頭下面,一團黑乎乎的東西,“咚”的一聲從墻頭上落下來。黑影的速度很快捷,彎腰揀起那團黑乎乎的東西,轉眼就往相反的方向跑這時候,兩人才察覺有一點異常,大聲斷喝一句,站住,你是干什么的?黑影驚慌失措地丟下黑乎乎的東西,跑得更快起來。那年頭,槍支管理得松懈。廠警晚上值班,隨身就能攜帶著槍支。是一把老式沖鋒槍,槍膛里有子彈,廠警打開保險,沖著天空,手指一扣,一團火星,一聲槍響,一顆子彈就射出去在深夜里,槍聲太突兀,太驚人,黑頭“撲楞”一下就驚醒過來,一看師傅屙屎沒回頭,一絲不好的預感冰水一般流心里。黑頭趕緊往外跑,跑出墻頭外面沒有遇見師傅,卻迎面遇見兩個追趕過來的廠警兩名廠警先是逮住一只丟掉的輪胎,后是逮住奔跑的黑頭。不管黑頭說什么話,廠警就是把這兩者相聯系——輪胎是黑頭偷的。
輪胎不是我偷的。
輪胎不是你偷的,半夜三更你跑什么?
聽見槍響,我跑出去看一看。
看一看,結果你看見了什么?
我看見你們倆。
還有我們倆手里的一只輪胎。
我說過,輪胎不是我偷的。
那你說誰偷的?
不知道。
你不知道,我倆知道。
你們說是誰?
是你。

盧西安·弗羅依德作品-12
趙心亮逃脫了。黑頭被帶進廠保衛科。趙心亮保持沉默。黑頭申辯無效。黑頭知道這件事是師傅做出來的,他不能出賣師傅,更不能連累師母和她的兩個孩子。趙心亮知道這件事讓徒弟背黑鍋的后果是什么,他沉默著不僅顧及生病的老婆和孩子,更是顧及自己的一張清白臉面。單說一只輪胎,或許廠里不會把黑頭怎么樣,趙心亮擔心的是新賬、老賬一起累加在黑頭頭上,那樣的話黑頭承擔的一份罪名就大了。趙心亮心里壓力越來越大,白天吃不香飯,晚上睡不香覺。在黑頭被抓進廠保衛科的第三天,趙心亮先是找到王懷禮,坦白地說出這件事情。王隊長說,你就不要再添亂子了,你想保護黑頭,我不想?說來說去,還是他自己一時糊涂做錯了事情嘛。趙心亮說,車胎真是我偷的。趙心亮也不敢說出從前的事情,一攬子歸一攬子,單說這一次。王隊長說,就是你偷的,也是黑頭偷的。趙心亮問,為什么?王隊長說,你說車輪是你偷的,沒人會相信。趙心亮去廠保衛科說出這件事情,他們也是這樣跟趙心亮說。廠保衛科跟趙心亮說,一件事歸一件事,從前車隊失竊的事情黑頭不承認,我們也不想歸在他頭上。廠保衛科說黑頭,你攤上這么好的一個師傅,怎么就不學好呢?廠保衛科念黑頭是初犯,象征性地罰一點款就把黑頭放回頭。哪知道緊接著是嚴打,新賬舊賬還是一起算在黑頭一個人的頭上,他被判刑五年。從那往后,趙心亮就不是原先的趙心亮了,完全變成了另外一個人,整天瘟頭瘟腦的,身上的手藝日漸荒廢……
——上述這些事情、這些細節都是趙天亮后來跟我說的。
老楊打電話,一輛救護車呼嘯著跑過來,連著我、連著那個擺渡人一起拉出防汛大堤。黑頭死去,是一具尸體,救護車不愿拉。醫生跟老楊說,你直接打電話跟火葬場聯系,讓他們來一輛運尸車。救護車是人民醫院的,拉一具尸體回去,不知道擱哪里。我坐救護車離開,擺渡人坐救護車離開,黑頭留下來。趙心亮依舊趴在黑頭的尸體上,像個女人似地一邊哭一邊說。——啊,啊,啊。黑頭呀,師傅對不起你,那只輪胎是我偷的呀,你是替師傅蹲勞改,你是替師傅死的呀。
一路上,擺渡人在救護車上不斷地叫喊著,我下車,我好好的一點事沒有。醫生說,到醫院檢查一下,沒問題,我們留你在醫院干什么?我安靜地躺在救護車的擔架上,一副渾渾噩噩的樣子,但有一點我明白,黑頭不可能再活過來了。
六
又一次見著黑頭是在火葬場的殯儀館里。
黑頭直挺挺地睡在一副水晶棺材里,化過妝,臉上,手上,脖子上,都是一片白生生的紅,像是一個白胖子。黑頭不再是黑頭,或者說死后的黑頭跟活著的黑頭一點也不一樣。在這里我第一次見著黑頭娘。老太太滿頭白發,一聲不哭,或許眼淚早已干涸。老太太說,兒子呀你死了好,死了就干凈了,死了就利落了,死了就輕松了,不過、不過,不過你死了,娘還活著有什么意思呢?老太太說著話,一口氣倒換不過來,就憋死過去。跟來的廠醫院醫生慌忙地上前去掐老太太的人中,去捏老太太的虎口。更嚇人的是,一個老中醫走過來,拿出一根半尺多長的銀針,擦一擦酒精棉球,就在老太太胸口的部位扎下去。憋、憋、憋,老太太的一口氣憋出三五分鐘那么長,還沒有緩過來,我覺得老太太差不多都死了。“啊——呀——”一聲,老太太的一口氣總算緩過來。四周人長長地松出一口氣。老中醫拔出銀針,一臉驕傲,一臉榮光。

盧西安·弗羅依德作品-13
老太太問身旁人,這個躺著的人是我兒子嗎?
老太太自問自答地說,這不是我兒子,我兒子沒有這么白,也沒有這么胖。
黑頭像是一直被河水浸泡著,一肚子鼓鼓的河水出不來。
趙心亮站一旁不哭不說話,兩眼呆滯,直愣愣地盯著黑頭,像一個已經死去的人。聽人說,那天趙心亮一直坐在塌陷塘的岸邊、一直趴在黑頭的身邊大哭不止。淮河大堤上的防汛隊員,沒有人去制止,沒有人去搭茬。想哭你只管去哭吧。面對一個死人,有人哭一哭總不是一件壞事情。左等半個小時,右等半個小時,火葬場的車子就是不見來,防汛人員有點著急,塌陷塘的岸邊有點混亂。老楊打電話過去問,火葬場那邊說車子早已經派出來,怕是壞在半路上。老楊說,你們不能重新派一輛車子嗎?那邊說,火葬場就這一輛破車。老楊問,就一輛破車你們怎么工作呀?那邊說,一般都是死人家屬找車子送過來。黑頭的尸體運不走,塌陷塘的岸邊不安寧。老楊去找趙心亮協商,想用他的車子把黑頭送往火葬場。老楊走過去,扯拉一把趙心亮的衣服。趙心亮張開淚眼看一眼老楊。
老楊說,你總不能這么一直哭下去吧?
老楊說,黑頭總不能這么一直擱在這里吧?
老楊說,你用車子把黑頭送去火葬場吧?
趙心亮停止哭,不要別人插手,一個人去抱黑頭的尸體,一個人去拉開駕駛室車門。一個活人去抱一個死人原本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黑頭比趙心亮的個頭高、身子胖,更是不容易。不知道趙心亮哪來的一股子力氣,硬是把黑頭塞進駕駛室的座位上。老楊要派兩個防汛隊員跟過去,沒人敢上車子防汛隊員說,趙師傅這樣的一輛破舊車子,這樣的一副迷糊狀態,誰敢上他的車子呀?要是車子翻到堤壩下面去呢?要是車子翻到淮河里去呢?就是不翻到堤壩下面,就是不翻到淮河里去,誰敢保證他在半路上不與別人的車子撞上?經過防汛隊員這么一提醒,老楊想一想是有點不放心,想去制止趙心亮已經來不及。趙心亮把車子開上堤壩,并沒有像人們擔心的那樣把車子開得飛快。這一刻,一輛破舊的車子在趙心亮的手下不再是一匹脫韁的野馬而是一頭牛,一頭慢吞吞的黃牛,邁開四只蹄子,一步一步地往前走,比人走路的速度快不到哪里去趙心亮這樣開車是在考驗防汛隊員的耐心與良心淮河堤壩東西走向,大致是一條直線。卡車沿著淮河堤壩從西往東開,防汛隊員一直能看得見卡車屁股。隔一會看過去,卡車晃動著屁股在前面,隔一會看過去,卡車晃動著屁股還是在前面。在防汛隊員的心理煎熬中,卡車屁股搖晃在堤壩上,搖晃在視線里,像是能永遠這樣搖晃下去。
黑頭死后第三天火化。

盧西安·弗羅依德作品-14
黑頭火化這一天,火葬場沒去幾個人。我,老宋,趙心亮,黑頭娘,加上黑頭的三個遠房親戚,再加上廠職工醫院里的兩個醫生,一共不足十個人按照國家勞動條例規定,職工在上班的路上出事故算是工傷,在下班的路上出事故不算是工傷。不說黑頭是廠里的一名臨時工,就算是一名正式工,事故是出在下班路上,都不能算工傷。黑頭死得有點不明不白。總廠工會(工會是負責職工傷亡后事的辦事部門)不出面去火葬場,粘土礦也不好出面去火葬場。俗話說,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總廠和粘土礦都害怕黑頭家人找后賬。好在車隊在用車上睜一只眼睛閉一只眼睛,趙心亮開著一輛破舊的卡車,來來回回跑火葬場好幾趟。這幾天,車子在半路上一次毛病沒出過,像趙心亮一樣,黑頭一死,變成一副隨和的樣子。車通人性,人通德性。趙心亮不多言不多語,車子不快不慢地開。黑頭娘上車,趙心亮去攙扶;黑頭娘下車,趙心亮去攙扶。其他人都站在車廂里,只有黑頭娘一個人坐在駕駛室。黑頭火化后,趙心亮去接骨灰盒,接過來一把抱懷里。骨灰是暖的,趙心亮的懷抱是暖的。黑頭娘不哭,趙心亮不哭,在場的其他人卻一律地哭。
趙心亮說,徒弟呀,我們回家。
黑頭娘說,兒子呀,我們回家。
廠子附近有一座丁家山,一半長石頭,一半長樹木,廠里人死后都往那里埋。丁家山是附近農村的,埋一個死人,要花一筆錢。這筆錢也是趙心亮出的。趙心亮說,我倆師徒一場,這筆錢該我花。黑頭在監獄省吃儉用留存一筆錢,這筆錢正好夠花在火葬場。一塊地方,一堆土,黑頭的骨灰就這么安放好。
大前天救護車把我送進人民醫院,做過一番檢查后,醫生說你身體各項指標屬于正常,可以回家休息了。那個擺渡人到醫院,又是嘔吐又是頭暈,醫生根據檢查的結果說他有中度腦震蕩。落一次水怎么會有腦震蕩呢?醫生說可能是小筏子碰著頭,或者是木棹打著頭。那么一瞬間的事情,沒人看清楚,也就很難診斷出真正的原因。那人不清楚什么叫腦震蕩,躺在病床上不斷地喊叫說,我的腦子壞了,我活不成了,我要死了。醫生說,你的腦子真要壞掉了,你就喊叫不出來了。那人伸手摸一摸頭腦,說我頭疼,不是腦子壞掉了是什么?醫生扒開他的頭發,發現他的頭上鼓出一個青紫色的血包。護士過來替他的血包消炎。醫生說,這個血包要是往里鼓,你的腦子怕是真要壞掉了。那人問,血包往里怎么鼓?醫生說,血包往里一鼓,還不鼓進你的腦子里?那人問醫生,聽你這么一說,我頭上的血包往外一鼓,還鼓出一個好來了呢?
老楊一聽說我要出院,趕緊打電話跟醫生說,曹干事不慌出院,還需要在醫院多觀察半天。醫生問老楊,你是醫生,還是我是醫生。醫生的意思是,聽我的還是聽你的。老楊說,你們醫院要多少錢,我們廠子里出。老楊這么要求醫生是有其目的的。在老楊的眼里,我落水與黑頭不一樣。黑頭落水是在下班的路上,我恰恰是在工作的路上。黑頭坐小筏子是回家,我坐小筏子是去接飯菜。這么一來,同樣是坐小筏子,同樣是落水,我與黑頭就有了本質性的差異。黑頭落水身亡后,老楊當時在電話里向廠黨委書記老高作了專門匯報,兩人統一口徑,黑頭不能算工傷。我多住半天醫院。最先是老楊帶著兩名防汛隊員代表廠防汛指揮部來醫院看我,吃的喝的買一袋子。吃的是水果,喝的是罐頭。那年月,幾斤水果、幾瓶罐頭就是探望病人的最佳禮品。老楊吩咐我說,你出院好好地休息,什么時候能上堤什么時候上堤,什么時候想上堤什么時候上堤。接著是老高帶著兩名機關工作人員代表廠黨委來醫院看我。一個是廠組織部干事,一個是廠工會干事。老高吩咐我說,你出院好好地休息,能上堤就上堤,不能上堤換別人。最后是老宋帶著兩名團員干部代表廠團委來醫院看我,兩位都是女孩子。老宋吩咐我說,要是今天晚上不能出院,她倆就留在醫院看護你。在醫院里,老宋沒問黑頭落水的事情,也沒說黑頭的其他事情。但我知道黑頭落水這件事情已經埋藏在老宋心里,遲早是要過問的,只是在醫院里時機不到罷了。老宋的眼淚在眼眶里隱忍著,一滴沒有掉下來。
黑頭的喪事就是老宋一手操辦的。
我就是出院,也完全可以不參加黑頭的喪事。但我躲避在宿舍里休息不安,連夜里睡覺都是噩夢連連。翻船落水的那一幕,像是一把水草似的糾纏著我。我越是掙扎,噩夢纏繞得越是緊迫。在現實中,翻船落水的那一幕我肯定沒有任何記憶。可是在噩夢中,翻船落水的那一幕卻是花樣繁多,層出不窮。在現實中不能理解的事情,在噩夢里卻做出一番解釋。比如說,一個暗藏的漩渦真的能夠使小筏子翻沉嗎?在噩夢里,我就看見一條水龍,青面獠牙,怪異多端,它在塌陷塘的水面下先是攪動幾下尾巴,形成一個很大的暗藏漩渦,而后張開血盆大嘴從水面下沖上來,連著小筏子,一下子把我們三個人一并吞嘴里。小筏子木質堅硬,吞咽不下,水龍一張嘴,一頂舌,一吐氣,把小筏子,還有我,還有擺渡人,一下子吐出來。我與擺渡人活著,黑頭落進水龍的肚子里。在另一場噩夢里,水龍變成一頭巨型鱷魚,“撲楞”一下,從小筏子旁邊猛然躥出來,先是掀翻小筏子,而后一口咬住黑頭的一只腿,使勁地往水下拖。黑頭喊叫著,兩只手在水面上亂撲騰、亂抓撓。落水時我離黑頭最近,黑頭一把抓住我,連著我一起往下水里拖。眼看就要悶死在水里時,打一個冷噤我醒過來,我的兩只手捂在胸口上面,胸悶難受得喘不過來氣。這個噩夢告訴我,落水的那一刻黑頭伸手抓我不是搭救我,而是拖累我。
在現實中,黑頭真的拉過我嗎?或者說黑頭拉我真的是想連著我一起拖下水?
另一場噩夢或許更接近事實本身。塌陷塘的水面下沒有水龍,也沒有鱷魚,就是一個暗藏著的漩渦。漩渦在水面下暗藏著不動,悄悄地等待著獵物接近。風平浪靜,陽光明媚,水底一片五顏六色,像是一處海底的珊瑚礁,不時地變換著形狀,不時地變換著色彩,鬼魅似的,具有欺騙性。擺渡人搖著小筏子慢慢地行駛過來,剛剛接近漩渦的邊緣,它猛然間收斂起笑臉及色彩,復原兇殘的面貌,旋轉起來,流動開來,一下子冒出水面,沖翻小筏子,擺渡人被甩出漩渦外沿,我被甩出外沿,黑頭被甩出外沿。我們三人不同的是,擺渡人所處的位置,漩渦的水流是往外旋轉,我所處的位置,漩渦的水流也是往外旋轉,黑頭所處的位置,漩渦的水流卻是往里旋轉。從水面的位置看,擺渡人離漩渦中心最遠,我離漩渦中心最近,黑頭夾在我倆中間。結果,我跟擺渡人逃脫一死,黑頭吸進漩渦里。
在這場噩夢里,漩渦本身是水妖變化的。她抓住黑頭的一瞬間,我看見了她的一張陰險笑臉,我聽見她的一聲刺骨笑聲。
安葬下黑頭,從丁家山回頭,老宋跟我說,曹干事,你晚上去廠團委辦公室一趟,我找你問一件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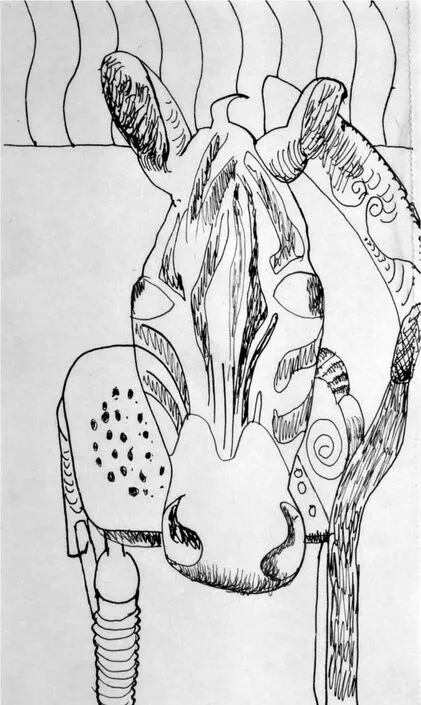
盧西安·弗羅依德作品-15
七
老宋說,我倆今晚打開天窗說亮話,我想幫一幫黑頭。怎么幫黑頭,你心里比我明白。
怎么幫黑頭,其實我當時心里真的不明白。
老宋說,黑頭死掉了,幫黑頭也就是幫黑頭娘。
黑頭一死,黑頭娘怎么生活,這是每一個人都要去想的。
老宋說,幫黑頭,也是為了黑頭的名譽。
老宋說話,我聽著。我不說話,是因為我不知道該說些什么,是因為我不清楚老宋找我談話的真正意圖。
廠團委辦公室是兩間房屋相連著的。外一間房屋的正中央,擺放著一張乒乓球桌子,四周墻上掛滿各種錦旗與獎狀。我跟老宋的兩張辦公桌子擺放在里一間房屋里。老宋關上外間的辦公室大門,關上里間的辦公室小門,我倆各自坐在屬于自己的一張辦公桌子前面,面對面,眼對眼,開始私密而漫長的談話。
老宋說,我作過初步調查。你們落水時,老楊在帳篷里,他沒有看見小筏子翻沉,不可能看見你們當時落水的情況。
老宋說這句話的意圖很明顯——老楊說他看見落水時“黑頭沒有搭救我”是虛假的,其反面指向就是落水時黑頭救了我。
老宋說,幫黑頭的關鍵還得依靠你。

盧西安·弗羅依德作品-16
老宋找我談話的核心內容漸漸地顯露出來,我不得不說話。
我問老宋,你查沒查著是哪一個防汛隊員看見黑頭搭救我?
老宋說,不是我們的防汛隊員,是五臺泵的一名職工。
我問,這個五臺泵的職工怎么說?
老宋不愿回答“這個五臺泵的職工怎么說”。老宋說,還是你自己先說一說當時落水的情況吧?
我跟老宋說實話。我說我當時的頭腦一片空白,什么都不知道。
老宋的表情有一些失望,遲疑一下說,你的“頭腦一片空白、什么都不知道”也是一種情況嘛,最起碼你沒有否定黑頭搭救你的可能性。
我說,黑頭到底有沒有搭救我,看來得由別人下斷語,我下不了。
老宋說,這個斷語你自己怎么就下不了呢?
老宋這是在明確地暗示我,想讓我承認黑頭搭救過我。
我說,我要說黑頭沒有搭救過我,可能我是昧良心;我要說黑頭搭救過我,事實上我確實不知道。
跟老宋的這次談話,我反復強調事實這個詞。但我知道事實這個詞往往最靠不住,也是最事實不了的。
老宋說,另一個事實是,黑頭死了,你活著。
我說,還有一個事實是,黑頭死了,那個擺渡人同樣也活著。
老宋跟我談話,心態有那么一點復雜。同樣我跟老宋談話,心態也有那么一點復雜。老宋最后說,我不想看著黑頭就這么不明不白地死去。
老宋找我談話之前,找過老楊,找過老高。老宋想以組織的名義,上報黑頭為見義勇為者,也就是說黑頭不是自己落水而死的,是因為搭救我而死的。老楊一口回絕老宋的想法,批評老宋說,你這樣做簡直是胡鬧,就算我在帳篷里沒有看見黑頭有沒有搭救曹干事,黑頭也不可能搭救過曹干事。老楊說話主觀武斷,想徹底打消老宋的這種想法。老宋不聽老楊的話,說老楊,你只要說當時在帳篷里沒看見就好。老楊知道老宋找過那位五臺泵職工。待老宋離開,老楊去一趟五臺泵,讓那位五臺泵職工不要再說看見過黑頭搭救我之類的話。老楊與那位職工一起站在五臺泵旁邊,眼睛眺望著塌陷塘的一片白茫茫水面。老楊小聲地問一句,你當時真的看見黑頭伸手搭救曹干事啦?那位職工一愣神,回答說,可能是我眼睛看花了。老楊“哈哈哈”地大笑起來說,我說嘛,這么遠的一大段距離,沒人敢說能把當時的情況看清楚。
老高的表態更鮮明。老高跟老宋說,莫說當時的情況沒人能夠說清楚,就算黑頭真的搭救了曹干事,我們也不能把黑頭當作見義勇為者報上去。老宋不解地問,為什么?老高說老宋在政治上太幼稚黑頭是一個什么人,你不比我心里明白嗎?老宋說黑頭是一個在服刑期間表現比較好,提前刑滿釋放的勞改人員。老高問,你說他在服刑期間表現比較好就表現比較好啦,我問你是代表哪一級組織?老宋說,省第三監獄里的管教干部就是這么說的。老高問,你手上有他們寫出的結論材料嗎?老宋說,黑頭五年刑期三年釋放就是最好的材料。老高說這就是你的證據嗎?要不我怎么說你在政治上太幼稚呢?前幾年“嚴打”有些做過頭,這兩年逐步地在調整,逐步地在改正。不要說黑頭判刑五年提前釋放回來,就是那些判刑十年八年的也有陸續釋放回來的。不說別的單位,就是我們廠就有四五個。你宋書記不會說不知道吧?

盧西安·弗羅依德作品-17
高書記的基本結論是,一個勞改釋放犯到什么時候都是一個勞改釋放犯,都不能跟一個正常人相比較;一個勞改釋放犯提前釋放不能說明他無罪,只是說明罪輕罪重罷了。
老宋說,看來只有先去證明黑頭被判刑是冤屈的?
老高警覺地問,你還想出什么幺蛾子?
老宋還是說那么一句老話,我不想看著黑頭就這么不明不白地死去。
緊接著出場的是趙心亮。趙心亮出場是他自愿的,還是老宋鼓動的,我就不太清楚了。從時間順序上來看,趙心亮這么做,最起碼老宋是知道的。就在老宋找我談話的第二天,趙心亮手里拿著一沓材料找廠里。這沓材料有些泛黃有些發烏,還是那一年黑頭被“嚴打”判刑的時候寫出來的。黑頭作替罪羊,遭廠里罰款,趙心亮去找廠里,沒人理會他。黑頭遭嚴打被判刑,趙心亮去找廠里,更加理直氣壯。趙心亮在材料上不僅承認偷輪胎,還承認以前盜竊的所有事。某年某月,盜竊車隊的哪一種物件,賣給哪一家廢品收購站,一筆一筆,材料上寫得清清楚楚,容不得別人去懷疑。廠里這一次很重視,看來真的冤屈了黑頭被判刑。廠警隊五花大綁地把趙心亮押解去公檢法機關。公檢法機關不接受趙心亮,說馬建軍的判決書生效,已經把他秘密押解去某處監獄服刑。也就是說,黑頭被判刑是鐵板釘釘無法更改了。趙心亮被廠警隊帶回頭,成為一個良心上被判刑的勞改犯。黑頭三年刑滿,趙心亮的良心徒刑沒滿。黑頭一死,趙心亮的良心徒刑更加沉重,更是遙遙無期了。
老高對重新上訪的趙心亮說,當年我們廠領導的態度就是明白的,現在要找你自己去找公檢法機關吧。
趙心亮開著那輛破舊的卡車,去市里,去省里,跑了好多趟,跑了好多天,一點頭緒都沒有。市里跟趙心亮說,黑頭現在是死無對證,你說這件事我們怎么去調查?省里不具體表態,把趙心亮遞上去的材料,原封不動地批轉回去,要求市里來處理。趙心亮回頭找市里。趙心亮說,只要你們說黑頭是無罪的,我愿意重新蹲五年勞改。市里說,這件事我們現在處理起來左右為難,要說當年我們沒有抓錯,馬建軍遇見嚴打被判刑五年算就是正常的;要說我們當年抓錯了,現在要我們去處理你,或者說要我們說馬建軍無罪都是不可能。市里說,現在不是嚴打的時候,像你這樣小偷小摸,我們拘留你十天半個月也就差不多了。但是在全市范圍內因“嚴打”釋放出來的成千上萬勞教人員,我們能去說他們其中的誰個無罪嗎?要說有錯誤,也是那個時代有錯誤,不是哪一個部門,哪一個人所能承擔得了的。
老宋見趙心亮上訪沒有結果,還是回過頭來找我,讓我承認黑頭搭救過我這件事。我依舊用一句老話對付老宋。我說,我當時頭腦一片空白,什么都不知道。老宋說,你就不去想一想黑頭死得冤屈不冤屈,你就不去想一想你的良心安不安?老高知道老宋一直糾纏我不放,跟我說,按照當時的實際情況,你說你“當時頭腦一片空白,什么都不知道”是最合情合理的。我說,我當時確實是頭腦一片空白,什么都不知道。老高說,廠黨委會全力支持你的這一說法。
老高向我透露說,看來廠團委是應該做一些調整了。一個團委書記整天這樣子,還怎么有精力抓工作。老高鼓勵我說,曹干事,你現在多做一些團委工作,有些工作你完全可以獨當一面抓起來。老高這么說話,一方面是要我咬緊牙關,繼續說“我當時頭腦一片空白,什么都不知道”,另一方面暗示我、許諾我廠團委調整在即,黨組織會重點考慮我安排我。
八
第二年的清明節前,我離開陶瓷廠。一位大學同學在南方的某座城市給我找一份臨時性工作,我辭職去了那邊。廠里所有人都明白,我去南方是逃避。我不愿意在黑頭這件事情上沒完沒了地糾纏下去。我身心疲憊,噩夢連連。我不想因為黑頭毀掉我自己的一生。有一次,我去市水利局找到一位水泵方面的工程師。我問他,五臺水泵一起開動起來,在水面下形成的吸引力到底有多大。我想弄清楚,黑頭落水離水泵幾十米遠,是一種什么力量促使他一下子到達水泵的渦輪下面。工程師想一想說,這個問題很復雜,要看水位的深淺,要看水流的走向,還要看人落水的方位,這是一個很復雜的力學問題,不做實驗恐怕是很難一下子說清楚的。這位工程師是我同鄉,黑頭的事情在市里傳播得沸沸揚揚,他想從我嘴里知道得更詳細。這位工程師問我,你是希望我說水泵有這么大的吸引力呢,還是希望我說水泵沒有這么大的吸引力?同鄉或許看出我心懷鬼胎,我卻笑一笑沒回答。有一天,老宋跟我閑聊,說到黑頭的水性好,扎猛子時間長。老宋說他十四五歲的時候,淮河就能輕松地游過去、游回來,要是憋足一口氣,差不多一個猛子都能扎幾十米遠。我問老宋,有沒有我們落水到水泵那么遠?老宋“咯噔一聲就不去說話了。老宋說這話,是無意,還是有意?又一天,趙心亮跟我神秘地說出黑頭的身世。原來黑頭不是黑頭大(爸)親生的。黑頭娘懷的是誰的孩子,黑頭娘一輩子不愿說出來,黑頭大(爸)一輩子不知道。趙心亮提示我說,曹干事你看黑頭跟老宋長得像不像?我吃驚地問趙心亮,你說這話的意思,難道黑頭跟老宋是兄弟倆?趙心亮說,我聽別人胡亂猜測的,我也說不準?我故意搖頭否認說,我看他倆長得一點都不像。趙心亮說,他倆要不是兄弟倆,老宋會為著黑頭的事情這么下力氣?我說,你不是也為著黑頭的事情沒少跑市里省里嗎?趙心亮說,我跟黑頭不一樣,是師徒倆,再說老宋整天跟在我后面盯得緊,不跑也由不得我呀。我說,老宋跟黑頭是鄰居,起小一塊長大,情感上還是不一樣。趙心亮說,老宋這個人你我都是看不透?我問,會有什么看不透的呢?趙心亮說,老宋打著黑頭的旗號整天去老高那里糾纏來、糾纏去,我看他是想在政治上有企圖。我說,就怕糾纏得老高心里煩,讓他去下粘土礦。趙心亮說,就怕老高有這個心沒這個膽。我說,難道老高怕老宋不成?趙心亮說,老高不怕活著的老宋,卻怕死掉的黑頭。我說趙心亮,你說話越來越玄乎,我聽不明白。趙心亮問,死掉的黑頭你怕不怕,反正我是害怕的。我想一想說,我也害怕。
有一種說法很快在廠子里謠傳開來,說黑頭屬于自殺身亡。理由是,依據黑頭的身體和水性,這么一個漩渦根本不會置黑頭于死地。所以黑頭死亡的原由只有一個,自己不想活了,采取這么一個貌似合情合理的自殺方式。廠里出現這種謠傳,老楊沒去制止,老高沒去制止,像是連著老宋、趙心亮都跟著默認了。有一天,我在廠子里見著黑頭娘。——她每月按時來廠里一次,到退休辦領取生活補助金。黑頭娘見人就問,你說我家兒子為什么要自己去死呢?人們說,這個問題只有去問你兒子。黑頭娘說,他要是沒死,我去找他問一問,你說現在我去哪里問他呢?人們說,你兒子不死也不會有這個問題呀?我遠遠地躲避開黑頭娘,我也不知道該怎么回答這種話。人一死,與之相關聯的許多問題都跟著死掉了。真是死無對證呀!我感到渾身一下子輕松許多。
防汛結束后,市里分到廠里一個防汛先進基層單位名額,老楊當家給了粘土礦。
春節前,趙心亮最后一次去省城上訪,卡車拋錨在半路上,回頭車隊把一輛新購買的卡車交給他。趙心亮從此當上一名司機,天天去外面拉貨,很少回廠里。司機去外面拉貨,廠里按天有一份補助,此外還有各種各樣看不見的一份好處,收入比當維修工高不少。從分配到車隊的那一天起,趙心亮就跟車隊隊長王懷禮吵嚷著想當卡車司機,不愿當一名維修工,現在總算如愿以償地實現了。
春節后,廠里調整中層領導班子,老宋調到廠財務科任科長,另外從基層團總支提拔一個人過來任廠團委副書記,主持廠團委工作,我依舊是干事。老高說我還年輕,需要再鍛煉兩年才能勝任廠中層領導崗位。事后我常常反問自己,要是當初廠里安排我當廠團委副書記,我還離開陶瓷廠嗎?我不敢肯定,真的很難去說。當年,老高為何在提拔我做團委副書記的時候食言呢?
后 記:
轉眼我離開陶瓷廠已經二十個年頭。這二十年,我不與陶瓷廠的任何人往來,我也沒有回過陶瓷廠一趟。我想在頭腦里漸漸地模糊我在陶瓷廠待過的那段日子,更想在頭腦里一下子刪除黑頭這件事情。事實上卻辦不到。隨著時間一步步往前推移,經過歲月打磨的許多事情會越來越清晰,會越來越堅硬,硌著你,錐著你,逼著你不由自主地重新去打量,重新去審視。于是我就像一個投機取巧走過捷徑的人,現在回過頭去把繞行過的道路重新走一遍,老老實實地記錄下這段經歷、這則故事。我這么做還不是為了黑頭早已逝去的生命,而是為了我自己。今年清明節前,我打算回一次陶瓷廠,回去看一看那一片我生活不到兩年的地方。前些年國有企業紛紛倒閉,陶瓷廠也不能幸免。丁家山現在還存在嗎?——那年安葬黑頭的時候,村民就在丁家山上開山炸石頭。黑頭的那座墳墓現在還存在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