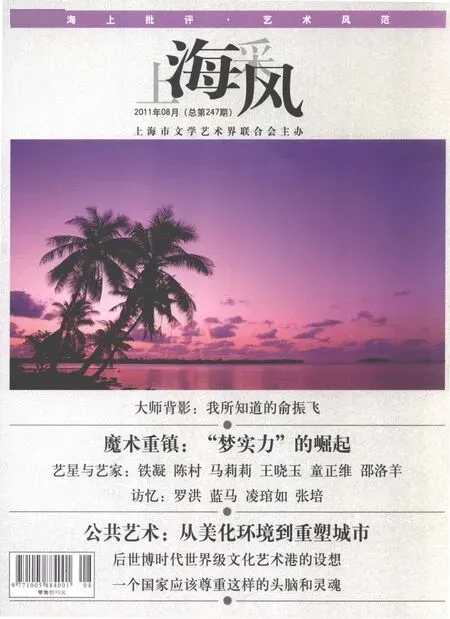馬莉莉:為保護“上海話”大聲疾呼
文/信 芳

“馬莉莉是當代滬劇藝術的重要代表。她很好地繼承了前輩演員的藝術遺產,又努力吸收現代劇場藝術,把握每一出戲的美學格調,深入刻畫角色性格,并把這一切都熔鑄成自己的生命形態而投入舞臺,使滬劇至今沒有出現衰弱。”這是1991年馬莉莉從藝30周年舉辦個人專場演出時,著名學者、時為上海戲劇學院院長余秋雨先生贈與的祝詞。
晃眼20年過去了,日前我見到她,再次提及這段祝詞,已經漸漸淡出滬劇舞臺的馬莉莉不由激動起來,當年“風華正茂”的歲月似又重現在眼前,但又表現出難以抑制的憂心。她毫不諱言:今昔已不能同日而語,現今滬劇出現“頹勢”,其市場“萎縮”已是不爭的事實。當然,作為滬劇這個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的傳承人之一,她豈能甘心?為“傳承”作了大量調查和研究后,她發現根本原因是:滬劇所依托的基礎——上海話已經開始“退化”。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為此,在上海市政協會議上,馬莉莉委員不由大聲疾呼:上海話,要盡快地保護和規范!
從“學藝登臺”到“嶄露頭角”
一個隨團的小演員成長為一位滬劇表演藝術家,馬莉莉在滬劇藝術的園地里耕耘了50個春秋,如今雖已過花甲之年,但她風采依舊,親切的笑容、甜美的嗓音讓人感到既熟悉又親切。回想當年學藝登臺、嶄露頭角的情形,平時信奉“寧靜致遠”的她,似乎也不能平靜,塵封的記憶又被打開。
從小聰穎活潑的馬莉莉,因母親特別喜歡滬劇的緣故,她對滬劇也情有獨鐘。“記得還是在幼兒園時,其他小朋友都唱歌、跳舞,我就一本正經跟老師說,要唱一段滬劇給大家聽。可以說,我從小對滬劇就很癡迷。”馬莉莉回憶說。
就在馬莉莉小學畢業那年,上海楊浦區戲曲學館來校招生。全家人為她該選擇什么樣的劇種而爭論,這時,酷愛滬劇的母親說話了:“女兒是我的,我作主,就考滬劇!”馬莉莉考進了學館,開始了學藝生涯。
最初的學藝是艱苦的,練功苦,生活條件更苦。當時正遇上三年自然災害,食物緊缺,正處于長身體階段的馬莉莉總是感到饑腸轆轆,但練功從不偷懶。還是應了那句話,機會給了有準備的人。畢業后,馬莉莉跟著愛華滬劇團轉戰數個大劇場。那年,愛華滬劇團正在演出《南海長城》,一位扮演甜女的演員突然因病無法上臺,當時離開場還有兩個小時,袁濱忠老師心急火燎地走進化妝間,來到馬莉莉身邊:“莉莉,你上吧!”馬莉莉又開心又惶恐地上了場。“當時我還沒有舞臺經驗,一邊演,一邊竭力掩飾自己的緊張,給自己打氣,總之不能讓老師們失望!”
這場讓領導和同事們捏了一把汗的演出就這樣被演下來了,馬莉莉說,“接下來的演出,我一天比一天演得好。甜女是我隨團以后,第一個有名有姓的角色。”
十年文革,上海幾十家劇團或被遣往干校,或遭解散,唯有愛華滬劇團得以幸免,原因歸功于它有一出劇目《紅燈記》。而這出戲對馬莉莉也有特殊的意義。1966年,她被選上飾演B角李鐵梅。馬莉莉明白這是她的重要機遇,所以當A角演出時,她晚上拼命地看戲,白天練功時又拼命地琢磨。機會來了,一個酷暑下午,日場《紅燈記》讓她上演。“李鐵梅”首演是韓玉敏老師,她的表演有口皆碑。馬莉莉平時一直關注老師的表演,從模仿到體會,到自己登臺演出。第二年,她欣喜地獲得了和自己老師韓玉敏、袁濱忠同臺演出大戲的機會。韓老師已“升格”演李奶奶,馬莉莉演李鐵梅。通過與兩位老師的合作,她的演藝大大長進,不僅從老師身上學到了表演,更學到了自信。《紅燈記》是馬莉莉平生演出的第一部大戲,自此她一發不可收,在演藝道路上越走越寬廣。

《霧中人》中飾白靈
從“英雄花旦”到“演啥像啥”
1973年,愛華滬劇團與上海市人民滬劇團合并成上海滬劇團,馬莉莉隨團加入,這是她藝術路上的一個轉折點。上海滬劇團薈萃了眾多滬劇名家,有丁是娥、解洪元、邵濱孫、石筱英、凌愛珍、王盤聲、韓玉敏等,對馬莉莉來說,不僅能向前輩學習更多,同時為她提供更大的施展舞臺。并團不久,她就出演了《沙家浜》中的主角阿慶嫂,她的舞臺形象顯出熠熠光華。
粉碎“四人幫”后,戲曲舞臺開始復蘇,而馬莉莉迅速進入了藝術生命的高峰期。《張志新之死》是她的一個重要劇目。這個根據張志新烈士的事跡改編的戲演于1979年,創作過程中,馬莉莉與編劇余雍和、導演楊文龍等專程去沈陽采訪,為了體驗角色,還帶上鐐銬走進當年關押張志新的監房。正因為有了深切的體驗和強烈的創作激情,所以在舞臺上,她把張志新的高瞻遠矚、剛毅不屈刻畫得特別真切動人。
這一時期,馬莉莉連續扮演了韓英、陳芳芳、張志新、白蓮花等一批叱咤風云的女英雄,因此人們戲稱她為“英雄花旦”。但馬莉莉懂得,扮演英雄,不是簡單地作英雄狀便可奏效的,重要在于挖掘并展現出英雄人物性格中的豐富內涵。
1982年,首任上海滬劇院院長的丁是娥決定把曹禺名著《日出》搬上滬劇舞臺,并且指定馬莉莉扮演主角陳白露。這對“英雄花旦”可是一個嚴峻的挑戰。陳白露是一個舊時代的人物,她集大學生、交際花于一身,是個性格復雜的女性。馬莉莉對此很不熟悉,又無法去體驗。然而,她勇于去迎接這一挑戰。她大量翻閱資料,反復揣摩劇本,向曾經演過陳白露的話劇前輩白楊、嚴麗秋、導演凌琯如等請教,經過艱苦的藝術創造,終于使陳白露這個角色在滬劇版中站立起來。
《日出》的成功是馬莉莉表演和演唱藝術趨于成熟的一個標志。丁是娥稱贊她“演啥像啥”,這是老藝術家極高的評價。此后,她的藝術創造力更如瀑泉噴涌而出。1983年8月,創作演出了現代戲《尋娘記》,馬莉莉在劇中扮演女主角梅莘。這位具有心靈美的女醫生,把無依無靠的奶娘接回家中贍養,而其丈夫卻對此大為不悅。全劇通過尋娘、趕娘、追娘、認娘等一系列戲劇情節,鞭撻了社會上某些丑惡現象,歌頌了尊老愛老的美德。馬莉莉塑造的梅莘形象真摯、熱情、親切,具有強烈的感染力量。演出后深受歡迎,連演280多場,觀眾達20余萬人次,后來又拍攝成電視劇《屋檐下的白玉蘭》,影響很大。
此外,她在《啼笑因緣》中一飾兩角,同時扮演沈鳳喜與何麗娜兩個面貌相似,但身份、舉止、性格迥異的女性。她還在《雷雨》中出演主角繁漪。1988年赴香港演出,香港觀眾稱她有丁是娥的神韻。頻繁的藝術實踐,辛勤的藝術創造,使馬莉莉由此成為當時滬劇界最有影響的一位中年演員。而馬莉莉更是在政治上嚴格要求自己,努力使自己成為黨的文藝工作者,1986年7月1日,她光榮入黨。

《宋慶齡在上海》馬莉莉(左)飾宋慶齡,華雯(右)飾宋美齡

《風雨同齡人》馬莉莉飾鐘佩文、呂賢麗飾陳潔
從喜摘“白玉蘭”到“梅花”映山紅
一個優秀的演員,總是不斷地超越自我,探索與創造永無止境。而對馬莉莉來說,她的藝術生涯還伴隨著改革開放的腳步。1989年,成立“直屬團”,開創了“文企聯姻”的先河;1993年,她當起了“自收自支”的浦東分院院長;1999年,她又敢吃螃蟹,成立了“馬莉莉工作室”。而難得的是在這三個節點上,她均向觀眾交出了滿意的答卷。
1989年,馬莉莉的直屬團排演新戲《霧中人》。這個戲題材獨特,描寫了中國人民志愿軍的戰俘歸國后的坎坷人生。馬莉莉以前扮演的張志新、陳白露等人物,一般性格比較明朗并富有造型感,《霧中人》中的女主角白靈卻迥然不同。她在戰俘營中不屈不撓,九死一生,但遣返回國因有變節嫌疑而屢遭顛沛,后在山村擔任教師,蒙冤受屈三十年,默默寡言,性格深沉。馬莉莉緊緊抓住白靈性格中一個“韌”字,表現她對黨的事業的無限堅貞。表演上改變了以往注重外部造型的方法,更多地運用眼神及細膩的情緒變化來刻畫人物,在藝術創造上實現了新的自我超越。當年6月,上海白玉蘭戲劇表演藝術獎首次舉辦,評委會以“全票”將主角獎的桂冠授予了成功飾演白靈的馬莉莉。同年10月,《霧中人》應邀參加1989年上海文化藝術節,又喜獲優秀成果獎。
1993年,出任上海滬劇院浦東分院院長的馬莉莉推出《風雨同齡人》。新戲講述的是,在改革開放的年代,昔日插隊落戶的知青鐘佩文,以美國夢達公司總經理的身份重返故土,到浦東投資,而在談判桌上重逢了當年的老同學、戀人歐陽杰。馬莉莉扮演的鐘佩文是一位從泥濘的人生路上走過來的“不惑”女性,下鄉、返城、出洋、回國,愛情的挫折、家庭的破碎、事業的艱辛,酸甜苦辣鋪滿了她從失望到彷徨到重建希望的人生之路。同為新中國的同齡人,馬莉莉將鐘佩文回國尋找失落的夢的復雜心態,通過真摯而細膩的表演,感人肺腑的演唱,將她演繹得親切而感人,強烈地撥動了同齡人和廣大觀眾的心弦。同年《風雨同齡人》赴福州參加第三屆中國戲劇節并獲創作獎、優秀演員獎。次年,馬莉莉又憑此戲摘走了第十一屆中國戲劇梅花獎。
1999年,馬莉莉組建的“馬莉莉文化工作室”一眼看中了《宋慶齡在上海》這個劇本。要在滬劇舞臺上首次塑造宋慶齡,她深感壓力不小。宋慶齡的形象那么深入人心,滬劇怎么演?馬莉莉又怎樣演?化妝師經過幾次造型,終于在宋慶齡和馬莉莉之間準確地尋找到了異同點和契合點,“很像!”首先外型在同事中獲得了通過。但馬莉莉很清楚,僅此遠遠不夠,要展現國母高風亮節的情操和胸懷,更要捕捉宋慶齡特有的氣質、風范和神韻。為此,她翻閱了大量有關宋慶齡的書籍、資料,由此反復揣摩宋慶齡的舉手投足和音容笑貌。《宋慶齡在上海》表現的是三十年代的往事,但考慮到觀眾對國母的印象大都是建國后的形象,因此在舞臺造型時,馬莉莉有意往宋慶齡的中老年形象靠攏,為的就是讓觀眾在最短的時間內接受“宋慶齡”。她抓住了宋慶齡“從從容容、細語春風”的氣質特征,仿佛生活在宋家的客廳里、花園中,一步一步走進了宋慶齡的世界。“像,像,太像了!”聽到廣大觀眾對她評價時,馬莉莉為自己成功地塑造了一位既偉大又近人的“平民國母”的動人形象而高興。作為她藝術生涯中的巔峰之作,1999年11月,《宋慶齡在上海》赴湖南長沙參加由文化部、中國劇協主辦的第五屆中國映山紅民間戲劇節演出,一舉獲得了編、導、演、音樂、舞臺美術等多項一等獎。
從振興滬劇到保護“上海閑話”
“現在很多上海小囡已經不會講、講不好上海閑話了,這讓我非常擔憂。”在上海市政協召開的專題會議上,兩屆委員馬莉莉一提出這個話題,就引起與會者的熱議。不少委員有了共識:“規范和保護上海話應提上日程,而最重要的,是弘揚上海城市文化,留住城市之魂。”
馬莉莉告訴我,早在上海市政協第十屆三次會議上,她就提交過保護上海方言文化的提案。而它的緣由就是,她看到現今滬劇出現的“頹勢”:目前上海專業滬劇院團僅存3個,編劇缺乏、演員流失,滬劇已大不“景氣”。從表面看,是市場經濟沖擊的因素,但實質是滬劇已缺失了它生存的土壤——滬方言大大的“萎縮”,這才是其根本原因。
“上海母語瀕臨危機!”馬莉莉直言不諱,“現在孩子從幼兒園開始,已不講上海話,而3、4歲是學講話的最好時光。這樣帶來的直接后果就是:很多上海小囡已經不能夠用上海話和別人溝通了。由于移民和外來文化的影響,上海本地青年也慢慢流失了‘母語’。滬劇是以上海話為支撐的,離開了地方語言,離開了聽不懂上海話的觀眾,那滬劇,還有滑稽戲,又怎么能傳承下去,更不用說發展了。”馬莉莉說這話時,語速極快,看得出她的“擔憂”心情。
“保護上海話,其實就是保護上海城市文化,方言是地方文化的載體之一。”馬莉莉舉例說,從某種意義上,中華文化是由各地文化組成的,浙江搞大型活動,必定會有越劇;安徽活動必定有黃梅戲;江蘇的活動必有評彈和錫劇參與。可能我們上海是大都市的原因,卻常常忘了滬劇。由于環境的影響,上海話的市場越來越小,而能講原汁原味的上海話的人更少。而滬劇團——一個完全靠滬語表演的藝術團隊,現在已經很難招聘到發音合格的年輕學員。她苦笑說,近年招來的鄰省學生,進校就得化大力氣學“比外國語還難學”的上海話。
面對現狀,馬莉莉說,與上海政協文化界39位委員自上屆提出提案后,她一直在考慮實施問題。近來她想到有兩個“切入點”,一是她到香港受到的啟發。在香港機場、地鐵、航船上“報站名”,通常用三種語言:英語、普通話、粵語。為什么上海公交軌交等報站名不也用三種語言:英語、普通話,加上海話呢。其二,能否在電視臺和電臺上,每天花半個小時用滬方言播報新聞,以規范、傳播上海話?特別是上海電視每天下午6點有檔“新聞坊”,主要播講上海及各區新聞,且背景是石庫門。我想,這時如能用上海話播報,那真是“形式與內容的統一”,韻味無窮。其實,不少外地,甚至外國來滬工作的人員也有學習上海話的需求,但苦于沒有好的教材。我們如果能在這方面“開綠燈”,那一定有助于規范和保護上海話。
馬莉莉知道,這項看來十分容易的工作卻很有難度。但“作為一種城市文化,上海話不應就此湮沒、變形。”所以,她目前正在考慮,既然這份提案已被上屆評為“優秀提案”,她決心還將聯絡其他委員,將此提案更細化,并且能夠實施。

時任副總理的朱镕基對馬莉莉說:“沒想到你還會唱京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