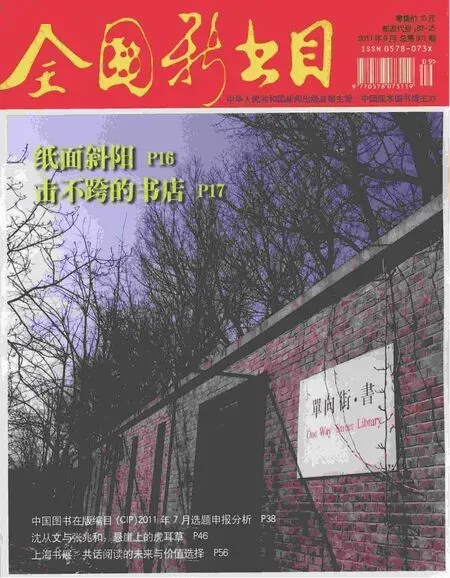書癡說書
⊙

《聽櫓小集》
王稼句著
中華書局 2009.9
定價:24.00元
說舊書
舊書的概念,實在很寬泛,曠古久遠的是,隔日黃花的也是,它們的價值懸殊高下,有版本、藏主、存量諸多因素,或貴如瑰寶,或賤如廢紙。然而時局的安定或動蕩,最為重要,即以蘇州為例,辛亥革命時,乾嘉名人鈔校本俯首可拾;抗戰(zhàn)初期,又有大批珍本古槧散出,價格低廉得難以想象。至文革發(fā)動,天下大亂,愚蠢之事,累累不窮,真匪夷所思,焚書就是其中之一,許多書就這樣灰飛煙滅了。那時的書,不論舊書,還是問世不久的新書,都成了累贅。抄家的,一紙不留,車載而去,也有當場就在門前點火焚燒,熊熊光焰里灰燼飛舞;不抄家的,有的自覺上交,有的偷偷燒掉,有的半夜里打包裝袋扔進河里,也有的依依不舍,就送去廢品收購站,或許尚存一線生機,而收購站收書是秤分量的,凡精裝本,都得將硬面的封皮撕去。書的命運,經(jīng)此一大劫,真是到了窮途末路了。
歷史就這樣開了一個玩笑。進入上世紀九十年代,舊書價值陡然高漲,即以北京嘉德的一次拍賣活動為例,一部百衲本《二十四史》,市場價約二萬,拍賣至十七萬成交;一部《四庫全書珍本》,市場價約三萬五千元,但拍賣以二十九萬定槌。另外,還有一冊宋本蝴蝶裝《文苑英華》,雖是殘本,但在拍賣會上以六十萬起價,終以一百三十萬被一位外籍人士所得。沒有想到,書竟然會與花園別墅或豪華轎車等值起來。線裝古籍如此,民國時出版物也是如此,在中國書店的一次拍賣會上,阿庚編的《死魂靈百圖》起價三千六百元,甚至連印數(shù)甚多的張愛玲《流言》初版本也起價五百元。據(jù)說,在深圳拍賣的新文學初版本,起價都是四位數(shù)。照此算來,如今幾位民國書刊的收藏家,都應該是巨富了。雖然拍賣市場和一般消費市場有一定的距離,但舊書的價值正在飆升,它的商品化程度也將越來越高。當然,這與一九四九年后的歷次運動,特別與文革的舉國焚書,有密切關系。陳登原《古今典籍聚散考》歸納書的聚散有四大原因, 一、受厄于獨夫之專斷而成其聚散,二、受厄于人事之不臧而成其聚散,三、受厄于兵匪之擾亂而成其聚散,四、受厄于藏弆者之鮮克有終而成其聚散 。就一九四九年后的情況來說,這四大原因幾乎都不同程度影響了書的命運,而聚而必散,散而又聚,則又是一條規(guī)律。故當浩劫之后,百廢俱興,書自然也是時來運轉了。
喜歡買書,且再收藏至一定數(shù)量的人,如今都可稱為藏書家,各地舉行名目不同的藏書家評選,標準大凡如此。古人則不然,并不認為藏書者一定是家,洪亮吉《北江詩話》卷三說: 藏書家有數(shù)等,得一書必推求原本,是正缺失,是謂考訂家,如錢少詹大昕、戴吉士震諸人是也。次則辨其板片,注其誤訛,是謂校讎家,如盧學士文、翁閣學方綱諸人是也。次則搜采異本,上則補石室金匱之遺亡,下可備通人博士之瀏覽,是謂收藏家,如鄞縣范氏之天一閣、錢唐吳氏之瓶花齋、昆山徐氏之傳是樓諸家是也。次則第求精本,獨嗜宋刻,作者之旨意縱未盡窺,而刻書之年月最所深悉,是謂鑒賞家,如吳門黃主事丕烈、鄔鎮(zhèn)鮑處士廷博諸人是也。又次則于舊家中落者,賤售其所藏,富室嗜書者,要求其善價,眼別真贗,心知古今,閩本蜀本,一不得欺,宋槧元槧,見而即識,是謂掠販家,如吳門之錢景開、陶五柳、湖州之施漢英諸書估是也。耿文光并不完全同意這個說法,他在《萬卷精華樓藏書記》卷一百四十二里說:此亦大概言之,未可細為區(qū)別。考訂家皆能校讎,收藏家亦深賞鑒。若考校而未能精審,收藏而不擇善惡,皆不可稱家。至于掠販一家,意在漁利,原無關于讀書,然其眼見甚廣,非讀書者所可及。余嘗謂讀書人宜勝書估,今則反是,似藏書與讀書截然兩事。時至如今,更是藏書與讀書截然兩事了,藏書雖多,而從不稍一閱讀者,不在少數(shù),有以藏書裝點居室顯示風雅的,也有以買古刻名鈔顯示富有的。俗話說得好,林子大了,什么鳥兒都有。在這個茂密的書林里,也不都是純粹的讀書人。至于洪亮吉說的數(shù)等里, 掠販家雖多,專業(yè)知識卻淺薄得很,與乾嘉時的書估有天壤之差,并且一蟹不如一蟹,其他諸家更是鳳毛麟角,寥寥可數(shù),且大都借公共圖書館的收藏,作自己的研究,這也是時代使然。
有人說,舊書將會與字畫、陶瓷、玉器等等一樣,成為收藏的熱點,這并沒有什么不好,因為藏書畢竟是風雅的事,附庸風雅總比贊美粗俗要好。藏書既為熱點,買書人和販書人就如逃如逐,如奔如追,撩撲不開,牽挽不住了,書價的行情還將看好,也就有經(jīng)濟實力的較量。再說,舊書也有贗品,但畢竟少于字畫、陶瓷、玉器之類多多,特別是民國刊本,本來價值有限,做贗本反不合算,至多是偽托作者或藏家的簽字、印章而已。由于我既沒有收藏癖,又沒有什么經(jīng)濟實力,對于這個收藏熱,只能持一種旁觀欣賞的態(tài)度,就像有人屬于愛車一族,但只能羨慕而無力購置,那就訂一份《車迷》雜志,煞煞有車的癮。
我雖然沒有收藏癖,但閱肆訪書還是隔三差五的事,凡買得一兩本中意的書,也很會高興一陣子。我所中意的書,也就是實用的書、想要讀的書,這就未必舊書了,有時新的就好于舊的。比如民國年間整理的筆記、別集一類,本來校讎不精,魯魚亥豕的,不及新校點的排印本。新的影印本也好,畢竟有舊版的面貌。有的新印本附有索引,有的還專門印出配套的索引,如中華書局印的《太平廣記》,便先后印過兩本索引,這對我來說,就是有用。再比如珂羅版的畫冊,自然也不及新印的,新印的逼真細膩,與原作更接近。八十年代,書價還很便宜,當時許多筆記、別集還沒有新印本,我就買了一些舊版的來讀,有的便是當年平襟亞們一折八扣的貨色,當買得新書,我便將這些舊書盡數(shù)送人,當然它們曾經(jīng)給我讀過,有的還不止讀過一遍。
或許正是這個緣故,我?guī)缀鯖]有什么舊書,雖然對新文學比較有興趣,但讀的大都是新印本或影印本,因為我不想作什么版本上的研究,如此讀讀,也就可以了。但正像與一個人的交往,時間久了,就會有感情,想知道一點他的過去,這也是很正常的事。因此曾在蘇州古舊書店的樓上,買過一點新文學的初版本、毛邊本,但十幾年過去,總共也沒有多少本。個中原因,主要還是囊中羞澀,收入與書價總是有距離,收入逐年增多,兩者間的距離反倒越來越大,這個收藏舊書的癖好也就難以養(yǎng)成了。
也說常銷書
常銷書的概念,也因時代而不同。科舉尚未廢止的時候,坊肆所鬻除制藝試帖外,如《綱鑒易知錄》、《詩韻合璧》、《廣事類賦》之類,都是州縣書啟行篋中物 ,而以《三字經(jīng)》、《百家姓》、《千字文》為代表的蒙學讀物,更是面廣量大、持續(xù)數(shù)百年而不衰,其他如詞曲、小說、唱本,也有相當?shù)挠?shù),一印再印,可以算作常銷書的。西風東漸,盛行林譯小說,再后來就是新派通俗文學,主要是言情、武俠、奇案、娼門等題材的小說,但也只能說是暢銷,未能持久。五四以后,新文學小說、散文、詩歌陸續(xù)問世,有的名盛一時,印數(shù)也就是幾千冊,遠不及李涵秋、包天笑、周瘦鵑、還珠樓主、張恨水們的鋪天蓋地,自然也不能算常銷。民國期間,真正常銷的,除影印或標點的古籍外,大概還是周越然、林語堂編的英語教材以及《辭源》等工具書。一九四九年后,最常銷的當然是毛選、修養(yǎng)等政治性讀物,以蘇俄小說為主的翻譯文學,我國作家的長篇小說新作,也盛銷了較長時間,當然還有普及本的中國古典文學名著、《新華字典》等。這有社會變遷和政治形勢的原因,也有大眾文化消費局限的原因。
多年來,常銷書確實是業(yè)內(nèi)的一個話題,教材教輔和辭書以外,大家都想做一點常銷的品種,能持續(xù)不斷地印一點,最好是每年有印數(shù),每年就有固定的收益。但是難矣,選題既不易得,銷售又是問題,況且有些書是依靠出版社的品牌,讀者就認這塊牌子,如外國社會科學名著,似乎非商務印書館莫屬,如《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大概已有二百馀種;外國文化普及讀物,似乎非三聯(lián)書店莫屬,《文化生活譯叢》,大概已有一百馀種;外國文學,似乎又非上海譯文出版社、外國文學出版社、譯林出版社等專業(yè)社莫屬。這里有傳統(tǒng)選題、策劃能力、編輯專業(yè)、市場走向、資金投入諸多因素,并非一朝一夕之功。有些出版社就不動腦筋,紛紛去印四大名著等古典小說,既省了稿酬的開銷,又有現(xiàn)成的可以借鑒 ,甚至不請專家重新整理,隨便找個本子就印起來,結果施耐庵、曹雪芹們就只好躺在特價書店打二折三折,即便如此,問津者還是不多。因為我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東邊不亮西邊亮,總還能走掉一點,回收一點本錢,但與做常銷書的初衷相距甚遠了。當設想中的常銷書剛剛入市,未必暢銷,甚至走得很慢,這對出版人的市場預見能力是一個考驗。因此,常銷書的形成需要一個過程,需要經(jīng)過市場周期的檢驗,這是很不容易的。當然,出版人更希望有暢銷書,暢銷書比常銷書更有近期利益,一本書一年銷六萬冊,另一本書一年銷三千冊連銷二十年,排除漲價因素,假設碼洋相同,投入的回報率卻是明顯不同的。出版人希望有暢銷書的另一個原因,就是現(xiàn)行的出版體制,一紙調令,即使常銷書,與他又有什么關系呢。有人認為,有些書可以從暢銷到常銷,其實不大可能,暢銷書往往不會常銷,曇花一現(xiàn),過了也就過了。幾年以后,問一般讀者,某年有哪幾本書暢銷的,十有八九答不上來。幾年以后,一本曾經(jīng)暢銷的書,收入作者全集,非但不會帶動全集的發(fā)行,而且不久就又是特價書店的貨,反不如剛問世時熠熠生輝。五四以后的新文學作品,大部分未曾暢銷過,但經(jīng)過幾十年幾代人的閱讀,有的成為常銷書,有的也只能作為研究者的資料。
有時我隨便瞎想,常銷書的形成,與構筑書香社會有關,如果讀書人多,買書人多,藏書家庭多,也就自然形成常銷書的市場。曾經(jīng)有一陣提出理想藏書,就是出版社設想的一個藏書愿景,以自己的產(chǎn)品來引導讀者。出版社自然各有各的愿景,也就可以做出自己的特色。在我想來,古典選題仍是一個重要方面,四大名著當然還可以做,整理校訂以外,特別要注重印裝的精美,具有典藏的品位。選題上,還可大大擴展,像馮桂芬、王韜這兩位對中國現(xiàn)代化極有貢獻的人物,至今沒有一套像樣的書,張岱的《石匱書》、《石匱書后集》,許多年沒有整理重印了,《袁宏道集箋校》也脫銷快二十年了。外國文學名著、中國現(xiàn)代文學名著,也應該是常銷的,只是如今動輒全集,反倒成了常銷的障礙,其實選本是一個很好的出路,除選得好和印得精外,還要多作市場引導。大眾文化讀物是常銷書選題的寶庫,但要做得好、印裝得好,插圖本也不是那么容易做好的,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的《西方文化大眾精品書系》,河北教育出版社的《房龍的書》,山東畫報出版社的《中國古代物質文化經(jīng)典圖說叢書》,江蘇人民出版社的《漢譯精品》等,開辟了一條很好的路,當然叢書中有的選題還可以斟酌。另外,旅游讀物絕不能小覷,常常有比較穩(wěn)定的銷量,只是目前做得太濫,作者沒有去過的地方,居然也能為它寫書,搞得買書的游人稀里糊涂,這樣的書當然是短命的。
閱讀有年輪,讀者也在換代,八十年代前期是一次出版和銷售的高潮,二十年過去了,新的讀者群體又產(chǎn)生了。鐘叔河先生為海南出版社的《人人袖珍文庫》擬了一條廣告, 都是父親讀過兒子還要讀的書,這固然是常銷書,但父親沒有讀過,兒子正在讀,孫子將繼續(xù)讀的書,也就是新的常銷書,它的形成和完善就是文化的傳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