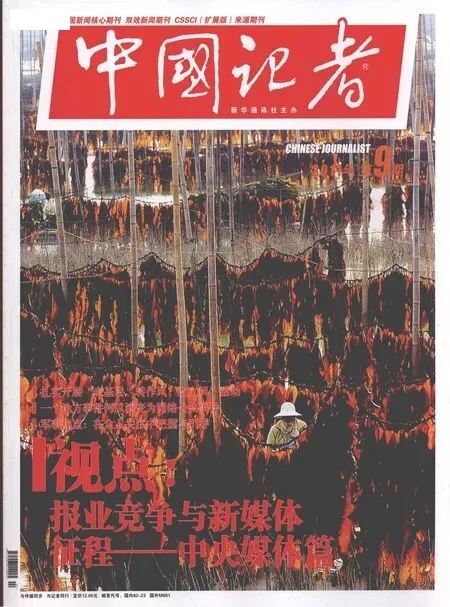環保報道里的經濟思維——讀《“沙子”怎樣變成“票子”》
□ 張 壘
在一個所謂“公民記者”的時代,我們為什么寫新聞?新聞若只是傳遞信息,那么,記者與一個同樣可以傳遞信息的非記者何異?又與一部足以全息攝像的機器何異?
人不是機器,因而,新聞也應該充滿人的思考、人的溫度。名記者郭玲春特別強調新聞寫作中的那個“我”,甚至于“常常不加掩飾地表露自己的傾向。有時按捺不住,會直白地呼叫、張揚我的觀點。”①今天,很多新聞難以打動人、震撼人,原因無他,就是來自記者作為認知主體的“我”不夠強大、過于簡單。
發表于《鄂爾多斯日報》漢文版2010年9月16日頭版頭條的《“沙子”怎樣變成“票子”》(該文獲第23屆少數民族地區報紙好新聞一等獎)一文是一篇工作性報道,卻處處體現了記者獨特的觀察思考。
排斥的吸引
《“沙子”怎樣變成“票子”》一上來就列出一對矛盾,挑戰人們的常識:“沙子”與“票子”本該是兩個相互排斥的極端,部分由于片面追求“票子”的原因,青山綠水才蛻變成漫天黃沙。而“沙子”變成“票子”則是件令人好奇的新鮮事。
排斥帶來張力,而張力則成為讀者深入閱讀的動力。
如同一次自我追問,標題的張力在開門見山的導語中又一次得以加強:“如何將生態建設與產業構建、經濟發展聯合有效推進,實現‘既有綠水青山,又有金山銀山’。這是杭錦旗歷屆領導高度關注和思考的課題。”隨后,文章順水推舟,點明:“杭錦旗確立建設綠色大旗目標”,實現了“生態建設產業化,產業發展生態化,生態生計兼顧,治沙致富雙贏”,從而“成功地創造了‘杭錦旗生態模式’”。
事實上,不僅僅是標題和導語,“發展經濟”與“環境保護”兩個核心主題本身就如同一把弓箭的兩端,整篇文章正是建立在這一兩極所建構的彈性之弦上。圍繞以經濟的思路做環保,以做環保來富民,以富民來鞏固環保成果等等一系列“反常”的行為,讀者的閱讀興趣一次次被調動,而作者的意圖則通過這種張力的一次次釋放而不斷向讀者傳遞。
成就的后臺
工作性報道共同面臨的一個難題就是:怎樣突破單純“宣傳成就”的套路,讓讀者除了對成績心生贊嘆之外,更多地掌握方法、擁有更多收獲?
在介紹成就的同時,《“沙子”怎樣變成“票子”》最核心的主體內容則是對“杭錦旗生態模式”的詳細闡釋。包括其來龍去脈、具體內容,以及杭錦人如何因時因地而宜采取不同的治理辦法。這些看似過于詳實甚至瑣碎的介紹,提供了一套“成功之術”,從而使成就不僅顯得真實,同時具備極為實際的參考價值。
如在回顧歷史之時,文章介紹了杭錦人摸索出的環境治理之法。
在新世紀,更是不厭其煩地介紹杭錦旗在退耕還林等“常規動作”之外,摸索出的一套生態治理模式:“在沙漠地區,通過‘封(封灘育草)、飛(飛播牧草)、造(植樹造林)’的途徑,建設‘莊園式生態經濟圈’;在宜林地區,采用‘草、灌、喬’相結合的方式……”

理念的力量
翻開中外那些獲得廣泛贊譽的新聞作品,一個最突出的特征就是:這些作品有著鮮明的時代烙印。從這些作品身上,人們總能以或嚴肅、或會心的方式感受到時代的脈動。
與此類似,《“沙子”怎樣變成“票子”》最打動人心的,就是通過經濟發展帶動環境保護的獨特立意。在全中國都在追問,高代價的增長能否終結之時,一個小地方的實踐,卻給人們帶來了春意和曙光。
文章在第二部分開頭即言:“不以綠色畫句號,產業鏈上做文章。杭錦旗人意識到,治沙的同時必須‘治窮’,生態建設才能可持續發展。”一句“不以綠色畫句號”,極大地突破了讀者思考的邊界——美好的環境不正是當代人所孜孜追求的終極目標嗎?而事實上,正是“不以綠色畫句號”,這種“綠色”才是可持續的,才是可以不斷復制和擴張的。原因正在于杭錦旗在長期的治沙實踐中得出的樸素而震撼的結論:“治沙的同時必須‘治窮’”。
正是在這里,良好的環境才與經濟的發展取得真正的和諧,科學發展觀也得到鮮活的明證。作者向讀者充分展現了這種發展模式轉變的結果。在宏觀上,“杭錦旗每年以造林40萬畝的速度向沙漠推進,涌現出千畝以上造林大戶2000多戶,每年‘沙中淘金’農牧民人均增收300余元。”而在個體層面,“牧民楊楞,從1999年開始在沙漠里種植甘草,迄今總畝數已達10余萬畝,年收入近200萬元,成了遠近聞名的‘淘沙大款’。與楊楞一樣,目前該旗在沙漠里‘淘金’的大小種植戶達2000余戶。”
文章最后自然得出結論:“只有百姓的生活好了,生態環境才好了。”這句話如同一曲反復震蕩,終于沖上峰頂的回旋,有力地指出了這一生態治理模式的核心經驗。而這一經驗,所印證的恰恰是科學發展觀的核心——以人為本。
如果說文章還有一些不足的話,那么也許作者可以找一個更為可親可近的新聞由頭,也許可以在文字上更多打磨,更多找到文章的節奏。“言而無文,行之不遠”。在思想的高度之外,還可以帶給讀者更多審美的愉悅。
【注釋】
① 郭玲春《我是這樣寫新聞的》,《中國記者》1989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