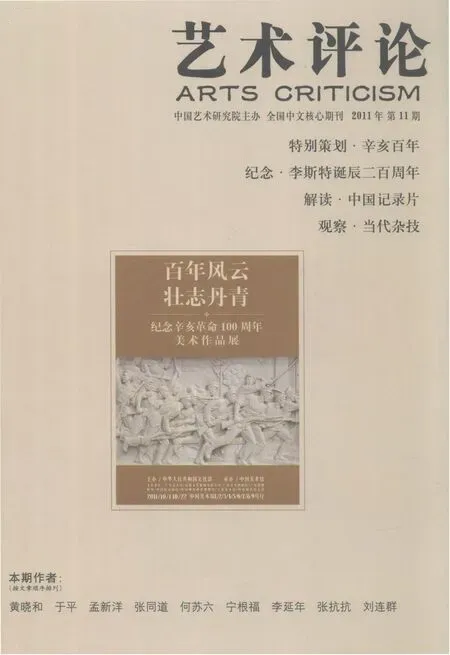《生命之樹》:敘事電影的反敘事化
劉小磊
劉小磊:北京電影學(xué)院文學(xué)系講師
“正是生命之樹的枝椏伸展的地方。我們看到無從探源的光芒,廣闊的星云,移動(dòng)的星辰,成形前的星球,太陽和月亮被黑風(fēng)暴所阻擋,給予生命能量的一道道閃電,汩汩地悸動(dòng)著的原始湖泊,史前植物、動(dòng)物,緩緩舞蹈的水母,雙髻鯊,棲身河岸的恐龍,一個(gè)胎兒的眼睛,以及最重要的,初生的孩子。”
——《生命之樹》獨(dú)白



2011年10月6日,瑞典文學(xué)院宣布將2011年諾貝爾文學(xué)獎(jiǎng)授予瑞典詩人托馬斯·特朗斯特羅姆,給予他諾貝爾文學(xué)獎(jiǎng)的頒獎(jiǎng)詞是:“經(jīng)過他那簡練、透通的意象,讓我們用嶄新的方式來體驗(yàn)現(xiàn)實(shí)世界”。這句頒獎(jiǎng)詞或許也可以送給獲得今年戛納電影節(jié)金棕櫚大獎(jiǎng)的影片《生命之樹》。
但泰倫斯·馬利克(Terrence Malick)的《生命之樹》自獲獎(jiǎng)以來一直引發(fā)巨大的爭議,有人認(rèn)為這是一部博大精深、精致美妙的史詩佳作,也有人認(rèn)為這只是一部矯揉造作、故弄玄虛的意識(shí)流之作。分歧的爭議點(diǎn)聚焦在“美輪美奐的畫面鏡頭、悲天憫人的宗教命題和支離破碎的敘事內(nèi)容”三者的無法對(duì)接。一部139分鐘的影片帶給觀眾的是一次費(fèi)解又意猶未盡的觀影體驗(yàn)。然而,如果對(duì)影片進(jìn)行剝絲抽繭似的解析,我們會(huì)驚訝地發(fā)現(xiàn):這部貌似打破敘事規(guī)則的影片恰恰是最大限度地遵從了好萊塢最傳統(tǒng)的敘事法則。
一、敘事法則——一個(gè)泛家庭化的故事
《生命之樹》從表面看沒有條分縷析的故事線索,也沒有深刻集中的人物刻畫。但將支離破碎的細(xì)節(jié)進(jìn)行重新整合后又會(huì)發(fā)現(xiàn),這是一個(gè)最好萊塢式的泛家庭化故事,遵從了一切傳統(tǒng)的人物塑造和敘事法則。
影片以《約伯記》開篇。這既是一個(gè)宗教背景,也是一個(gè)哲學(xué)背景。《圣經(jīng)》中的約伯正直、敬神,從不做不義之事。他有一個(gè)幸福的家庭,妻子為他生了七個(gè)兒子三個(gè)女兒,他還有7000只羊、3000只駱駝、500頭牛和500頭驢,以及成群的奴仆,上帝認(rèn)為他是最正直敬神的人。有一天,撒旦混在天使中對(duì)上帝說“約伯怎么會(huì)敬神?因?yàn)槟惚Wo(hù)他的一切。要是你毀了他的一切,他還會(huì)敬奉你嗎?”上帝對(duì)撒旦說“好吧,我現(xiàn)在把他的一切都交給你。”于是,約伯失去了一切。但約伯仍然一如既往地信仰上帝,上帝非常開心,還給了約伯14000只羊、6000只駱駝、2000頭牛和1000頭驢。妻子為他生了七個(gè)兒子三個(gè)女兒。約伯又活了140年,得見幸福。
《生命之樹》以這樣的開篇提出了好萊塢慣常表現(xiàn)的兩個(gè)主題:家庭與信仰,故事在美國一家五口人的平凡家庭瑣事中展開。布拉德·皮特(Brad Pitt)飾演的父親是個(gè)事業(yè)無成的中年男人,年輕時(shí)的他極具音樂天賦卻放棄理想,做了一名普通的工程師。但是他發(fā)明的專利無人問津,盡管他工作勤奮、從不請(qǐng)假,“甚至連星期天都沒有休息”,但他為之奉獻(xiàn)了大半輩子的工廠依然面臨倒閉的命運(yùn)。他將自己所有未實(shí)現(xiàn)的理想和對(duì)于成功的判斷標(biāo)準(zhǔn)都強(qiáng)加在三個(gè)兒子身上:逼兒子學(xué)鋼琴,在家中實(shí)施近乎苛刻的家教,教他們打架,教育他們不能對(duì)人仁慈、不能被他人利用。父親的所有行為都是在“美國夢(mèng)”破滅后對(duì)美國普世價(jià)值的一種變相反抗和消解。杰西卡·查斯坦(Jessica Chastain)飾演的母親則帶有強(qiáng)烈的符號(hào)性,她是基督教信仰的化身,帶有著圣母瑪利亞般的光暈。母親寬容、感恩,用愛來教育孩子,并保護(hù)孩子遠(yuǎn)離父親的家暴。
電影的節(jié)奏是由三個(gè)兒子從出生到成長的整個(gè)過程控制和切分的,以大兒子杰克為視點(diǎn)和主軸,以小兒子的死亡為重要的轉(zhuǎn)折點(diǎn)。兒子剛出生時(shí)的畫面純凈無暇,充滿著童趣和快樂,隨著年齡的增長,當(dāng)他們開始有了自我意識(shí)、認(rèn)知和辨析能力后,生活也開始從純粹簡單向復(fù)雜而充滿未知和危機(jī)的狀態(tài)轉(zhuǎn)變。杰克在目睹了饑餓、貧窮和死亡后,開始對(duì)世界感到恐懼;父親的嚴(yán)苛教育讓他學(xué)會(huì)了被迫的迎合和順從。母親施予的“愛”在面對(duì)強(qiáng)權(quán)和暴力時(shí)則帶有著太多的無力感。于是,“俄狄浦斯情結(jié)”再次出現(xiàn)。《生命之樹》在展現(xiàn)杰克成長時(shí)有兩次重要的“俄狄浦斯再現(xiàn)”:
第一次是父親在車底修車,杰克慢慢走向支撐汽車的千斤頂,他沉默地徘徊在周圍,嘴里小聲嘟囔著“上帝啊,讓他死吧;上帝啊,讓他死吧”。兒子必須要透過殺死父親才能夠確立一個(gè)獨(dú)立的“我”,才能作為一個(gè)真正的主體而存在。
第二次是處于性啟蒙時(shí)期的杰克滿臉通紅、鬼鬼祟祟地闖入鄰居的臥室,翻找女主人的內(nèi)衣。一縷陽光射進(jìn)來,杰克迎著陽光,仿佛捧起一件圣袍般地舉起那件女主人的睡袍仔細(xì)觀看,然后把它偷走,讓它隨著河流飄走。杰克表現(xiàn)出的是一個(gè)男孩子在青春期對(duì)“性”圖騰般的膜拜。
一直以來,“俄狄浦斯情結(jié)”是好萊塢敘事電影的重要法則,在宣揚(yáng)“自由、平等、博愛”的信仰教義的美國最注重的就是作為“個(gè)體”的成長。這個(gè)成長的過程必然是混沌中的破舊立新,父親也成為阻礙個(gè)人成長的重要符號(hào)。從經(jīng)典好萊塢時(shí)期希區(qū)柯克的電影,到新好萊塢時(shí)期的《畢業(yè)生》、《教父》甚至最近的《貝奧武夫》、《猩球崛起》……好萊塢電影大多呈現(xiàn)出一種凸顯個(gè)人成長的“泛家庭化”傾向,這符合了美國對(duì)電影一直以來所強(qiáng)調(diào)的“信仰教義”,電影希望觀眾直面的是《約伯記》中所提出的問題:“假如撒旦拿走上帝的恩賜,你該如何面對(duì)?”
《生命之樹》給出的答案是多年后的杰克(西恩·潘[Sean Penn]飾演)還是被父親的潛移默化所影響,置身于現(xiàn)代的社會(huì)機(jī)器之中,多個(gè)仰拍鏡頭和低機(jī)位跟進(jìn)的鏡頭凸顯出杰克身心的疲憊與壓抑,他與父親實(shí)現(xiàn)了和解,更使得所有人最后在天堂相聚。
如果給《生命之樹》脫去耀眼奪目的華麗外衣,它講述的就是這樣一個(gè)簡單的故事:從一家人單純快樂的生活,到逐漸加深的隔閡與矛盾,再到最后的化解和體諒。這是一個(gè)典型的“泛家庭化”好萊塢敘事,但是泰倫斯·馬利克用反敘事化的表現(xiàn)手段給一則敘事故事加上了哲學(xué)的注解。
二、反敘事化——一首生命起源的贊美詩
泰倫斯·馬利克是一位詩性導(dǎo)演,他習(xí)慣于用一種反敘事化的方式去講一個(gè)通俗的故事,這在他為數(shù)不多的作品《天堂之日》、《不毛之地》和《新世界》等都有所表現(xiàn)。但是和其他習(xí)慣于碎片敘事的導(dǎo)演不同,馬利克基于的最根本的表達(dá)立場(chǎng)是源于生命之初的“新道德價(jià)值觀”,這也是在他所有作品中一以貫之的。
新道德價(jià)值觀是哲學(xué)家尼采對(duì)于道德自然主義的重構(gòu),尼采認(rèn)為“我制定一個(gè)原則:道德中的每一種自然主義,也就是每一種健康的道德,都是受生命本能支配的……相反,反自然的道德,也就是幾乎每一種迄今為止被倡導(dǎo)、推崇、鼓吹的道德,都是反對(duì)生命本能的,它們是對(duì)生命本能的隱蔽的或公開的、肆無忌憚的譴責(zé)”。尼采明確地把他所倡導(dǎo)的新道德價(jià)值稱為以生命本能為基礎(chǔ)的道德。他肯定個(gè)人生命應(yīng)該從自然欲望出發(fā),強(qiáng)調(diào)個(gè)人生命本能的正當(dāng)性,鼓勵(lì)個(gè)人的自愛、創(chuàng)造和強(qiáng)大。
泰倫斯·馬利克是尼采“新道德價(jià)值觀”的忠實(shí)擁護(hù)者,《天堂之日》中男主角讓自己的女友委身嫁給所剩時(shí)日不多的農(nóng)場(chǎng)主,從而引發(fā)了一場(chǎng)災(zāi)禍;《不毛之地》中少女與青年垃圾工人相愛,他們因?yàn)榉噶艘患\殺案而各自逃亡;《生命之樹》中則是父親強(qiáng)迫性地在兒子身上加諸屬于自己的夢(mèng)想……但是因?yàn)閷?dǎo)演肯定生命的自然欲望,所以他對(duì)主人公的行為是不做出任何價(jià)值判斷的。換句話講,一切遵從生命個(gè)體欲望的行為都是符合新道德價(jià)值觀的。在新價(jià)值道德觀的表達(dá)立場(chǎng)下,泰倫斯·馬利克以“宇宙、生命和家庭”為關(guān)鍵詞,用一系列美輪美奐的鏡頭進(jìn)行反敘事化的組接,試圖將“泛家庭化”的故事上升至對(duì)生命起源的探討。
從影片結(jié)構(gòu)上看,導(dǎo)演是將地球生命、人類生命與家庭瑣事三條線索進(jìn)行穿插式的并置敘述:第一條線索是展現(xiàn)從宇宙大爆炸到寒武紀(jì)、侏羅紀(jì)乃至白堊紀(jì)的宇宙演變,觀眾目睹了巖漿噴發(fā)、地球改變、植被生長、恐龍滅絕,直至人類誕生;第二條線索是展現(xiàn)作為個(gè)體的“人”的孕育過程:從放大的顯像細(xì)胞到細(xì)菌乃至胚胎的形成。地球的起源與人類小生命的誕生是相同相通的,隨著地球的變幻,人類也在代代繁衍;第三條線索則是展現(xiàn)一個(gè)普通家庭的平凡瑣事:從快樂、到矛盾、爭吵直至原諒。正因?yàn)槭侨龡l線索的并置敘述,讓每一個(gè)鏡頭都成了導(dǎo)演詩意化的畫面展示:陽光、海洋、樹木、火山……自然界的神秘奇妙,殘酷和諧,動(dòng)蕩平靜都通過影像的魅力淋漓盡致地表現(xiàn)了出來,宛若一首生命起源的贊美詩。
但是觀影爭議也因此出現(xiàn)了。精美畫面與敘事故事之間那微妙的前因后果究竟應(yīng)該如何地體現(xiàn)?影片中那充斥著大量的隱喻性符號(hào)與鏡頭語言蘊(yùn)藏的駁雜繁復(fù)的生命奧義究竟有何關(guān)聯(lián)?導(dǎo)演很努力地用各種畫面充當(dāng)隱喻性的符號(hào),從而實(shí)現(xiàn)對(duì)“新道德價(jià)值觀”的表述,但是卻因?yàn)檫^于細(xì)碎和繁復(fù),最后給觀眾留下的難免只是一種模棱兩可又欲言又止的感受,以至于忽視了導(dǎo)演原本想要講述的是一個(gè)再通俗不過的敘事故事。
影片的結(jié)尾還是非常撼人心魄的:成年后的杰克走向海邊,跟隨著兒時(shí)的自己,回憶父親和母親,回憶那早逝的弟弟,思考著生命的緣起。這時(shí),他跟年輕時(shí)的父母走到了,終于接近了天空,感受到了生命的意義,正如母親一直教育他們的:There are two ways through life — The way of nature ,and the way of grace(人生有兩種生活方式:一種是自然之道,一種是感恩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