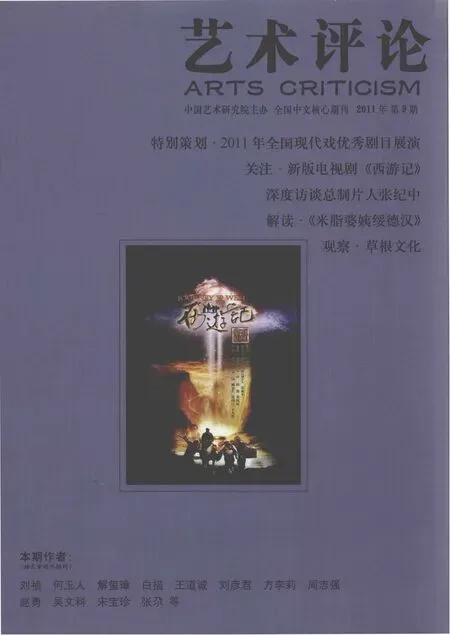大秧歌扭起來
劉彥君
劉彥君:中國藝術研究院話劇研究所所長、研究員

由無以數計的陜北大秧歌和六十余首信天游連綴、整合而成的陜北秧歌劇《米脂婆姨綏德漢》火了。大姑娘小伙子們載歌載舞,生機勃勃地從陜北舞到了北京,舞向了全國。宏強的性格,宏大的場景,宏偉的氣勢交相輝映,匯聚為洋洋大觀。創作者以他們特殊的眼光與視角追求著“恢弘”與“廣闊”,以他們的激情點燃著觀眾的激情。
陜北秧歌劇的產生,據說與革命有關,那已是上個世紀40年代初的事情了。當時抗日戰爭的形勢發生了變化:日軍為了鞏固被他們占領的土地,暫時收縮了戰線,抗戰進入相持階段;延安成了政局較為穩定的后方。中共中央調集了兩萬多名各級黨政干部來延安學習、培訓,以提高他們的素質。而戲劇演出,就成為他們豐富生活、開闊眼界的重要方式。但由于從事戲劇工作的大多是來自城市的青年,最初上演的只是他們所熟悉的一些中外名劇,如《雷雨》、《日出》、《欽差大臣》、《求婚》、《帶槍的人》、《偽君子》等。這些作品的上演較少考慮時間、地點和觀賞對象等特點,演出內容與農民、戰士的生活產生一定距離,客觀上出現了偏向。后來,延安文藝座談會及時召開,端正了邊區文藝運動的方向,一批反映火熱斗爭生活的作品,和一些為群眾喜聞樂見的民族戲劇形式被挖掘,被創造出來。秧歌劇就是在這種背景上產生的,當時熱演的獨幕劇如《夫妻識字》、《兄妹開荒》,多幕劇如《白毛女》、《周子山》都是秧歌劇中的精品。
《米脂婆姨綏德漢》的演出,不僅讓我們想起了這段紅色歷史,而且讓我們感受到了秧歌劇的激情。因為,邊唱邊扭,正是一種激情狀態,所謂“情動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這種激情,能夠動員起火熱的社會斗爭,也能把我們帶到更為遙遠,更為廣袤的時空,甚至是從亙古走來,并且還連接著未來的愛情生活。即使是這種人類最柔和的情愫,秧歌劇中的青年男女,也浸染著秧歌劇的激情。“上一道道坡坡下一道道梁,想起我的小妹妹好心慌”, “蕎面皮皮架個墻飛,想哥哥想成黃臉鬼”,“三十里明沙二十里水,八百里路上尋妹妹”,“我心里有誰就是誰”,“我撲進懷里貼上身身”……且不說這些信天游蒼涼、高亢、幽遠、熱烈的曲調,就是歌詞本身,也有著自己單純、狂放的個性,直接、率真得幾乎要溢出體外。在強調含蓄、溫馴等文明“國民性”的訓誡面前,秧歌劇中的生命告白顯得是何等強悍。這種青銅雕像般的雄強性格和粗放人性的渲染,顯然是由一種自覺要求出發的。創作者要以這樣的性格塑造,把蘊藏在陜北農民強健體魄中的,蘊藏在民族肌體中的偉力,盡其所能表現出來,以寄托他們民族復興的理想。
與這種理想民族性格的呼喚相對應的,是創作者對于陜北大地的崇拜和禮贊。這是秧歌劇,也是這部作品賴以產生的背景和土壤。這種崇拜和禮贊,作為創作者激情狀態的一個重要構成,決定著舞臺宏闊性的總體構思、意象選擇,以及他們為這場演出確定的濃郁色調。舞臺上,時代感被淡化,暗示性被強化。沒有環境流轉的過程,沒有單調、徐緩的日常節奏。創作者力圖以寬廣的歷史視角,使自己的作品具有史詩結構的宏偉性。他們抓住最鮮明的形象,突出了畫面,使其顯示著強烈的主觀性和抒情性。隨著舞臺的旋轉,幽幽的山坡,深深的丘壑,挺挺的老樹,高高的窯洞,紅紅的落日,彎彎的月亮等簡潔而明快的意象依次呈現,在紅、黑、綠、紫、黃等瑰麗色調的映襯下,顯得遼闊、單純而又神秘。經過了創作者心靈的過濾,這些現代電腦制作出來的影像景觀,既具有陜北剪紙的風格,又具有年畫的艷麗色澤。略去了具體村落,略去了現實的農家,舞臺上那方土地的內涵與主題,被創作者明顯地放大、延展了。其“個性”與“氣質”,與生活于其中的人物渾然一體,構成了作品宏偉的風格特征,從而超越了地理學的意義,成為了人物精神的外化。其作用和功能,不僅是劇中人物賴以活動的空間環境,或者說借以依托的物質世界,而成為了一個獨立的有意味的藝術形象。與此相呼應,《米脂婆姨綏德漢》在人物造型、服飾設計、色彩處理上的夸張筆法,也是一種詩意的表達。大紅大綠的大花襖,大花褲,被放大了棱角的羊肚肚手巾,紅蓋頭、花肚兜,都造成了一種強勢的視覺效果,給人以心靈的震撼。

閱讀印象夏季到香港來看書 劉昕亭前沿題域 主持人:喬以鋼性別與傳媒的十年博弈 林丹婭男性雜志中的“熟男”成長史 陳 寧百合花開:女同性戀的文學呈現 陳亞亞邋遢公主變身記——兒童繪本中的新女性形象 董曉璇主題書評 主持人:程巍文化形態學的近代史——讀《通往立憲之路》 傅永新新史記傳教士筆下的辛亥革命——以布朗的《中國革命》為中心 王 靜曾文正公“復活”記——一段近代中國的閱讀記憶 譚徐鋒讀書一問當進步成為信仰 黃增喜《中國圖書評論》2011年第9期要目每個人都是生活的導演——一種新的影像敘事 鄭二利“速度”的祛魅 盧 楨不如無書現實有愛恨,歷史無情仇——侯宜杰《神拳》疑思 陳曉平思想文化文明史、現代性與現時代問題——讀《文明的進程》 葉 雋斯道雷與開放的文化理論 許苗苗小窺“歷史中的結構”——讀馬歇爾·薩林斯《歷史之島》 高 源馬克思的《大綱》與《大綱》中的馬克思——以馬賽羅的新書《馬克思的<大綱>》為例 張秀琴南轅北轍霍金:一個“科學之神”的打造及其意義 江曉原 劉 兵燈下閑讀錢穆七房橋世界的前世今生——兼評《錢穆與七房橋世界》 盧元偉
這些充溢著“力”的“巨人”和“大地”形象,為秧歌劇帶來的,不僅是具有異樣品質的本土文化特色,在歌舞的渲染和包裹中,它們還共同繪就了這部作品恢弘大氣的風格。歌由信天游、小調、小曲、酒歌等山村野調的旋律組合而成,充滿著野性的張力。舞由邊唱邊扭的陜北大秧歌貫穿。為了制造莽蒼、粗獷的情調和美感,我發現,創作者們刻意強化、規模化了群體的舞蹈場面。如果說,豪放灑脫、桀驁不馴的山大王虎子帶著隨從上山下山,還能夠納入正常敘事邏輯的話,那么,為了守住愛情,步步為營的石娃,則不可能隨時隨地糾集起一幫人來與虎子對峙。顯而易見,兩邊的旗鼓相當是出自另一角度的考慮和安排。況且,幾場大規模的群體舞蹈如“送彩禮舞”、“搶親舞”、婚禮上的“紅綢舞”等,不僅以其蓬勃、夸張、大開大合的動作設計推動著劇情發展,牽引著故事的起承轉合,而且營構出了熱烈、歡快的氣氛。正是在這種氛圍中,人對于自身的信念,掙扎著溢出了大秧歌的歌舞外殼,由內而外地把作品點亮,讓我們看到了這方土地這方人渺小軀體中所蘊藏的那種可以排山倒海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