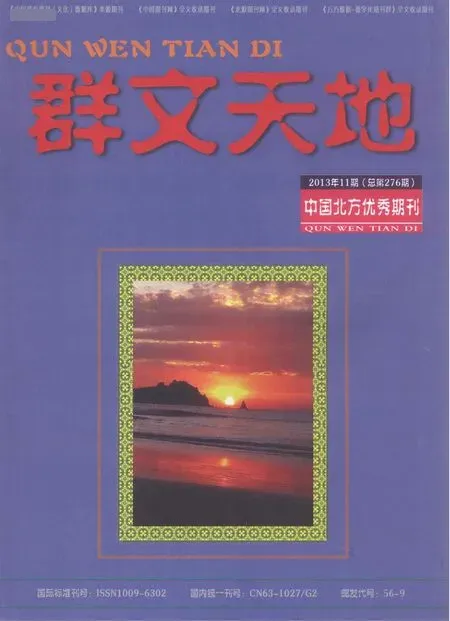談打擊樂在戲曲表演中的作用
■ 張建軍
世界何其大,舞臺又何其小,中國戲曲藝術卻將這大千世界中的萬事萬物濃縮在小小的舞臺里,使大千世界變小了,小小舞臺變大了。而打擊樂以其自身獨具的藝術功能和豐富的表現力,活靈活現并有聲有色地馳騁穿梭在這個舞臺上。
我國戲曲藝術是由各地方劇種組成的,由于各地方劇種所在的地域和形成發展的淵源不同,藝術特色、表演風格不同,其伴奏樂件中打擊樂的配置、運用與特點自然不同。
自古戲曲離不開鑼鼓,沒有鑼鼓伴奏不能稱之為戲,離開鑼鼓戲曲將不復存在。中國戲曲歷史悠久,種類繁多,博大精深,浩如煙海,猶如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地質寶藏。據有關史料記載,中國的戲曲劇種有360個之多。在某些古老劇種形成之初,除演員的表演外,音樂方面開始只有鑼鼓伴奏幫襯,后來歷經多年的發展完善,才吸收加進了一些絲竹管弦樂器。在絕大部分的戲曲劇種中,鑼鼓至今仍在演出中起主導作用,沒能脫離開打擊樂的伴奏,鑼鼓與其共存共榮,尤其我國一些較大型的、具有代表性的戲曲劇種更是如此。像昆曲、秦腔、漢劇、京劇、川劇、評劇……實際上,在中國戲曲藝術這個母體孕育之初,鑼鼓即隨之誕生并逐步加以完善,與之形成了一個有機的整體。
在談到打擊樂舞臺運用的時候,必須對打擊樂做一番公正恰當的評價。首先,必須承認這一事實:在現代戲曲音樂中,打擊樂的運用已達到了相當高的程度。它是戲劇藝術的重要組成部分,是表演節奏的支柱和靈魂。無論唱念做打、演員的上下場,無不在一定的鑼鼓點中緊密配合來完成。它能通過音色、音量、節奏、鑼鼓點的變化來表現戲劇矛盾沖突、刻畫人物性格、渲染舞臺氣氛,配合舞蹈、武打等舞臺表演。
打擊樂作為一種聽覺藝術,憑借著特有的藝術功能,在戲曲舞臺上得到廣泛普遍的應用。它不僅是簡單響器的鋪墊,而且深深地融匯在戲曲藝術的機體內,自始至終活躍在舞臺藝術的方方面面,不論在劇前劇中、劇間劇后,還是幕啟幕落、場前場后,大家都可以感覺到它的存在,聽到它的聲音,受到它的啟迪、感染和鼓舞。它在戲曲舞臺上可以說是“無處不有處處有,無時不有時時有”。我們如果把戲曲舞臺上各種藝術門類,如劇情(劇本文學)、表演、唱腔、音樂(管弦樂)、舞臺美術等所展現的情節、片段、聲腔、曲調、畫面、句逗、章節等比作是一顆顆五顏六色、閃爍耀目的夜明珠,那么打擊樂就是串聯珠粒的“金絲線”。設想,如果沒有了這條“金絲線”的串聯,一顆顆閃爍奪目的珠粒就會散落在舞臺大盤中,可能就變了味,變成了話劇、歌劇、舞劇和雜技了。中國戲曲美學家陳幼韓先生說:“在戲曲表演藝術中管弦樂主要起著血脈作用,而打擊樂才是骨干。要使形象樹立起來的最終權威,還是打擊樂。它是整個戲曲舞臺表演藝術的‘主心骨’”。可見,打擊樂在戲曲舞臺上普遍廣泛地應用,且又古今不衰,正是因為它有著強大的生命力。
戲曲打擊樂不同于管弦樂,它的主奏樂器沒有音律的高低,奏不出音樂的旋律,只能打擊出特有的音響、音色。然而,因為它在音樂的節奏節拍方面十分靈活善變,所以形成了自己獨有的音響、音色的節律。如果將舞臺表演藝術比作海洋,打擊樂就如同魚兒那樣任意泳動,不論是長是短、是快是慢、是強是弱,或是漸緩漸急、漸弱漸強,或是強擊海浪,或是靜水漂浮,或是“抽刀斷水”打亂節律,散兵游泳。總之,任其節奏千變萬化,打擊樂都可以應用如常,用自己特有的音響、音色和靈活善變的節奏節拍來伴奏表演,塑造形象,伴奏唱念做打,抒發喜怒哀樂。
打擊樂的許多鑼鼓譜速度的變化,如同一條松緊帶,可以根據需要隨意拉長縮短,節奏變緩或加快。故而一首打擊樂譜可以用慢、中、快不同速度演奏,也可以有繁、簡、強、弱之不同力度和不同打法,當然萬變不離其“本”,這就是它的基本錘法和節律。另外,還有只用打擊樂伴奏的板歌,又名數板,它是別具一格的說唱形式,其節拍有“整行整說”和“整行散說”之分,也是一種非常獨特而又具有強烈戲劇性的音樂形式。
平弦戲打擊樂以板、大鑼、鐃鈸、小鑼四大樂器為主,通常有三種配置:第一種大鑼為主,鐃鈸、小鑼為輔;第二種不用大鑼,以鐃鈸為主,小鑼為輔;第三種大鑼、鐃鈸均不用,小鑼單打。在打法上可歸納為四種基本點子:
(1)以“倉七”沖頭型為主,其變化形式包括:沖頭、導板頭、帽兒頭、五擊頭、四擊頭、住頭、歸位、串子、長錘、緊錘、九錘半、搜場;
(2)以“倉七臺七”長錘型為主,其變化形式包括:快慢長錘、一錘鑼、搖擺長錘(風點頭等);
(3)以“倉七臺七”閃錘型為主,其變化形式包括:閃錘、滾頭子、紐絲等;
(4)以“倉臺臺七臺”抽頭型為主,其變化形式包括:抽頭、馬腿、風點頭、收頭、奪頭等。
武場四大件中大鑼具有固定音高下滑的音響特點;小鑼具有固定音高上滑的音響特點;鐃鈸具有不同音高點,平行音響特點;其組合成的綜合音響能密切配合道白四聲調值、語調與節奏感,從而加強了語言的音樂性。同時在與唱腔及文場樂器的配合上,均具有獨特的色彩與功能。除武場四大件外,還運用了其他眾多的打擊樂器,如水鈸、大鈸、齊鈸、木魚、梆子、碰鐘、小湯鑼、大小堂鼓,現在還吸收了定音鼓、軍鈸、吊鈸等打擊樂器。
打擊樂在戲曲音樂至整個戲曲舞臺方面占有重要的地位,它不僅在渲染舞臺氣氛、調節身段表演、配合語言韻律、掌握唱腔與伴奏音樂的節奏上和速度上以及豐富樂隊的音響方面起著積極良好的作用,而且在以節奏音響帶動全局、貫穿全局、統一整個舞臺的節奏方面起著重要的作用,是表演節奏的支柱和靈魂。無論唱、念、做、打,還是演員上下場均無不在一定的鑼鼓點配合下來完成,它能通過音色、音量、節奏、鑼鼓點的變化來表現戲劇的矛盾沖突、刻畫人物性格、渲染舞臺氣氛,配合舞蹈、武打等。而戲曲音樂中的司鼓,可以說是整個戲曲樂隊的總指揮。徐慕云在《中國戲曲史》中說:“凡屬歌舞劇之類者蓋無一不以亦無不皆以鼓板掌其節折、齊其動作、鼓其精神也”。可見,司鼓在戲曲樂隊伴奏中的地位是多么重要,根植于西北大地的平弦戲也不例外。平弦打擊樂是節奏的靈魂,打擊樂千變萬化,可以說伴奏的過程就是司鼓的創作過程,司鼓要根據劇本的格調,對打擊樂進行合理地編排,達到渲染劇情、襯托劇中人物的目的,同樣的一個擊樂句,靈活運用它的“輕、重、緩、急”可以得到完全不同的舞臺效果。司鼓是核心,指揮所有的打擊樂器,掌握整個樂隊奏出按劇情要求的正確節奏,更好地烘托劇情,同時也加強了戲劇效果。
改革也好,守舊也罷,如果一味地在形式上追求所謂的“革新”和“繼承”,筆者認為是不可取的,平弦戲是一門新興的綜合性表演藝術,在長期的發展過程中已逐漸形成了富有自身特點的平弦音樂,其中也包括司鼓在內的打擊樂。如果為了創新而使固有的程式面目皆非,支離破碎,對平弦戲的發展是極為不利的。作為一名打擊樂演奏員應具備創新意識,從以下幾個方面去努力:
(一)堅持文化學習,提高對藝術的鑒賞能力和感悟能力。多讀名著、汲取營養,特別是要經常性地誦讀,熟背一些唐詩宋詞。因為詩詞中不僅含有大量豐富的文學知識,還具有一定的格律、韻律和明快的音樂與節奏,這對于我們處理唱腔、分析人物有著直接的幫助。而有了一定的文學素養,可以提高我們的接受能力、理解能力、聯想能力、藝術想象力、統一及變化的感知能力。
(二)不斷加強樂感的培養,提高對音樂節奏、力度、速度、音色、曲體等方面的辨別能力和感知能力。要多聽中外名曲,不但從民樂作品中感受涓涓細流,也要在龐大的、充滿質感的交響樂中感受音樂世界無限的空間。作為一名司鼓演奏員,如果只在鼓板上做文章,到頭來他只能是一名匠人,而不能成為真正的大師,所以,能較透徹地領悟樂曲的特點和內涵,更好地接受樂曲的美感,準確地把握戲曲的節奏,對于每一位音樂工作者,特別是戲曲司鼓演奏員來說,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
(三)長期不懈地堅持基本功訓練。司鼓演奏員不僅要具備最基本的素質和技能,還要與其他人配合得天衣無縫。在熟能生巧的過程中,悟得藝術的精髓;在枯燥乏味的技術訓練中,隨時滲透技巧美感的因素,不斷賦予技術一定的生命力和感染力。在演奏中,一定要準確地把握音色,有剛有柔,感情上有放有收,把死的技術變成活的技巧,使司鼓在板頭與唱腔之間、場景的轉換和人物的交替之間銜接得自然貼切、酣暢淋漓,并使整個劇情的節奏在音樂的伴奏下流暢、連貫地進行,使人有一氣呵成的美的快感。
(四)做一個稱職的打擊樂演奏員,不僅要練就基本功,而且必須熟悉文武場的每一種樂器,熟悉一些通常應用的唱腔、曲牌和鑼鼓點,而且應當熟悉大量的劇目,只有通過扎扎實實的學習和實踐,才能領悟出藝術的規律,樂隊伴奏的規律,領悟出如何把握舞臺節奏,如何打出人物的情感和性格。鼓師在配合表演中絕不是機械的搬用,在不同的地方應該有不同的表演形式,這就要求打擊樂演奏員必須吃透演員的表演而賦予鑼鼓以活生生的情感內容,既要合乎一般規律,又要具有創造性的思維,從而深刻、準確地體現人物情感,起到打擊樂的作用。同一劇目的每場演出,絕不是簡單重復,每一次都有新的創造,而演員個人條件、精神狀態、觀眾情緒以及其他外部條件變化,也都決定著臨場發揮。在演奏中可能出現各種變化,這就要求鼓師必須具備靈活、敏銳的觀察力和應變能力。
總之,戲曲打擊樂不僅能夠打出劇中人物外在形體的動態與靜態,而且還能打出人物內在感情的喜怒哀樂,從而達到聲形并茂和聲情并茂,使聲、形、情通過觀眾的視覺直觀和聽覺直感,融匯成統一的觀感,享受到戲曲藝術之美。這正如馬凌元先生所說:“高水平的打擊樂藝術家,以爐火純青的技藝,巧妙地運用每一個鑼鼓點,并準確地配合劇中人物的外在形體之一舉一動,而且還能巧奪天工般打出人物的內在感情節奏。這正是我國戲曲打擊樂的高明之處。”戲曲打擊樂應用的廣泛性,表現手法的多樣性,節奏節拍的可變性,是其戲曲舞臺實踐和應用規律的三大特征。我們可以將其歸結為:聯綴藝術門類,創造舞臺氛圍;服務生旦凈丑,塑造人物形象;領伴唱念做打,通用“四功五法”;打出內(在)外(在)節奏感,抒發喜怒哀樂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