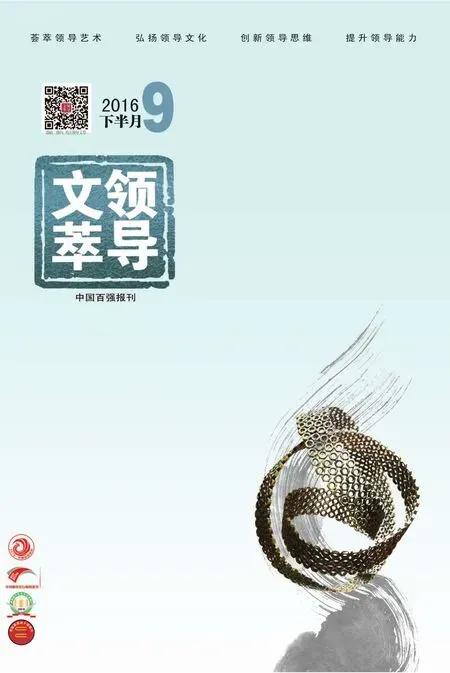李煦之死
莊秋水
如果官員們僅把自身看做某一特殊政權服務的臣仆,則權力和積累之財富皆如幻影
一七二九年早春,李煦在打牲烏拉(今吉林市西北的烏拉街)時孤獨地死去。誰能想到,這個死于饑餓和寒冷的七十五歲老翁,曾擔任三十年蘇州織造,八任鹽運御史,是先皇康熙的奶兄弟和心腹。
李煦出身于“簪纓巨族”。他的父親李士楨雖是清軍的俘虜,成為正白旗的包衣奴才,此后卻從龍入關,尤其在平三藩時戰功顯赫,官越做越大。李煦生母則成了康熙的保姆。李煦的表妹王氏后來進宮成為皇帝的妃子。故此,李煦與康熙的關系可謂非同一般,一如他在奏折里所言,“一家老幼疊受圣主天恩”。
康熙三十二年,即一六九三年,李煦奉命擔任蘇州織造。這是一個五品小官,卻無人膽敢小覷。在皇帝的布局中,李煦任蘇州織造,負責政情;他的另一個奶兄弟曹寅任江寧織造,招攬名士;杭州織造孫文成則關注海防。他們是他在江南——這個漢文化累代蓄積之地——的眼睛。李煦作為蘇州織造,官方職責是管理“滸墅關”稅務,兼揚州鹽政,但更重要的身份,其實是皇帝設在蘇州的特情人員。
作為皇帝的耳目,李煦主要就是用密折向皇帝匯報江南官場和民情。藉由奏折與奏折朱批,皇帝與臣子們形成一種互動。皇帝掌握全國各地的資訊、各地官員們的工作績效和思想狀況;同時透過朱批,將自己的治國方略與教誨之語,傳達給重要的官員們。在皇帝眼中,如此一來,君臣之間形如一體,沒有隔閡,堪稱一個上下一心的政治生命共同體。
終康熙一朝,皇帝對李煦可謂恩上加恩,視做自家人,朱批里常說些私房話。李煦自己說是“奴才夢想不到”的。但一如《紅樓夢》中秦可卿告誡王熙鳳之言,烈火烹油鮮花著錦之盛,也不過是瞬間的繁華。一般認為,這部中國古代最偉大的小說,正是李煦妹丈曹寅的孫輩曹雪芹根據自己家族和姻族的故事創作而成。
一七二三年,亦即雍正元年,新皇帝甫上臺,僅一個多月便抄了李煦的家。皇帝給出了一個莫須有的罪名:“奏請欲替王修德挖參”。也就是說李煦上了一個奏折,替王修德(內務府皇商)等人奏請采人參。這樣一個奏請,即便有不當,但并未形成事實,何以竟成了被廢官治罪的緣由?
此后,采參一事再未被提起。雍正翻出李煦在任上虧空舊賬。查抄結果出來,李煦虧空織造處386841兩銀。據李煦之子李鼎供稱,其父在鹽差任內,商人所欠折色短平銀共378840兩。此案審結時,被訊問的商人們非常合作,他們表示上感皇恩浩蕩,下憂公帑虛懸,愿以十二年為期,照數賠償。事實上,這些銀兩并非商人們欠款,而是李煦辦差無錢可用,算作預支,先講明折扣,折色短平,算作利息。李煦的錢花到哪里去了呢?康熙六次南巡,李煦和曹寅四次接駕。康熙宣稱,南巡所有費用和物品出自內帑,不取民間一絲一毫,兩織造自然也算“內帑”了。李鼎供詞便說父親“在織造任內,無有進項,仍拆東補西,以致虧空”。對此,康熙也一清二楚。
除去接駕之用,亦有不少花費在打點奉承上司上。翻閱李煦奏折,可以發現康熙幾次三番提醒李煦,“已后凡各處打點費用,一概盡除。奉承上司部費都免了,亦未必補得起鹽差之虧空。若不聽朕金石良言,后日悔之何及。爾當留心身家性命子孫之計可也”;“爾向來打點處太多,多而無益,亦不自知”。在一個高度的專制政體下,人格化權力是政治權力的主要運行模式,當皇帝避開常規的行政機構,使用自己的專制權力,臣子們便如芒在背:他們隨時可能因為一件小事,丟失了皇帝的寵信、財產、自由甚至生命。李煦和其他官員們一樣,需要未雨綢繆,向潛在的皇位繼承者表示忠心,以確保自身的地位和子孫的未來。可惜,李煦投資失算。一七二七年,在被革職抄家之后,他又被流放到打牲烏拉,罪名是為在皇位之爭中失敗的皇八子胤禩買女子,因此被刑部定為“奸黨”。
李煦不幸卷入康熙繼承人危機之中,最終成為晚期帝制下無數榮枯悲劇中的一個。他不曾想到的是,如果專制權力不受限制,肆無忌憚,如果官員們僅僅把自身看做某一特殊政權服務的臣仆,則手中之權力和積累之財富皆如幻影。無人可以真正安全。
(摘自《新世紀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