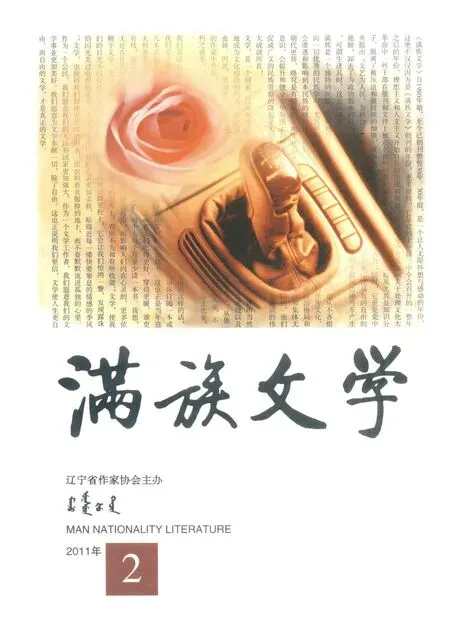將小說研究帶進“微理論”時代
——我讀王彬先生的《水滸的酒店》
牛學智
將小說研究帶進“微理論”時代
——我讀王彬先生的《水滸的酒店》
牛學智
無論《紅樓夢》,還是《水滸傳》,畢生精力花費在這上面的學者,僅就數量而言,大概不在少數。由此可以推知,對于這樣的古典長篇小說,如同有些人所說,不可能沒有哪個角落沒被論及,應該不是武斷之語。
也就是說,《紅樓夢》也罷,《水滸傳》也罷,一邊不斷地顯示著它們豐富的意義空間,一邊也在不斷地暴露著文學研究者開拓新領地的乏力和窘態。這樣的現狀,當然不能簡單地歸結為研究者的努力不夠,而是應該有深刻原因的。
可是,《水滸的酒店》顯然不一樣,而且應該說很不一樣。王彬先生有著深厚的古文學功底,我們可以從他簡潔雅致的“序”或者“后記”中領略他的謙遜和度量,清晰地讀出他拿捏研究對象的輕巧與幽微之處。他處理研究對象的輕巧,是說他經常為了惜墨如金,總是千方百計地研磨既有的幾乎所有方法,然后幾乎還是非常猶豫地進入對象。因為他對擺在他面前的成堆的研究成果實在是太熟悉了,因著特別的尊重,他選取的研究方法一經實施,那就絕對探微燭幽,發前人之所未發之處,令人眼前豁然一亮。說他的研究又往往給人幽微之感,不僅指他長期以來一直堅持著他的微觀考證的學術思路,更是指他下手細、妙、獨,但從來不失對對象的整體把握,尤其像《水滸傳》這樣的長篇小說的文化語境。能從細處、微妙之處、文本獨特的視角還原出具體的人文景觀和從預設的時代背景、人文狀況,挑選出適當的細節,即“小題大做,舉例說明”的方法完全不同。借用詹姆遜“歷史化”的觀點說,后者是使歷史化文本,而前者則是使時代的文本回到它應有的位置,
王彬先生自己也說過,他寫作的時候“始終感覺似乎是用泥土摶塑什么、復原什么、組合什么”,并且“這種感覺仍然縈繞在我的腦海之中。”王彬先生選“酒店”作為研究《水滸傳》的切口是想突出文化在文學中的價值。他認為,酒店之于《水滸傳》,無異于提綱挈領式的關鍵部件,抓住它,便打開了宋代的日常生活狀態和文化處境,同時也復原了酒店作為生活場景在小說中的作用與意義。他通過精心的耙梳與整理,得出《水滸傳》中主要人物命運大都與酒店有關的結論,比如武松,原本是一介草民,因為在景陽岡喝醉了酒而打死老虎,做了陽谷縣的都頭;在獅子樓酒店殺死西門慶給兄長報仇以后,被發配孟州;在快活林酒店,武松打敗蔣門神,為施恩奪回酒店,從而得罪了蔣門神與其后臺張都監,受到陷害,再次成為囚犯;武松殺死張都監與蔣門神等人,逃跑途中被十字坡酒店的小二捉去,張青夫婦發現是武松,把武松打扮成頭陀摸樣,從而逃出孟州,最終上了梁山。總結武松的人生經歷,從百姓到都頭,與酒店有關,從都頭到囚徒也與酒店有關,從囚徒到頭陀則是在酒店中發生的,從此武松的命運發生徹底變化。其他人物,林沖、宋江、李逵、魯智深等也莫不如此。
多年來我們對古典文學的研究,陷于沉寂狀態,鮮有有新意的研究成果問世。為什么會是這樣?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在于沒有新的研究對象,也沒有新的研究方法。為此,王彬先生做出了艱辛的探索,在對象與方法上進行了不懈的努力與探索,他十年前出版的《紅樓夢敘事》與近日出版的《水滸的酒店》都做出了很好的典范。在《水滸的酒店》中,王彬先生將酒店,小說中的生活場景作為考察對象,從具有典型意義的細部入手,他曾經對我解釋,這個細部,精確地講應該是精微之處,用儒家的表述是:“至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是核心細部,并不是一地雞毛式的撿到籃里就是菜。研究對象變了,研究方法也應該隨之改變,比如他十年以前出版的《紅樓夢敘事》,運用了敘事學,而在這部《水滸的酒店》,則采取了中國傳統的考訂,在這個基礎上他又增加了西方的細讀法,中西結合,鍛造了一支銳利的刻刀,對歷史的與文學的酒店精心雕琢。他把這個方法歸納為“微理論”,用這個理論燭照他視心儀的小說,得出了不少令人稱羨的成果,“微理論”或者是一個可以嘗試的研究方法。這就啟示我們,在既有的研究領域,應該有意識地調整思路,調整對象與方法,當然這樣的調整,考驗的不只是研究者的耐心、智力,重要的是對文學的信念和坐冷板凳的勤勉。當一個學者給書店供應一本新書的時候,學者本人也許還是老樣子,還是那么一個普通的個人,但他的書卻從此獲得了獨立,成了學術殿堂里能提供給后來者的一個大世界。
〔責任編輯叢黎明〕
book=79,ebook=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