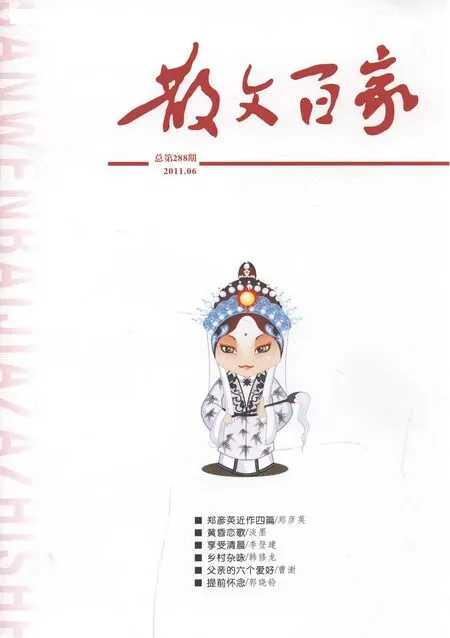父親的六個愛好(外一篇)
●曹 澍
父親的六個愛好(外一篇)
●曹 澍
最近整理書柜,找出三本很舊的精裝書: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和《自然辯證法》。這是父親上個世紀50年代的藏書,因為我那時很喜歡,所以,1975年,我離開家調往另一個單位時就悄悄帶走了。記得當時帶走了二十多本,30多年過去,我從湖北調到河北,搬了七八次家,只剩下這三本了,在我心里非常珍貴。父親是工農出身的干部,文化程度并不高,但他對理論問題有比較濃厚的興趣,買了大量馬恩列斯著作。我少年時代就知道“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這句拗口的名言,就是被父親耳濡目染的。
父親上班有時間就看理論書,為此曾受到一位老上級的善意批評:“老曹,咱們這是工廠,不是馬列主義學院。”父親的這位老上級很有水平,是30年代初期的高中生和黨員,曾在張學良的部隊做過“兵運工作”,是西安事變的見證人。高中畢業在30年代就算“大知識分子”了,毛主席也不過中師畢業。父親是1953年從地方政府調到工廠,他去的第一個工廠就是蘇聯援建的156個項目之一,正是一五計劃時期,也是共和國的黃金時代。父親對理論問題的興趣,一直保持到晚年。讀書看報瀏覽雜志,用紅藍鉛筆勾勾畫畫,還寫了大量心得筆記。我愛人第一次到我家來,看了父親書桌上厚厚的稿子,好奇地悄悄問我:“你爸寫的東西發表過沒有?”其實,父親寫東西沒有任何功利性,他大概從來沒想過投稿,就是喜歡就是興趣,有點像今天的人寫博客。父親還有記日記的習慣,文革時曾被造反派搜走,斷章取義地批判了一陣子。
父親一生有三大愛好:一是買馬列的書捉摸理論問題。二是買京戲唱片聽京戲,父親每次從北京開會回來,我和妹妹等著他從旅行袋里拿出好吃的,他卻興高采烈地捧出一張京戲唱片對母親“炫耀”起來,打開電唱機就陶醉在里面了。文革爆發,京戲屬于“四舊”,母親讓我把近百張京戲唱片用自行車馱到廢品收購站賣了,還有一些送給同學當“鐵環”滾著玩了。當時父親在外地籌建新廠,造反派已開始搗亂,根本沒心思過問他的那些寶貝了。我好買書應該是受父親的影響,但京戲卻沒好起來,因為沒機會。這些年,上班路上,穿過公園,碰上老人們唱京戲,只要有時間,我都要駐足聽一會兒,“樣板戲”除外,那不是真正的京戲。我們學校有位從縣里調來的老教師,到處對人宣稱他會唱京戲,結果一開口全是“樣板戲”,令我大失所望。林語堂先生說,中國人,一到40歲,就把父親留下的瓜皮小帽和長袍馬褂穿起來了。我沒“穿”,但都“收藏在心里了”。
父親的第三個愛好是比較講究穿戴,他是廠級干部中唯一穿西裝系領帶的。我看過父親50年代穿西裝的許多照片,確實很精神。這在北京、上海,在大學、研究所和設計院,在知識分子和民主人士比較集中的地方,可能比較常見比較普遍。但在蘭州、在工廠就算很時髦很前衛了。一群毛料中山裝里,冷不丁冒出個西服革履的,確實很搶眼很另類,頗有點鶴立雞群的味道。我至今不知道他的同事背地怎樣議論他,也沒聽母親說過,大約不會說好話吧。父親穿西裝可能是受了廠里蘇聯專家的影響。上個世紀60年代,父親就改穿中山裝了,這恐怕和當時的政治氣候有關,階級斗爭越抓越緊,大批封資修,西裝肯定是資產階級的,父親也就不好再穿了。我比較注意衣著整潔,近而言之是受父親影響,遠而言之是向周總理學習,周總理是共產黨人中穿衣最精神最帥的。父親每天晚上睡覺前,都要把毛料褲子疊好,搭在椅背上,抽出來的皮帶盤成整整齊齊的一圈,放在書桌上。這個細節給我印象特別深。父親離休后,在設計院那群老頭里也是衣著最講究的一個,毛料中山裝還是一做就一套。我覺得人越老越應該注意穿著,老人一臟,讓人感覺特別不好特別復雜。最起碼讓老伴和孩子特沒面子。上海人有個說法,丈夫衣領臟是妻子沒做好。
父親還有三個小“愛好”,第一個是擦皮鞋。他是一點家務活也不干,但每隔兩三天就要把自己的皮鞋擦一遍,而且非常認真,去浮灰、打鞋油、拋光,一道工序也不少。有時,擦完他的,再擦母親的,邊擦還邊批評母親的皮鞋保養得不好。兩雙鞋擦完,周圍空氣已充滿鞋油味。第二個是攝影,我和妹妹們小時的相片都是父親照的,父親后來說,攝影花錢太多,就不玩了。前兩年,一位照相的朋友看了父親留下的老式德國相機,說,現在能賣16萬。不論多少錢母親都不會賣的。父親的第三個小“愛好”就是看公雞打架。文革后期,在湖北山區三線工廠,允許職工養雞。父親只要下班回來晚了,不用說,準是在路邊看公雞打架,不看完,他是不肯離開的。這和父親從小在農村長大有關,可能是他童年時代和少年時代養成的習慣。農村孩子嘛,沒有什么娛樂活動,只能挑逗公雞們互相斗爭。為此,母親經常笑話父親“童心未泯”。由看公雞打架延伸下來的是父親喜歡看籃球賽,兩者都屬“競技運動”。每有球賽,他就早早拿個小板凳走了,在燈光球場找個好位置,從上世紀50年代就如此。70年代中期我已是廠隊隊員,我在場上打,父親在場外看。他說我打得不好,他有自己喜歡的“球星”。父親工作過好幾個工廠,和廠隊“球星”都是好朋友。父親去世太早,否則,絕對是NBA最忠實的觀眾,而且肯定是姚明的鐵桿粉絲。
父親去世那年才66歲,比我現在的年齡只大10歲。奪走他生命的病是肝癌。這和十年文革有直接關系,氣大傷肝,父親又是個火爆脾氣。
所以,我們一家對文革沒一點好感。
快樂的女出租車司機
天像下了火,熱得人都想吐舌頭,出門辦事,打了一輛車。剛坐進車,看見女司機左邊車窗上拉了一道月白色的窗簾,挺醒目,太少見了,隨口問:怎么拉個簾?
女司機:防曬。平時沒什么,同學聚會,說,怎么曬得這么黑呀!
我這才注意,她胳膊上還戴著白綢子長套袖,手上也戴了手套。
女司機說話很好聽,聲音里非常明顯地洋溢著樂觀快樂喜悅的情緒,很亮很昂揚,因此也很年輕,似乎還有一點點孩子氣。
我從側面看看女司機,40出頭,并不漂亮,個子也不高,還有點瘦。我的座位正前方有個立著的營業證之類的牌子,上面有她的相片,梳個馬尾巴辮,仰著頭,脖子長長的,上衣是圓領的,很有點舞蹈演員的味道,給人的感覺是個熱愛生活的俏麗女人。俏麗是她自己的感覺,也是照片中的她給我的印象,不單指容顏,是韻味氣質。生活中,你覺得自己美,你就會用美的標準要求自己:穿著打扮言談舉止向美看齊,結果,你就是美麗的。所以有人說,女人30歲以前丑,怨遺傳;30歲以后還丑,那就怨自己了。
我歷來喜歡和出租車司機聊天,不論男女,因為他們的信息量大,知道的事情多。有人說,和北京的出租司機聊天,給你的感覺是,他們不是從中南海開會剛回來,就是正要去人民大會堂開會,要不,怎么什么都知道啊。邯鄲的出租司機雖然遠沒有北京的出租司機那么牛氣,但也大都是見多識廣之人,每次聊天,我都有收獲。再說,啞巴似的坐著也悶啊,更沒意思。
我:孩子多大了?
女司機:大的大學剛畢業,小的上高中。
我:哎,你怎么生了兩個?破壞國家的計劃生育政策啦。
女司機笑笑:老大是個女孩。
我假裝悲傷地說:我明白了。去醫院開個證明,說孩子身體不好,養孩不能防老。其實,滿腦子傳宗接代的封建思想。
女司機:你咋盡說實話呀,我還說只有我說實話呢。
女司機說完,快樂地笑起來。
我:小的是兒子?
女司機:對了。
我:兒子學習不好?
我以常規推了,好多家庭都是這樣。為什么?寵的,慣的。
女司機:還行。去年沒考上一中硬線,夠一中軟線,要拿錢;夠三中四中的硬線,我們就讓他去了三中。老大承德醫學院護理專業,正在中心醫院實習。她男朋友去廣州了,她以后也去廣州發展。她說了,我們這個專業最起碼在省醫院,沒有在市醫院的。我們不管她,由她去折騰。再說進中心醫院要找人花錢,聽說十萬都打不住,我們又沒那么多錢。
我:你這個年紀應該趕上高考了,怎么沒上大學?
女司機:我是82年高中畢業,沒考上大學。那時候還沒有補習這一說呢。當時招工機會特別多,也沒想那么多,就進廠上班了。不是跟你吹,我寫字寫文章都不賴,領導挺重視,車間的黑板報、廣播稿都是我寫的。
我:那時興上“五大”,什么電大、夜大的……你沒上?
女司機:上了,上了一年就不上了。和我一起上的,畢業的都當干部了。
我:你愛人什么文化?
女司機:他初中。他畫畫可好了,和他一起畫的那些人,現在都出名了。
我:他現在還畫嗎?
女司機:早就不畫了。掙錢養家,我白天開,他晚上開。
我:太可惜了。那你還寫點東西嗎?
女司機:有時也寫,可寫了給誰看?我女兒剛給我建了個博客,讓我往博客上寫。說,媽你就寫吧,寫了就有人看。現在一天到晚緊緊張張的,也挺累。但我感覺比小區里牽個小狗的女人活得充實。
我:你和我見過的那些出租司機不一樣,你特別樂觀,不像他們總是牢騷滿腹。
女司機:高高興興是一天,愁眉苦臉也是一天,干嘛不高高興興?我就說我們家那口子,一天到晚叨叨的,像個娘們,發那么多牢騷管什么用?還弄得心情不好了。我們家那口子上午睡覺,下午總愛去沁河公園和一幫退休的老頭們爭論毛主席那時候好,還是現在好。他是擁毛派,說現在不好。我不同意。現在吃的什么穿的什么?那時候呢?再說了,現在只要你不懶不傻,總能找份工作干,好好干,就有希望。你別老和當官的比,你說是不是?我女兒昨天還說她爸,不要整天抱怨生活欠了你什么,生活根本就不知道你是誰。這丫頭可會說了,我們娘倆是一派。這不,我們家十年前就在廣廈小區買了房,如今老大也畢業了,基本不用我們管了。
不知不覺,我該下車了。我告訴女司機,我也在廣廈小區住,我掏出紙筆,寫下我的博客地址,我說:你寫吧,最起碼我會看你的博客,慢慢地,我的那些博友也會去看,大家串起門來,看的人就會越來越多。其實,咱們老百姓的生活挺有意思。
女司機拍拍方向盤大笑起來:你要早說在廣廈小區住,我就不跟你講那么多我們家的事了。這下完了,我們家的那點機密全讓你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