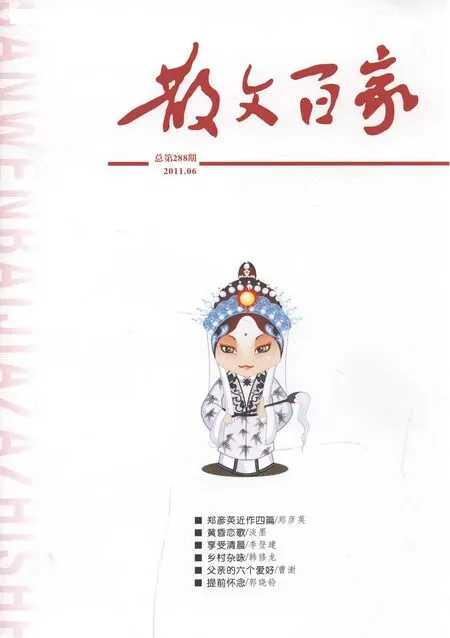“戲迷”父親
●靳天順
“戲迷”父親
●靳天順
我敢說,父親如果有一副好嗓子,或者說有一副正常的嗓子,憑父親對戲曲的執著熱愛、憑父親的聰敏好學、憑父親惟妙惟肖的表演天賦,父親一定會成為舞臺上一位頗有建樹的大腕人物。
但是,“挑擔就怕沒膀子,唱戲最怕沒嗓子”,父親雖然遍身戲曲細胞,可偏偏就缺了一副好嗓子。因為自小嗜煙如命,常年咳嗽,父親的嗓子損壞到了幾近沙啞,說話遠聽像山谷滾雷,近聽似空屋捶鼓,音傳二三里,不知何所云。因此,父親每每觀看戲曲,一旦遭遇了那些唱功、做功不怎么樣的拙劣表演,常常頓足捶胸、氣恨交加,怒罵其玷污祖宗傳統、糟蹋寶貴藝術——憤懣至極點,雙目瞪若銅鈴,鐘馗捉鬼般地怒視著手中的尺長煙袋,咬牙切齒,口吐戲曲韻白:可恨哪可恨!老夫一世朗朗前程,不想卻毀在你這宵小賊子之手……
父親雖然遺憾于舞臺表演,但卻拉得一手令人稱絕的好板胡。
父親一生為農,一雙大手皮糙筋突。但父親看似粗大、拙笨的手指,一旦觸及板胡,即可化變得柔軟光滑、靈巧異常。父親的手指在板胡的絲弦子上按壓移挪、上下翻飛,時而如蛟龍出水,時而似鳳凰翻翅,一曲曲優美、動聽的戲曲曲牌、唱腔過門或如小河流水,或似幽女悲歌,奔騰著、歡叫著、悲戚著、嗚咽著在父親的手指下傾瀉而出……此時的父親,全神貫注,左手把持板胡,右手揮甩弦弓,神態恰似眾多舞臺和電視熒屏上的藝術家一般,腦袋隨著樂曲韻律的疾、緩、張、弛,上下左右有節奏地、劇烈地、夸張地搖擺著。那種幸福、自足和陶醉,完全脫卻了一個農民的憨厚、木訥、內斂和謙卑,仿佛自己已經幻化為肋生雙翅、身披雷電的鯤鵬,馭駕著美妙的天籟之音,翱翔在藍天白云、浩渺無際的穹宇之間;也仿佛是長久孕育在土壤深處的種子萌芽,歷經艱辛一旦拱破堅實的地表,即刻瘋狂地喧囂、張揚著生命和靈魂……數曲拉罷,顆顆豆大的汗珠,便會布滿父親消瘦、黝黑的臉龐和脖頸,少頃,又化作一道道閃閃作光的蚯蚓,掙扎著、蜿蜒著徐徐淌落,為父親原本一絲不茍、滿臉專注的神色平添些許的生動……
每每曲終人散,父親便會長長地、緩緩地呼出一口氣,然后便如雕塑般地口含煙袋,默不作聲,長久地凝望著手中那把漆色油亮、會說會哭的板胡。此刻的父親,滿臉徜徉著的是慈祥、和善與親切。眼神像兩口汩汩噴涌的山泉,流淌的是意猶未盡的回味和與命運進行抗爭后獲勝的快感。良久,父親輕輕地拍拍板胡,微微張口,仰頭向天,仿佛在默默地喚回板胡遠離軀體、依然留戀在音樂天堂的靈魂,也仿佛在傾聽飄蕩在云端、風頭的一縷縷愈來愈遠、愈遠愈悠揚的樂音的腳步……
父親雖然鐘愛、嫻熟板胡,但父親卻將在我們村業余劇團拉“頭弦”的位置讓給了同姓的一位遠房長輩。
長輩是父親的叔輩,小父親十余歲,為人忠厚,性情木訥,年近三十,尚未婚娶。長輩每每聽到父親的板胡一響動,就會從隔壁的家中第一時間跑到父親身旁,舉止恭敬,滿臉羨慕。這個長輩,莊稼人的春種秋收、二十四節氣歌每每記不全,卻天生樂感,父親拉的戲曲曲牌只要聽一兩遍就能哼唱成調調。父親有意為之,用了不到半年工夫,竟把長輩培養成了自己的接班人。長輩第一次登臺坐在樂隊本應屬于父親的位置上,即引來舞臺下許多年輕漂亮女人葵花向陽般的注目和竊竊私語……
長輩結婚后,真誠地要把板胡送還給父親。父親卻拒絕了,對長輩說:你離開了板胡,舞臺上就沒有了你的位置,生活就缺乏了樂趣。而我則不同,只要愿意,舞臺上處處有我的容身之地。
父親所言不虛。因為情有獨鐘,處處留心,父親是我們村劇團公認的多面手,而且還有一個外號“戲偷”。
“戲偷”即偷戲的意思,學名叫做移植。我們鄉是個“戲窩”,全鄉村村有劇團,男女老少人人會哼哼。肩挑茅糞,臭味熏鼻,嘴里卻美滋滋地哼唱著“李世民坐龍位萬民稱頌”;五黃六月,烈日如火,田間地頭你一句我一句地接唱“走一道嶺來翻一架山”……農人雖然常年不舍四季親近土地,但骨子里卻向往著讀書人的風流倜儻、富貴者的衣食無憂,甚至于居官司者的大權在握、朝廷君臣的治國韜略。這種向往表現在形式上,即是在春節或農閑時節,于村中的古戲樓或村口臨時搭建的簡易舞臺上,幾十號有“嗓子”(會唱)、有身段(會表演)的男男女女“粉墨登場”,或扮生旦,或飾凈丑,踩踏著“咚咚嗆嗆”的鑼鼓點,伴隨著琴笛笙弦的抑揚頓挫,或唱、或念、或做、或打,盡情地演繹著才子佳人的愛恨情仇、演繹著朝廷社稷的金戈鐵馬、忠奸紛爭……一般觀眾看戲看的是熱鬧,父親看戲看的卻是門道。哪個村子來了外地劇團演出“生戲”(當地觀眾沒看過的戲),父親是風雨不誤的最忠實觀眾。只要連看兩場演出,父親就能把一部戲的一應人物、劇情、唱詞、唱腔、板式、對白、場景等記得完完全全,一絲不差,然后就在我們村劇團排演,搬上舞臺。
有一年正月,一個河南“亂插班”劇團來我們鄉演出。說實話,這個劇團的演出水平實在不敢恭維,但他們懂得揚長避短、夾縫生存,盡是演出一些“生戲”。父老鄉親天天面對“大米白面”,膩了,當然也想換換口味,嘗嘗山野菜的滋味。一連兩天,觀看外地劇團演出的觀眾人山人海,而其他各村舞臺下的觀眾還沒有舞臺上的演員多。父親急了,撇下來我們家走親戚的舅舅、姑父、姨父一干人等,懷揣一個鉛筆頭、幾頁紙,也去看外地劇團演出了。不料,戲唱到一半,突然下起了鵝毛大雪,舞臺下數千觀眾除我父親外,頃刻間作鳥獸散。劇團演戲的規矩是,只要舞臺下還有一個觀眾,你就不能中途停演,否則就要被扣罰演出費。但二三十號演員給一個觀眾看,畢竟是沒面子的事,演員自然提不起精神來,就開始以說代唱、刪繁就簡,玩起“偷工減料”的把戲,想草草收場。父親火眼金睛,當即就跳上舞臺和劇團團長理論起來。團長先是不屑,認為一個貌不驚人的山區農民,豈能懂得高雅、神圣的藝術,一定是地痞無賴借機生事、找茬鬧場。不料唇槍舌劍中,父親如數家珍,扳著指頭從劇情發展、表演程式、唱腔板式、人物著裝等,一二三四五,頭頭是道,把團長和一干演員“教訓”得五體投地,佩服不已。團長是個江湖人,也是個虛心人,一看今天是大水沖了龍王廟,遇到了“神人”,臉上立馬生動起來,當即就搬出十多部父親從未見過的劇本,又是遞煙,又是端茶搬凳子,一口一個“師傅”,求父親“休嫌我等無知,萬望不吝賜教”。父親受到尊重,得意起來,使出看家本領,認認真真給他們排演了一部戲。晚上一演出,觀眾好評如潮,贊不絕口。第二天上午,我們村劇團就開始排演父親“移植”來的劇目,下午就在我村上演了,而且內容、語言、服飾更加符合我們當地觀眾的欣賞習慣,一下子,吸引各村觀眾猶如海水漲潮地一浪接一浪,滾滾涌向了我村。一連五天,父親下午、晚上去看外地劇團演出,并幫助他們排演劇目,提高演出水平,次日上午再指導我村劇團排演新劇目,走馬換槍,兩不耽誤。外地劇團演出結束后,對我父親一而再、再而三地表示感謝,相識恨晚地走了,而我村劇團的演出劇目也實現了“鳥槍換炮”,全面以舊換新、升級換代。
每年過了正月初八,父親都會帶著我們村劇團前往一山之隔的山西省演出。山西靠近河北一帶的農村百姓,酷愛戲曲,正月唱大戲、鬧社火是各村百年不變的傳統。父親和劇團在山西走村串鄉,如魚得水,每到一村,受到的款待就像是腰纏巨資回鄉投資的華僑一般。這種待遇與榮耀,一直要享受到春種農忙、脫掉冬裝換春裝,往往,還要把明年的演出預約簽訂得滿滿當當。一年之中,父親最歡樂、最興奮、最幸福的日子莫過于此,整日笑呵呵的,精神煥發,像是帶著一幫兄弟姐妹們走進了北京人民大會堂參加戲曲匯演。鑼鼓笙弦奏鳴聲中,父親既是一個總管,又是一個上下前后跑場的雜役,忙碌并痛快著、勞累并幸福著。在父親眼里,并沒有多少文化的兄弟姐妹們,能夠在一席之地的舞臺上“出將入相”,盡情地放肆著自己的精神,釋放著自己對命運的挑戰和不屈,袒露著自己遙不可及的心聲和愿望,無疑是一個農民畢生最大的成就、最大的輝煌。這種精神層面的豐收,堪比甚至更勝于黃土地上的豐收。這種收獲珍藏在心里。慢慢地發酵、慢慢地張揚,勢必會成為充實人生的填充劑和人生幸福的潤滑劑。
哦,父親雖然缺了一副好嗓子,沒有機會成為舞臺上 “唱念做打” 的人物,但父親并不遺憾,因為父親不需要憑嗓子演出,父親是在用心演出,演出的也不僅是戲曲、不僅是藝術、不僅是文化,而是自己豐富多彩、飽滿充實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