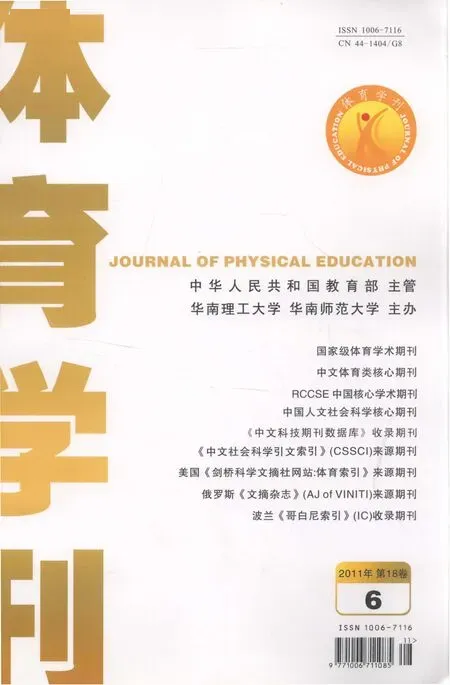體育義務的內涵
宋亨國
(華南師范大學 體育科學學院 民族體質與健康研究中心,廣東 廣州 510006)
體育義務的內涵
宋亨國6
(華南師范大學 體育科學學院 民族體質與健康研究中心,廣東 廣州 510006)
在義務、法律義務概念再認識的基礎上,提出體育義務是指體育法律規定的對體育法律關系主體作為和不作為行為的約束,其本質不僅體現體育法的核心價值——“公平”要求意義上的“應當”,而且體現法律要求意義上的“應當”;其構成要素主要包含體育義務主體、“應當”的體育行為。同時認為,對不同體育主體體育義務進行規定的體育法律包括體育國際法、體育國家法、體育固有法、體育行業協會以及體育權威機構頒布的體育法規。其中,體育固有法對體育行為具有直接的約束力,而體育國家法是保證實現體育義務的最后保障。
體育法;體育義務;體育行為
在體育領域中存在多種義務類型,如體育道德義務、體育習慣義務、體育倫理義務、體育法律義務等,這里所指的體育義務即體育法律義務。體育義務和體育權利共同構成了體育法律的基本內容,二者處于同一個統一體中相輔相成,缺一不可。體育義務對保障體育主體的權利、體育法律關系的順利進行以及體育秩序的穩定具有重要作用。本文在解讀“義務”、“法律義務”概念的基礎上對體育義務的內涵進行分析。
1 體育義務的定義
近些年來,我國諸多學者對體育義務的概念進行了界定,其中代表性的觀點主要有:
第一種觀點是“體育權利是體育主體依法享有的某些權益,體育義務是法律要求體育主體必須履行的責任。二者對立統一,相互聯系、相互依存,權利通過義務來體現,義務由權利而決定”[1]。體育義務是體育法規定的體育法律關系主體必須承擔和履行的某種體育責任[2]。此類觀點有其合理性,“責任”、“體育責任”包含著行為的“必須”和“強制”的內涵,這一點與體育義務關系相當密切。但二者存在著明顯的區別:體育義務多含正面、積極的意思,且“對義務人來說,并不必然意味著不利”[3];而“責任”、“體育責任”多含“制裁”和“不利”的意思,即因不履行或違反體育義務,而給體育主體必然帶來不利后果。因此,不能用體育責任來解釋體育義務,更不能用體育責任來代替體育義務。
第二種觀點認為“體育義務是體育主體做出或不做出一定行為的必要性。如中國公民必須承擔遵守憲法、體育法律、體育道德等義務”[4]。這一觀點以體育義務的基本屬性作為落腳點,顯得有些籠統。體育義務只有經過體育法律規定,才具有“必要性”、“必為性”,但這種法律規定還是靜態的,體育義務的實現還需要通過體育法律關系主體的實踐活動才能夠發揮其價值和功能,離開了主體的體育行為,體育義務的存在就不具備現實意義。同時,“必要性”作為一種依從屬性只反映出體育義務的部分特性,體育責任、體育仲裁等也都具有這種屬性。因此,“必要性”不能完全體現體育義務的本質。
第三種觀點認為“體育義務是國家通過體育法律規定,要求體育法律關系的主體應這樣行為或不這樣行為的一種限制和約束”[5]。這一觀點的合理性成分較多,但也存在一些值得進一步商榷的問題。其一,將體育義務限定為“國家通過體育法律規定”,其范圍過窄,體育固有法、體育權威機構制定和頒布的法規也都對體育義務有著具體的規定和要求。其二,定義中的“應”(應當)本身就包含著“限制”、“約束”的含義,存在詞義上的重復。
2 體育義務概念的重新審視
2.1 義務、法律義務的含義
“義務”作為倫理學和法學研究的關鍵性概念,眾多學者從不同視角對其進行了界定,一種觀點認為“義務”即是指主觀、精神上的“應當”。例如英國學者米爾恩[6]提出:“‘義務’的中心思想是,因為做某事是正確的而必須去做它。說某人有義務做某事,就是說不管愿意與否,他都必須做,因為這事在道德上和法律上是正當的。義務和利益有時沖突、有時和諧,但它們在邏輯上總是有區別的。如果某人負有一種道德義務去做某事,那么他在道德上對是否去做這件事就毫無選擇余地,盡管他對怎么做、何時做、何地做可以進行選擇。”英國哲學家羅素[7]認為:“‘應當’有主觀正當或客觀正當的含義,它是可以解釋‘客觀正當’是一個不能精確的概念,但是可以定義,就它可以定義的范圍來說,根據的是社會或群體中的整體愿望,而不是行為者,或者更確切地說是行為者只居其一的許多人的愿望。”另一種觀點認為“義務”就是應當的行為,即由“應當”加“行為”構成。如張恒山[8]認為:“‘義務’產生于規則和社會的評價和義務人的承諾,主要包含4層含義:表達對人尚未做出行為要求意義上的應當;表達對人已經做出的行為的評價意義上的應當;表達對事物的某種狀態的希望意義上的應當;表達對事物或事物的狀態的推測意義上的應當。”胡平仁[9]提出:義務是一種價值行為,包含著相關主體(個體、群體和社會)的價值評判;是一種期待行為,即一定的個體、群體和社會期待和要求特定的行為主體做出或不做出特定的行為;是一種規范行為,它要受到內在準則(良知、信仰和理性)和外在規則(道德、習俗、法律、教規、政策、章程和紀律)的約束與規范;是一種責任行為,即被期待的主體必須做出被期待的價值行為,否則就要受到相關期待主體的責備、譴責甚至懲罰(包括自我良心的不安)。
本文認為,義務是指“應當的行為”,其核心是“應當”,“行為”是“應當”的載體和途徑。“應當”有很多種含義,如希望、推測、猜測、評價,但能夠作為義務性“應當”含義的只有米爾恩和羅素認為的正確及自律要求意義上以及社會要求意義上的“應當”。
一般而言,法律義務即是指法律要求或規定的“應當的行為”。但何為法律要求或符合法律規定卻始終是學者們研究的關鍵問題。從研究資料看,眾多學者主要從“制裁”、“尺度”、“規范”、“責任”、“約束”和“負擔”等入手闡述了這一個問題。雖然這些觀點不盡相同,但有幾點是可以達成共識的。
首先,法律義務離不開法律主體。權利主體和義務主體共同存在于具體的法律關系中,不同類型的主體具有不同的權利和義務。法律義務的主要目的是保障法律主體的權益及法律關系的順利進行。
其次,“應當”是法律義務的核心內容,是指社會和國家通過法律對主體在一定條件下作為和不作為行為的規定,這是法律義務存在的前提。法律是由國家或社會權威機構制定或認可,并由強制力保證實施的社會規范,它集中反映和體現了國家或社會權威機構的意志、要求。一類行為只有經過法律規定而成為法律義務,才具有法律效應,也才能體現既定的價值目標。因此,離開了法律規定法律義務就無從談起。同時,這種行為規定必須具有“約束性”,其包含兩層含義:一是要求主體通過自律自覺履行法律義務;二是如果未履行或違反法律義務,則會出現“引起法律責任的可能性”,需要通過“社會和國家強制力”予以調整。
最后,法律義務的目的在于規范主體的行為,它必須要通過法律關系主體的現實行為才能夠產生具體的功效。也就是說,使法律義務實現了從期待行為模式到現實行為的轉化。
綜上所述,本文認為法律義務就是指通過法律規定的,對法律關系主體作為和不作為行為的約束。
2.2 體育義務的概念
通過對義務、法律義務概念的分析,也就不難對體育義務進行界定。體育義務作為法律義務的一種,自然要反映法律義務的基本屬性,所不同的只是體育義務必須要通過體育法律、法規進行設定。本文認為體育義務是指通過體育法律規定的,對體育法律關系主體作為和不作為行為的約束。這里需要注意的是:
第一,與其它法律不同,體育法在公平、正義、公正、自由、秩序等法價值中選擇“公平”作為其核心價值,因此體育義務首先要體現這一價值要求意義上的“應當”。
第二,對體育義務規定的體育法律不僅局限于體育國家法,它還包括體育固有法、體育國際法、體育行業協會以及體育權威機構頒布的體育法規。
第三,體育固有法對體育行為具有直接的約束力,而體育國家法是保證實現體育義務的最后屏障。
3 體育義務的構成要素
根據義務、法律義務概念的理解,體育義務的構成要素主要包括體育義務主體、“應當”的體育行為。
3.1 體育義務主體
體育義務是體育法律對體育主體行為的設定,也就是說離開了體育主體,體育義務也就不存在。因此,主體是體育義務的基本要素。在具體的體育法律關系中,體育行政機構、公民、運動員、教練員、裁判員、體育法人等都享有一定的體育權利和履行相應的體育義務,因此他們是直接的體育義務主體。從法理學看,法律對不同主體體育義務的規定并非是簡單地維護或保障其他體育主體的利益實現,它也包含著對義務人自身利益的保護,這從根本上體現出權利主體實現利益要遵循不損他性這一原則。同時,法律也不會對體育義務主體有損害性的體育義務進行設定,這體現了體育法律對體育權利主體和體育義務主體的平等性對待原則。
自然,以上是體育義務主體的主要組成部分,但在現代體育的發展中,國家也成為了重要的體育權力、權利和義務主體,它在根本上決定著體育的走向和發展。這里提到的國家包含3層含義:一是國家是有階級社會的組織;二是國家的本質是階級統治;三是國家是機器,即國家是由許多部件所組成的互相聯系的有機整體[10]。
關于國家義務產生根源的研究由來已久,目前法學界普遍的共識是:國家義務直接源于公民的權利需要,其根本目的在于保障和實現公民的權利。因此,從根本上看,體育權利作為公民的基本權利之一,它也從根本上決定了國家體育義務的產生。從法理學看,國家的體育義務屬于積極義務范疇,主要包含3項內容:一是通過立法途徑,建立公平的體育法律體系;二是通過司法途徑,建立良好的體育糾紛解決、救濟和執行體系;三是通過行政管理途徑,宏觀調控和管理體育發展。這里需要注意幾點:
第一,公民的體育權利決定國家的體育義務,因此國家的體育義務必須針對全體公民,其根本目的在于保障和實現全體公民的體育權利。同時,國家的體育義務也僅通過對全體公民具有普遍性和適足性的法律法規體現出來,如《憲法》、《體育法》、《全民健身條例》等。
第二,在體育的諸領域中,主體不同,其體育權利存在較大差異,因此國家的體育義務也具有多樣性和層次性。
第三,國家為穩定體育發展秩序,保障和實現體育主體的體育權利必須要創建和認可各類體育法律規范,即國家應依正義、公平原則,以共同的政治形式負擔正當、有效的體育法律體系設計及適用的義務。
第四,在現代體育的快速發展中,各種爭議和糾紛不斷出現,國家應為體育糾紛裁決、執行體系的建立提供支持和拓展途徑。
第五,國家的體育義務表現出一定的漸進性。這一特征和當代體育的發展緊密相關。當代體育日益成為社會的主要文化、經濟實體時,其涵蓋內容、發展形式日趨多樣和復雜。在此背景下,不斷出現的體育社會問題決定了國家體育義務內容、形式和途徑的調整和豐富。如將體育權視為是一項人權時,國家的體育義務也要進行深刻的調整和完善。
綜上所述,國家體育義務是復雜的范疇,目前對此研究不足。從現實看,國家已經成為當代體育的核心主體,因此對其體育義務的內涵和外延進行系統研究,不僅決定著體育的走向和發展,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整個社會的和諧進程。
3.2 “應當”的體育行為
迪亞斯[11]441認為:“對行為的控制主要是由(法律)義務來進行。脫離開行為,就不可能研究(法律)義務。”馬克思也指出:“權利和義務是國家通過法作用于社會的橋梁。國家首先是通過法確定規范模式,指給社會人們以行為模式,從而使法定權利和義務轉化為現實權利和義務,形成具體的法關系,使社會秩序得以形成,以實現法的功能。”[12]因此,“應當”的體育行為是體育義務的核心內容,即主體的體育行為生成并體現出體育道德、精神內涵要求意義上的“應當”以及體育法律要求意義上的“應當”。具體而言:第一,“應當”的體育行為指向要符合社會的期待與認可,即對體育價值的共識[13-14]。“法律義務是一個帶有道德意味的概念。在漢語中,義務一詞的文義有‘按義理務必應作之事’的意思。因此,‘有義務’與‘被強迫’是有所不同的。‘有義務只意味著被一項正當理由(權利)所約束和支配,而不是被其他力量所約束和支配。’”[15]因此,法律對體育義務的規定必然要體現體育的價值和精神內涵。義務必須與流行的道德觀念相一致,至少不與之過分悖離,社會能在一定程度上承受義務與道德觀念之間的沖突,但這種沖突一旦達到尖銳的程度,義務就必須變更或者廢除。正如艾倫所言,如果法律要獲得人們的尊重,義務就不應過分逾越既定的道德觀念[11]439-440。隨著現代體育的發展,體育多元價值體系已經獲得人們的廣泛認同,尤其是在今天,“構建體育發展秩序,實現體育良性發展,提高大眾健康素質”業已成為體育發展之根本目標。因此,反映體育價值,尤其是“公平”價值的要求就是設定體育義務具體內容的先決條件。
第二,“應當”的體育行為必須經過體育法律的規定才能生成并形成具體的體育義務。一方面,體育法律規定是指對“社會期待體育行為”的設定。這類行為深刻反映出社會群體對體育的期望和要求,其根本目的在于保障體育主體權利實現、體育法律關系順利進行和體育秩序的穩定,這是構成體育義務內容的基礎。如我國《體育法》中規定:“國家發展體育事業,開展群眾性的體育活動,提高全民族身體素質;國家對青年、少年、兒童的體育活動給予特別保障,增進青年、少年、兒童的身心健康;教育行政部門和學校應當將體育作為學校教育的組成部分,培養德、智、體等全面發展的人才”等。另一方面,“規范性”是法律義務的本質屬性,體育義務雖然要深刻反映和體現社會對體育價值的共識,但不等于二者沒有區別,相反,它們之間有著本質的臨界點。體育認識、體育道德、體育價值等只有通過一定程序上升到法律層面,才具有穩定性、確定性、約束性和必須性。因此,體育義務應當必須是法律實證的。正如迪亞斯[11]450所言:“雖然某一特定義務中的‘應當’或者‘不應當’可能最初來源于某個人的意見,但一旦披上法律的外衣而成為‘法律’,則該意見就退化為背景,甚至完全消失。因為該‘應當’已具有某種獨立的價值,即忠于法律的價值。”這種情況在體育中廣泛存在,如產生于資本主義工業革命背景下的《奧林匹克委員會憲章》,正是由于顧拜旦、西蒙等人的不懈努力,最終以體育國際法規范的形式確定下來,并在全世界產生法定效力。
體育義務的“應當”一方面說明體育法律設定的行為模式內在邏輯上的當為性,即以“必須”、“是”的存在形式表現出來;另一方面,體現的是對這些設定的體育行為外在“應當的”表現形式,即表現出體育義務履行的正當性和合理性。這里需要注意的是,由于體育的特殊性,在訓練方法、運動技戰術體系創新方面,即使得到社會或相關機構認定,也不能申請專利權,其他主體也可以無償使用,不必履行法律一般意義上的義務。
第三,我國的《體育法》屬指示性法律規范,其中一些條款用語中的“應當”和“必須”并不必然意味著一項體育義務的規定,而是對一類體育行為提出了指示性的要求。如我國《體育法》第10條規定:“社會體育活動應當堅持業余、自愿、小型多樣,遵循因地制宜和科學文明的原則。”第13條規定:“國家機關、企業事業組織應當開展多種形式的體育活動,舉辦群眾性體育競賽。”這種“應當”是對體育義務進行整體的或宏觀層面的規定,目的在于對體育主體(法人)的行為提供法律上的引導。
這里需要注意的是,雖然在體育法律規范上已經預先排除了主體對體育義務及不當體育行為的選擇,但在具體的法律關系中,主體卻能夠對體育行為進行自主選擇,即社會期待或法律要求的體育行為與現實體育行為發生分離,而且在具體的體育活動中二者也必然存在一定程度的分離。其包含3層含義:一是在義務主體自主選擇下,體育義務期待行為并不必然轉化為其要求一致的行為,如為了提升運動成績而可以采取不同的合法行為。二是當主體的體育行為違背法律規定的要求時,體育義務也并不因此而消失,相反,可能還會提高其約束的程度。三是當主體體育行為違反了體育法律規定的要求時,就出現了能夠引起體育責任的可能性,也就是說,出現了通過社會、國家強制體育法律關系主體履行義務或承擔體育責任的可能性,這其實就是體育義務動態性的體現。
體育義務作為獨立的范疇具有十分復雜的內涵,對不同體育義務主體的作為和不作為進行科學合理的法律規定,不僅是保障主體體育權利順利實現的必要條件,而且也是維護體育秩序穩定的基礎條件。因此,需要立足我國社會、經濟、文化發展的現實狀況,依據體育發展規律進行系統的論證。社會主導價值觀為體育義務的規定提供了觀念上的導向性支持,體育法律體系為體育義務規定提供了現實的保障,兩者必須緊密關聯,不可偏執其一。
[1] 張厚福. 體育法理[M]. 北京:人民體育出版社,2001:61.
[2] 湯衛東. 體育法學[M]. 南京: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61.
[3] 張恒山. 法理要論[M].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305.
[4] 中國體育科學學會,香港體育學院. 體育科學詞典[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276.
[5] 董小龍,郭春玲. 體育法學[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21.
[6] A J M米爾恩[英]. 人的權利與人的多樣性——人權哲學[M]. 夏勇,張志銘,譯. 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5:34-35.
[7] 伯特蘭·羅素[英]. 倫理學和政治學中的人類社會[M].肖巍,譯.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89.
[8] 張恒山. 義務、法律義務內涵再辨析[J]. 環球法律評論,2002(冬季號):446.
[9] 胡平仁. 法律義務新論[J]. 法制與社會發展,2004,60(6):132.
[10] 列寧[蘇]. 國家與革命[M].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11] 迪亞斯[英]. 法律的概念和價值(法理學論叢)[M].黃文藝,譯.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
[12] 張光博. 堅持馬克思主義權利義務觀[M]. 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8:21.
[13] 裴洋. 國際體育線織規章的法律性質及其在中國的適用問題[J]. 體育學刊,2010,17(11):20-25.
[14] 閆成棟,周愛光. 職業體育俱樂部的法律性質[J].體育學刊,2011,18(1):53-56.
[15] 鄭成良. 現代法理學[M]. 長春:吉林大學出版社,1999:93.
Connotations of sport obligation
SONG Heng-guo
(National Constitution and Health Research Center,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Guangzhou 510006,China)
On the basis of reviewing the concepts of obligation and legal obligation, the author put forward the following opinions: sport obligation refers to the restraints specified by sport laws on the behaviors of feasance and nonfeasance on the subjects of sport legal relations; its essence is embodied but only in the “shalls” in terms of“just” requirements-the core value of sport laws, but also in the “shalls” in terms of legal requirements; its constituent elements mainly include sports obligation subjects, and sports behaviors in terms of “shall”. In the mean time, the author concluded via analysis that sport laws which specify the sport obligations of different sport subjects include the national sports law, intrinsic sport law, international sports law, and sports regulations promulgated by sports industrial associations and sport authorities, among which the intrinsic sport law has a direct binding force on sport behaviors, while the national sport law is the last assurance for ensuring the realization of sport obligations.
sport law;sport obligation;sport behaviors
G80-05
A
1006-7116(2011)06-0027-05
2011-03-11
國家體育總局體育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項目“我國體育行政主體的體育義務研究”(1645SS11054)。
宋亨國(1974-),男,副教授,碩士,研究方向:體育法學、體育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