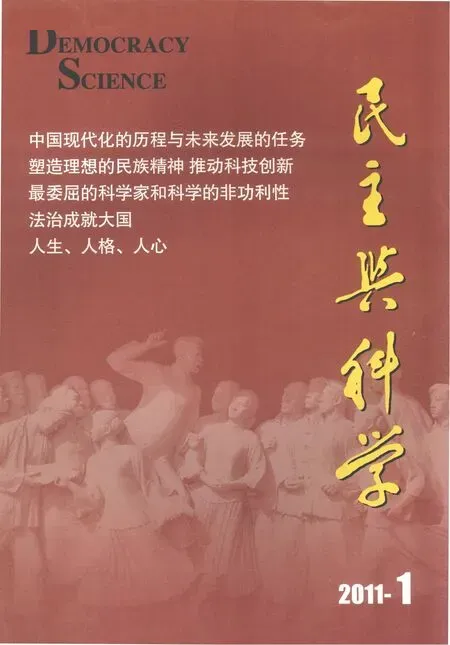大學(xué)學(xué)術(shù)評價(jià),如何與時(shí)俱進(jìn)
■丁福虎
大學(xué)學(xué)術(shù)評價(jià),如何與時(shí)俱進(jìn)
■丁福虎
一種先進(jìn)的學(xué)術(shù)評價(jià)方法,只要隨著時(shí)間的流逝,就不可避免地被一些趨利蟲尋找出漏洞,并以極快的速度加以利用和傳播,這就像夏天的米要出蟲子一樣,學(xué)術(shù)創(chuàng)新工作產(chǎn)生了功利化行為之后尤其如此。事實(shí)上,學(xué)術(shù)不端行為與學(xué)術(shù)評價(jià)之間的博弈,從來都沒有停止過。關(guān)于學(xué)術(shù)成果之間數(shù)量與質(zhì)量的關(guān)系,學(xué)術(shù)界與學(xué)術(shù)評價(jià)領(lǐng)域也是有定評的,比如同行評議、核心期刊、期刊影響因子、引文分析等評價(jià)方法都在一定的時(shí)期取得過積極的效果,但也被一些趨利蟲多方利用,可謂有利有弊。2005年美國科學(xué)家赫希又提出了“高影響力論文”的概念,簡稱H指數(shù)。通俗講,H指數(shù)就是一個(gè)學(xué)術(shù)人員發(fā)表了H篇被引用次數(shù)不少于H次的論文,這個(gè)H的數(shù)值就是該學(xué)術(shù)人員的H指數(shù)。例如赫希本人的H指數(shù)是49,這表示在他已發(fā)表的論文中,每篇被引用了49次以上的論文總共有49篇。赫希認(rèn)為H指數(shù)能夠比較準(zhǔn)確地反映一個(gè)人的學(xué)術(shù)成就大小。之后,一些旨在評價(jià)學(xué)術(shù)人員績效的新方法不斷問世。由于這些評價(jià)方法能夠兼顧學(xué)術(shù)論文的數(shù)量與質(zhì)量,在應(yīng)用上簡單明了,而且對目前重“量”輕“質(zhì)”、重“表”輕“里”的學(xué)術(shù)評價(jià)標(biāo)準(zhǔn)具有明顯的超越性,因而在國內(nèi)學(xué)術(shù)界引起了很大的轟動,并產(chǎn)生了一批比較可觀的學(xué)術(shù)成果。
我們知道,赫希的H指數(shù)是49,這首先是他要發(fā)表49篇論文。事實(shí)上這只是他發(fā)表眾多論文中的佼佼者。其次是這些論文要被有相當(dāng)水準(zhǔn)的科學(xué)工作者在研究工作中進(jìn)行引用,并且引用之后能夠發(fā)表并進(jìn)入某些有一定質(zhì)量的數(shù)據(jù)庫源期刊上;引文條數(shù)達(dá)2401次以上,這相當(dāng)于至少有2401人次的同行科學(xué)家對他的工作進(jìn)行了公開的表決。您想,想擺平這么多人會有多么不容易,而且這些人的論文發(fā)表還要受到期刊編輯和審稿專家的嚴(yán)格審查。其三是被引用的時(shí)間要相對快速和集中,不能像孟德爾那樣石沉大海,生前不為人知!所以說,能夠鉆H指數(shù)評價(jià)體系空子的人,要有相當(dāng)?shù)膶W(xué)術(shù)貢獻(xiàn)和相當(dāng)長的學(xué)術(shù)經(jīng)歷才可以。H指數(shù)的研究還表明,美國研究型大學(xué)晉升副教授H指數(shù)為10~12,晉升正教授的H指數(shù)為18,美國科學(xué)院院士一般在45以上。那么在國內(nèi)呢?筆者曾經(jīng)利用中國知網(wǎng),調(diào)查了某省10多所本科院校中的法學(xué)和經(jīng)濟(jì)學(xué)學(xué)術(shù)人員,每個(gè)學(xué)科隨機(jī)抽取14位任職多年的正教授,他們從事學(xué)術(shù)工作的時(shí)間通常都在20年以上;之后以論文的第一作者進(jìn)行文獻(xiàn)全庫檢索,統(tǒng)計(jì)數(shù)據(jù)顯示這些正教授的H指數(shù)大約為4。那么,H指數(shù)4是一種什么樣的學(xué)術(shù)概念呢?根據(jù)H指數(shù)的定義,可以得知H指數(shù)4就是一個(gè)學(xué)術(shù)人員發(fā)表了4篇被引證次數(shù)不少于4次的論文,理論上相當(dāng)于有16人次以上的同行科學(xué)家對他的工作進(jìn)行了公開的表決,按照通常的標(biāo)準(zhǔn)來判斷,如果論文被引證4次,個(gè)人的自引一般會在一兩次之間,這是個(gè)人課題深入研究的一項(xiàng)基本標(biāo)志;而其他同行的引證僅有兩三次。如果一篇論文在發(fā)表之后的引證次數(shù)達(dá)不到4次,這就表明該項(xiàng)研究很少能引起同行之間的關(guān)注,甚至個(gè)人也缺乏持續(xù)深入的研究,這必將導(dǎo)致學(xué)術(shù)創(chuàng)新的萎縮或低水平重復(fù)研究,百家爭鳴從何談起?H指數(shù)4與美國研究型大學(xué)晉升正教授的H指數(shù)18相比較,可謂極其懸殊!同時(shí),筆者利用中國知網(wǎng),調(diào)查了某地2009年晉升的20多名正教授,發(fā)現(xiàn)他們的平均H指數(shù)只有2.47,而人文社科類的平均H指數(shù)只有2.25。其中H指數(shù)達(dá)到4的僅占28.57%。H指數(shù)4,這個(gè)不算太高的學(xué)術(shù)指標(biāo),為何就這么難以逾越呢?
筆者從事學(xué)術(shù)管理工作二十多年,認(rèn)為這種狀況主要是由以下原因造成的。
首先是學(xué)術(shù)不端,有恃無恐。在今天,學(xué)術(shù)研究工作已經(jīng)成為一種謀生的職業(yè)。學(xué)術(shù)工作者雖然具有較高的人文素質(zhì),但驅(qū)利的軟肋人人皆有,一旦有合適的條件和機(jī)會,就不可避免地陷入其中。學(xué)術(shù)不端行為產(chǎn)生的直接原因,一是當(dāng)代學(xué)術(shù)出版物和學(xué)術(shù)文獻(xiàn)呈指數(shù)曲線增長,同一學(xué)科的專家都不能窮盡本學(xué)科的文獻(xiàn),因此作弊者極少能被發(fā)現(xiàn)。當(dāng)學(xué)術(shù)不端行為被發(fā)現(xiàn)的概率接近或低于自然災(zāi)害發(fā)生的概率時(shí),學(xué)術(shù)道德的免疫防線就會開始崩潰。作偽者就會認(rèn)為搞不端行為的方式非常劃算,如果有人被偶爾揭露出來,他們會認(rèn)為是自己不夠幸運(yùn),還認(rèn)為這種不幸運(yùn)在人類社會中普遍存在。二是學(xué)術(shù)研究高度專業(yè)化之后,許多領(lǐng)域的前沿工作很多都是資歷較淺的學(xué)者在開展。但由于資歷的局限,他們很少有參與評價(jià)的機(jī)會。而有資歷參加評價(jià)的,大多又不是真正的同行,也很少在前沿領(lǐng)域繼續(xù)活動,這就使得不端行為有了可乘之機(jī)。在這種投機(jī)心理的支配下,作偽者便會前赴后繼,舍生忘死地去搞不端行為。這時(shí)再加上發(fā)現(xiàn)后懲治不力,這種示范效應(yīng)會使學(xué)術(shù)不端行為像決堤的洪水一樣泛濫成災(zāi)。中國傳媒大學(xué)一項(xiàng)關(guān)于大學(xué)生網(wǎng)絡(luò)道德現(xiàn)狀的調(diào)查顯示:超過53%的大學(xué)生承認(rèn)自己抄襲論文,認(rèn)為抄襲是一種學(xué)術(shù)敗壞的占38%。看來,學(xué)術(shù)不端就是一塊“臭豆腐”,雖然臭不可聞,但吃起來卻很“香”!
其次是評價(jià)滯后,本末倒置。學(xué)術(shù)界中的意志不堅(jiān)定者為了無償占有知識創(chuàng)新的勞動價(jià)值,在與評價(jià)者進(jìn)行博弈時(shí)可謂機(jī)關(guān)算盡:當(dāng)評價(jià)者只是盯著紙質(zhì)材料時(shí),非法期刊、假書號、假證書便開始“一條龍”出現(xiàn)。當(dāng)評價(jià)者學(xué)會了網(wǎng)絡(luò)查詢時(shí),各種“槍手”在網(wǎng)絡(luò)中滿天飛,商業(yè)出版物比比皆是,甚至還誕生了驗(yàn)證假學(xué)歷的假網(wǎng)站。由于造假者的成本低下,致使造假者捷足先登。而又由于晉升指標(biāo)的限制,導(dǎo)致真正打硬仗的創(chuàng)新者被甩在造假者的身后,就像《紅樓夢》里面一副對聯(lián)形容的那樣:“假作真時(shí)真亦假,無為有處有還無”。學(xué)術(shù)界有人強(qiáng)烈抨擊論文的考核標(biāo)準(zhǔn),說是“逼良為娼”,卻不知搞不端行為的人壓根就不講學(xué)術(shù)規(guī)則。最為可怕的是評價(jià)的本末倒置,起點(diǎn)優(yōu)勢有時(shí)竟然會優(yōu)于終點(diǎn)評價(jià),站在起跑線上的成績會比終點(diǎn)沖線時(shí)更加厲害。比如,論文數(shù)量會高于論文的質(zhì)量,研究經(jīng)費(fèi)的數(shù)量會高于研究成果的質(zhì)量,年輕時(shí)取得的學(xué)歷優(yōu)勢會高于一個(gè)人取得的終身成就。
其三是狐貍洞口,由誰來堵?有一則民間故事講,有一窩狐貍的洞穴有一前一后兩個(gè)洞口,四處透風(fēng),小狐貍怕不安全想堵住其中的一個(gè)。老狐貍告誡小狐貍:“堵住了洞口,獵人來了往何處跑?”事實(shí)上,一些單位也知道現(xiàn)行評價(jià)機(jī)制的弊端和漏洞,但是大家都存在泡沫績效,自己把泡沫擠得太干,如何參與社會大蛋糕的分配?都說職稱貶值,但沒有那么多的增量職稱,如何來增加學(xué)術(shù)人員的工資?如何來實(shí)現(xiàn)大學(xué)的擴(kuò)招?如果真的堵住了漏洞,管理者自身的利益調(diào)控幅度會更小。所以說學(xué)術(shù)評價(jià)一日不作為,學(xué)術(shù)不端行為便難以有大的改觀。
那么如何改進(jìn)現(xiàn)行的評價(jià)機(jī)制,逐漸提高學(xué)術(shù)人員的學(xué)風(fēng)水平呢?
一是改革評價(jià)觀念,“終點(diǎn)優(yōu)于起點(diǎn)”。“終點(diǎn)優(yōu)于起點(diǎn)”理論,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修正學(xué)術(shù)評價(jià)的一些失誤,減少學(xué)術(shù)評價(jià)的漏洞發(fā)生。在作物的生長階段中,有發(fā)芽、生根、開花、結(jié)果等環(huán)節(jié),根據(jù)“終點(diǎn)優(yōu)于起點(diǎn)”的理論,開花優(yōu)于發(fā)芽,結(jié)果又優(yōu)于開花。在體育競賽中,進(jìn)入決賽的成績一般要優(yōu)于復(fù)賽,進(jìn)入復(fù)賽的成績一般又優(yōu)于初賽。而在學(xué)術(shù)評價(jià)當(dāng)中,研究項(xiàng)目一般可以分為課題中標(biāo)、經(jīng)費(fèi)劃撥、階段成果、最終成果、成果應(yīng)用等階段,倘若有人將課題中標(biāo)的評價(jià)高于成果應(yīng)用階段,則屬于本末倒置;如果一項(xiàng)成果應(yīng)用在國內(nèi)取得了空前的成就,卻不如一項(xiàng)國家級科研項(xiàng)目更實(shí)惠,也屬于本末倒置。在學(xué)術(shù)論文的評價(jià)中,論文發(fā)表、論文被引、H指數(shù)是一個(gè)遞進(jìn)的發(fā)展過程,如果出現(xiàn)了論文發(fā)表數(shù)量的評價(jià)優(yōu)于引文數(shù)量的評價(jià),那是在渾水摸魚,也應(yīng)屬于本末倒置。弄清楚了“終點(diǎn)優(yōu)于起點(diǎn)”的理論,學(xué)術(shù)評價(jià)就不會迷失大方向,學(xué)術(shù)評價(jià)的創(chuàng)新就會日新月異。
二是區(qū)分不同對象,制定相應(yīng)措施。筆者在中國知網(wǎng)上對幾所高校新晉升的中級、副高級、正高級三類職稱進(jìn)行第一作者全文檢索,發(fā)現(xiàn)新晉中級職稱的文獻(xiàn)收錄平均為2.66篇,引證次數(shù)平均為0.8次;新晉副高級職稱的全部文獻(xiàn)累加收錄平均為10.37篇,引證次數(shù)平均為9.12次,H指數(shù)1.88;而新晉正高級職稱的全部文獻(xiàn)累加收錄平均為22篇,H指數(shù)2.47。所以,中級職稱的評價(jià)看文獻(xiàn)收錄的數(shù)量,要比看容易造假的紙質(zhì)期刊先進(jìn);副高級職稱的評價(jià)看文獻(xiàn)的引證次數(shù),要比看文獻(xiàn)的收錄篇數(shù)先進(jìn),因?yàn)橛幸C的論文泡沫相對較少;正高級職稱的評價(jià)看文獻(xiàn)的H指數(shù)會更先進(jìn),因?yàn)镠指數(shù)不便于搞“短、平、快”工程。但是這些評價(jià)必須在同一學(xué)科內(nèi)進(jìn)行。比如,成果鑒定本來是用于評價(jià)工程技術(shù)成果的,現(xiàn)在卻用來評價(jià)人文社科成果。美國的《社會科學(xué)引文索引》在全球范圍內(nèi)收錄了四千多種人文社科類期刊,卻沒有中國大陸的一份期刊。按此標(biāo)準(zhǔn),中國的人文社科學(xué)術(shù)水平竟然排在菲律賓和土耳其之后!所以說,美國標(biāo)準(zhǔn)在意識形態(tài)較濃厚的領(lǐng)域就不適應(yīng)。
三是利用電子資源,減少人為干擾。學(xué)術(shù)評價(jià)之所以出現(xiàn)那么多不盡人意的地方,就在于人們肆無忌憚地加入了許多學(xué)術(shù)之外的調(diào)和劑。有人不適合從事學(xué)術(shù)工作,但在學(xué)術(shù)之外卻比較活躍。單位要把他們流動出去,既缺少相應(yīng)的機(jī)制,又沒有合適的職位和社會保障,因而這項(xiàng)工作大多是虎頭蛇尾。幾百種非法期刊能夠順利擠入職稱評定的材料堆里,使“辦刊者”成為暴發(fā)戶,使造假者順利晉升,許多情況下并不是審查者不知情,而是他們不敢講出來。即使是有人敢于舉報(bào),處理時(shí)大多數(shù)都是輕描淡寫。近年來,江蘇、福建、吉林、廣西、山東等省市開展職稱網(wǎng)絡(luò)評審,要求進(jìn)行電子文獻(xiàn)檢索驗(yàn)證,就是試圖在減少這些人為因素的干擾。如果各個(gè)部門建立了完善的電子檔案,利用權(quán)威的電子文獻(xiàn),以及中國知網(wǎng)等部門研制的“學(xué)術(shù)不端行為監(jiān)測系統(tǒng)”進(jìn)行評價(jià),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評價(jià)的公信力。
四是公示評價(jià)材料,受理網(wǎng)絡(luò)舉報(bào)。學(xué)術(shù)不端行為的大面積淪陷,僅靠少數(shù)管理者是無能為力的。一方面是管理者在很多情況下不熟悉專業(yè)前沿;另一方面是管理者在明處,極易受到打擊報(bào)復(fù)。2010年8月,方舟子遇到襲擊,就是一個(gè)典型案例。如果將各種評價(jià)材料長時(shí)間公示在網(wǎng)絡(luò)上,吸引眾多的專業(yè)人員參與進(jìn)來,由他們提供可靠的線索和準(zhǔn)確的事實(shí),然后由管理者去驗(yàn)證,則會有效地打擊各種學(xué)術(shù)不端行為。尤其是將與被評價(jià)者有著切身利益沖突的群體調(diào)動起來,則可以明顯遏制學(xué)術(shù)不端行為發(fā)生的概率。
五是應(yīng)用先進(jìn)方法,提高博弈能力。任何學(xué)術(shù)評價(jià)方法都是特定時(shí)期的產(chǎn)物。在提高學(xué)術(shù)評價(jià)的博弈能力方面,我們可以向其他領(lǐng)域?qū)W習(xí),比如體育界中的反興奮劑做法,治安領(lǐng)域的禁毒做法,以及政府查獲偽鈔的做法等,那是下了血本才有所收效的。假如我們的學(xué)術(shù)評價(jià)手段一直停留在紙質(zhì)文獻(xiàn)時(shí)代,而面對千變?nèi)f化的網(wǎng)絡(luò)時(shí)代熟視無睹、無暇顧及、善惡混淆,一邊評價(jià)一邊心安理得裝“紅包”,心慈手軟、敷衍了事、你好我好大家都好,則學(xué)術(shù)評價(jià)也就失去了最基本的意義,我們的知識創(chuàng)新體系就會魚龍混雜,就會產(chǎn)生可怕的“劣幣趨良”和“鳩占鵲巢”現(xiàn)象,直到一個(gè)民族失去自己的基本思維能力。事實(shí)上,學(xué)術(shù)評價(jià)的前沿領(lǐng)域,都時(shí)刻不停地誕生著各種新理論和新方法。評價(jià)者只要虛心學(xué)習(xí),勇于探索,無私無畏,不斷改進(jìn),就一定能夠有所超越。
(作者單位:河南科技學(xué)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