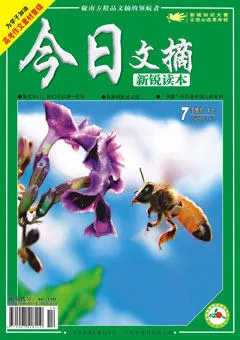我和父親季羨林
2011-12-29 00:00:00季承
今日文摘
2011年14期
寫悼文,我會用這個名字,因為生前他很少被叫“爸爸”。
我小時候沒叫過他“爸爸”,年長了隨兒女叫他“爺爺”。叫“爺爺”可能還順口些,叫“爸爸”總覺得生疏。他最后的日子里,我也很少叫他“爸爸”,在外人面前,就叫他“季先生”。沒有爸爸,我還為此遭到小伙伴嘲笑,家里人常指著墻上一幅照片,說那就是爸爸。長到11歲,我才和回國的父親見上面。父子間的疏離,他心里是明白的,心知肚明。
我的名字季承,是自己取的。原名季延宗,是祖父給取的,寓意香火繁茂。但我對這個名字不感興趣。高中時,我在濟南寫信到北京,叫父親給改個名字,但他拒絕了,說名字是祖宗賜的——直至“文革”“破四舊”時,我才有了個心儀的名字。
父親對我的影響,身教甚于言傳。我和姐姐都很刻苦,很樸素,也不圖名圖利。我們一家人都比較淡泊。鄭重其事地給誰過生日,這在我們家是沒有的。據說父親九十大壽過得很熱鬧,但當時祖母、媽媽和姐姐都已不在人世,我也沒有參加。
在家里,父親寡言,情感很少外露。祖母——實際上是叔祖母,90歲走的(父親兒時過繼給了叔祖父)。父親在文里稱她“季家第一功臣”。早年他在國外,后來又常年獨居北京,只有寒暑假才回濟南。這些日子,都是祖母撐起山東的家,照顧媽媽、姐姐和我。父親對她很欽佩,也很感激,平素對她特別恭敬。但祖母走的時候,他所有悲傷的表現,就是陷入更深的沉默。媽媽、姐姐走的時候,也一樣。
相當長時間,家人都不認為家庭對父親是重要的。……
登錄APP查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