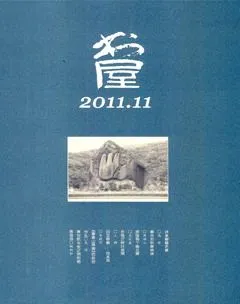“死”在句下
唐人死在沙場,宋人死在古藤蔭下,明人死在芍藥欄邊一片冷石上。清人最憋屈,死在字下。近代以降稍好,死在句下,倒也別有一番風流。
“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回”。“黃沙百戰穿金甲,不破樓蘭終不還”。唐詩的豪情,入宋便闌珊,徒增了些悠閑蒼老。宋人偏好幽暗里的靜謐,連陽光都害怕,更何談塞外?請看排行頭四位的文人,蘇東坡說:“惟有柳湖萬株柳,清陰與子共朝昏。”王荊公說:“春風取花去,酌我以清陰。”陸放翁說:“百花過盡綠陰成,漠漠爐香睡晚晴。”辛稼軒說:“病起小園無一事,杖藜看得綠蔭成。”秦少游晚年受黨爭迫害,徽宗即位始起復,無奈歸途中卒于藤州。他有一首詞《好事近·夢中作》,其中兩句“醉臥古藤陰下,了不知南北”,便被宋人視為詞讖。
宋人的古藤陰固比不得唐人的沙場,然究竟是天地間的山水,自然界的花樹,到了明代,死所更狹小了,只是假山假水、亭臺樓閣。湯顯祖渴望后花園里的死,牡丹亭畔,湖山石邊,梅樹依依可人,生生死死隨人愿,便酸酸楚楚無人怨。義仍的摯友袁中郎也說:“與其死于床第,孰若死于一片冷石也?”
明亡,天下是別人的了,只留下故紙堆。清人的死,頗印證了中國傳統思想之劣根性。清人的學問號稱“樸學”,其實一點兒也不樸素,在在透出貴族氣、權勢味。清人整理經典,字字皆追根溯源,此一步驟固然重要,卻非根本。須知字在句中方“活”,離了句的字是“死”字。清人走上歧途,把全部精力都用在“死”字上。只問字的出身,不問實際作出的貢獻,出身決定一切,絲毫不得亂來,等級森嚴,界限分明,于是創造力與自由精神皆被扼殺。
從“死”在字下到“死”在句下,實可以見出近代學術的轉向。西學東漸,傳統再生,近現代哲學、史學、詮釋學等一道道新視線,開始貫注于古代經典之上,拂其塵土,煥然重光。
近代以降,死在句下最著名的例子,當屬王國維的“三境界”之說:
古今之成大事業、大學問者,必經過三種之境界:“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眾里尋她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此第三境也。”(《人間詞話》)
王國維早歲研習叔本華、尼采哲學,故有此一番創見。王國維“死”在句下,死在這三句話中,他將隨這三句話一起不朽,而塵世間的種種遺存,如墳墓、如紀念碑、如毀譽、如流言,豈能免東海揚塵之變乎?
無獨有偶,近現代不少哲學家有著與王國維一樣的嗜好,以文學經典之句表述哲學思想。如熊十力《十力語要》卷一《答謝石麟》:“今日治哲學的人,如有超出眼光,能理會《中論》玄旨于文言之外,必另有一般樂趣。宋人詞云:‘眾里尋他千百度,回頭驀見,那人正在燈火闌珊處。’此言雖近,可以喻遠。”同書卷一《與張東蓀》亦云:‘馳求知識者,反己自修,必豁然有悟。’眾里尋他千百度,回頭驀見那人正在燈火闌珊處’下自注小字:‘喻意,尋思熄處,冥證真理。’”
毋庸置疑,熊十力受《人間詞話》影響甚深,只可惜熊先生沒能死在句下。熊十力的高足牟宗三,總算是死在南唐馮延巳的句下了,其《中西哲學之會通》云:“康德的說法:現象是某種東西現于我們的眼前,現到我這里來,它就是現象;而我則喜歡如此說,即:現象是為感性所挑起所皺起的,此可以‘吹皺一池春水’來比喻。”
現代另一位杰出的哲學家賀麟,則死在了李杜的詩句下,《近代唯心論簡釋·時空與超時空》云:
中國哲學家中陸象山、陳白沙可以說是持主觀時空論的人。陸有‘宇宙即是吾心,吾心就是宇宙’的名言(宇即空,宙即時)……又詩人如李白“天地者(空),萬物之逆旅,光陰者,百代(指客觀無限之時間)之過客”,頗能美妙地道出常識中認時空為客觀實在之見解。而杜甫詩中如“乾坤萬里眼,時序百年心”二名句,則頗具主觀的時空觀之適度。此二語意思本甚含蓄,如要加以哲學的解釋,則可釋為“乾坤萬里”(空間)與眼相對,“時序百年”(時間)與心相對;“乾坤萬里”乃眼底之現象,“時序百年”乃心中之現象,眼識之外無乾坤萬里,意識之外無時序百年。蓋李較著重外界自然,杜較著重歷史文化。
句下之死,除了創造性的闡釋之外,還有一種死法,便是“死摳文字”。讀書是需要“死摳”的,不能用陶潛的“不求甚解”來搪塞,因為陶潛接下去又說:“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此會意處,便是摳文字處,只是陶潛不愿意做注疏的工作,遂令后人無緣分享其死摳文字之樂。
《莊子·人間世》引述孔子之語:“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盛也。”梁啟超便死在了這句話之下,《飲冰室論諸子集》詮釋道:“這個‘若’字極要注意。命的有無其不必深究,只是假定他是有的,拿來做自己養心的工具。”
這一個“若”字便是儒家與釋、道二家的區別所在,是儒家精神的精粹所在:“假定”有命以養心,而實際卻是繼續做事,不認命,不服輸,不甘心。
熊十力另一位弟子徐復觀,在其《中國人性論史》中釋《孟子》“今人乍見孺子將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云:“‘乍見’是心在特殊環境下,無意地擺脫了生理欲望的裹脅……此時的心,也是擺脫了欲望的裹脅而成為心的直接獨立的活動,這才真的是心自己的活動。”
“乍見”是必須要摳的,否則便不能理解孟子性善論的真諦。最后,也想舉出本師的一個例子,《論語·子罕第九》:“子貢曰:‘有美玉于斯,韞櫝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善賈者也。’”胡曉明先生《靈根與情種:先秦文學思想研究》釋云:“子貢的求善賈,與孔子的待善賈,一字之差,意義重大:‘求’有炫耀義、輕率義;而‘待’則是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不降志,不茍合。”
儒家主張的“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上不怨天,下不尤人”,“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等等,皆統攝于此一“待”字中。
闡釋是一件比較危險的精神活動,弄不好就變成附會穿鑿,深文周納。王夫之感嘆說:“一部《杜詩》,為劉會孟湮塞者十之五,為《千家注》沉埋者十之七,為謝疊山、虞伯生污蔑更無一字矣。”中國歷代的文字獄更是過度闡釋的結果,多少文人因之死在自己的句下!這時的“死在句下”已不復風流蘊藉,而淪為恐怖殘酷了。故闡釋應恪守其精神活動之純粹性,不能為政治斗爭所利用。
闡釋大致可分為兩類:我注六經與六經注我。前者固當以小心謹慎為宜,后者則自可灑脫快意,重情適性,當王國維書寫“三境界”之時,目中豈有晏殊、柳永、稼軒諸子在焉?
既不違于常理,復含妙趣于言外,于古人名句下做一風流快活之鬼,遠勝于塵世間庸庸碌碌之死百倍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