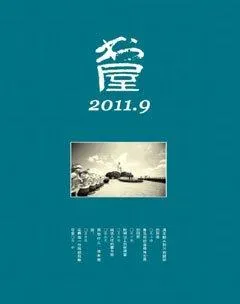“為白人的羞恥付出代價”
在美國南方一個白人家庭里長大的馬克·吐溫,曾有過作為白人的愧疚和持續增長的種族問題意識。為了回應奴隸制度遺留的種族歧視,他創作了《哈克貝利·費恩歷險記》。
小說通過哈克貝利與逃亡奴隸吉姆的友誼故事,詮釋了黑白兩個種族間的平等意識。小黑奴在這個白人男孩的生命旅途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記。哈克貝利下意識地觸摸到奴隸的價值,進而揭示出兩個種族的同等地位,而非人們固有觀念中的優劣關系。
在吐溫所處的那個時代,奴隸制被普遍接受。在學生時期,他并不覺得這個制度有什么不好。他在自傳中寫道:“當地的報紙沒有反對它,神職人員也說得到了上帝的許可。”用吐溫的話來說,那個社會,在他心里,也在故事中的哈克貝利心里,種下了“變形的良知”。幸運的是,故事中的倆人都有一顆“健全的心”,可以戰勝那良知變形的心。在他的另一部著作《赤道環游記》中,吐溫還提到當年目睹一個奴隸被活活殘殺的經過。在逐漸認清奴隸制的本質后,他獲得了最終的結論:奴隸制找不出任何存在的理由。
奴隸制盡管在美國內戰后就被廢除了,但由它帶來的種族歧視持續地禁錮著有色人種的生活和地位。各種文化都建立在偏見和不平等的基礎上,尤其是像密西西比河谷(吐溫成長和故事發生地)遺存在奴隸制之上的文化。比如說,有一種表演是由白人扮演黑人,模仿他們的言行來達到滑稽的效果。這些表演掩蓋并壓制了白人對黑人道德和人性的認識。羞恥、無知、木訥、順從,這些都是與人們心中典型的黑人形象有所關聯的詞匯。
吐溫筆下的吉姆就是按照這種典型來塑造的。在故事里,他得毫無尊嚴地接受湯姆·索亞對他的愚弄。吐溫在揭露這層“典型”面具的偽裝之中,展示了吉姆的人性。兒時的種種經歷增添了白人作家的內心愧疚,面對戰后重建中想為黑人在白人主流社會中找到位置的失敗,吐溫決意“為白人的羞恥付出代價”。正如他幫助一名黑人學生就學耶魯大學法學院一樣,撰寫《哈克貝利·費恩歷險記》也是他“付出代價”的一種方式。
最初的打算是將這本書寫成《湯姆·索亞歷險記》的續集。此書是一本深受兒童喜愛的書,現在的續集卻嚴肅深刻得多了。吐溫在寫給一位圖書館管理員的信里承認,《哈克貝利·費恩歷險記》是供成人閱讀的書。的確,雖然是好朋友,和湯姆不同,哈克貝利有他自己的思想。他的經歷更加充滿真實生活所帶來的危險,而湯姆卻更多的是出于自己天真的想象。帶著更加務實的態度,哈克貝利從現實中學習并建立人際關系,在現實上踐行道德標準。
盡管是白人,落魄的哈克貝利并非生活在主流社會里,而是生活在主流道德規范之外。他的局外人的位置,促使他同中心的道德語言相分離。故事里這個沒受過什么教育的男孩,話語里出現很多語法錯誤,就象征著他疏離主流社會。他的道德水平絕非成熟或文明——他甚至試圖振振有詞地為偷竊找借口。顯然,哈克貝利缺少恰當的理性思考,喜歡根據他與人的關系來自發地認定道德規范。例如,他從未為了其他人或事堅持立場或者做出行動,直到他與瑪麗·簡的關系和情感超過了他與兩個騙子,“公爵”與“國王”的關系,才最終決定幫助瑪麗·簡結束一場詐騙。
盡管吉姆是個逃亡奴隸,哈克貝利也對他一視同仁,只因他是好朋友之一。這就解釋了這個故事有爭議的結局。在結尾里,哈克貝利默認湯姆在救吉姆出來時戲謔他,把自己的快樂建立在別人的痛苦之上。這似乎與哈克貝利應做的以及故事想要表達的思想背道而馳。其實,對于哈克貝利來說,湯姆和吉姆同樣是最親密的朋友,不想為任何一方而忽略湯姆對娛樂的需求或者吉姆對自由的需求,他們之間不分等級先后。他本能地選擇沉默,與其說不想拿友誼來冒險,更加表明他自發地把湯姆和吉姆看成平等的個體。
哈克貝利另一次沉默的選擇也飽含深意。湯姆受槍傷,哈克貝利與正在逃跑的吉姆進退兩難,或者讓湯姆就醫延誤吉姆行程,或者保證吉姆自由但危及湯姆的生命。哈克貝利再一次選擇了沉默,但把決定權給了吉姆。“說出來,吉姆”。哈克貝利說。他想道,“我知道他內心是個白人,我也猜到他會說他說了的話……所以現在一切都沒事了,我也告訴湯姆我會去找醫生”。
這幾個事實說明,哈克貝利不老于世故,也沒有清晰的是非觀。他還沒有達到這樣的高境界,從一種文化特定的價值觀審視普遍的道德原則;他沒能從自己意識到“吉姆內心是白人”來得到概括性的“種族歧視是不對的”結論。事實上,他的無修飾的選擇與反射正體現了健全的人性——對種族平等本能的感知。我們在此可以窺見吐溫的傾向:如果人們沒有被社會觀念所束縛而隨著本能和靈感,就會不帶偏見的面對不同的種族。
在剛提到的場景中,吉姆的反應比哈克貝利的顯得更重要,因為它顯示了一個黑人的人性,這種白人社會企圖掩蓋的品質。吉姆對哈克貝利“說出來”的要求作出了回答:“要是不找醫生,我一布(步)也不走,即便要等四十年也行!”他不僅把湯姆的安全看得比自己的自由重要,還提到了四十年的期限。四十年,也就是吐溫寫作此書的時候,這象征著吉姆愿意將自己的奴隸生涯延長到漫長的歷史時刻,甚至他的余生。吉姆也相信湯姆也會為他做同樣的事情。這個數字是吐溫用來放大吉姆的道德而特意設計的。因為事實是,故事中任何一位白人都不愿意為黑人犧牲這么多。小說故事不僅揭示了吉姆有人性,而且作為一個黑人,有著超出種族的愛心和同情心。
他的人性在其他地方也有所體現。在一個濃霧把河上的吉姆和哈克貝利分開的場景中,重逢時他看到哈克貝利還活著喜極而泣;而哈克貝利卻惡作劇地告訴他一切都是他的想象,他們從來都沒有分開過。吉姆被觸怒了,說:“那邊一堆殘枝敗葉是垃圾;那些把臟東西往朋友的腦袋上道(倒),叫人家為他害少(臊)的人也是垃圾。”罵哈克貝利是垃圾,同時又澄清他們的友誼。哈克貝利明白了黑奴也是有感情并會受傷害。這是哈克貝利和讀者一同領悟到黑人人性的開始。后來,在故事里,哈克貝利還觀察到吉姆為他的家庭擔憂。“他坐在那里,腦袋垂到膝蓋中間,獨自唉聲嘆氣……情緒低沉,思家心切。”哈克貝利由此“相信他跟白種人一樣,愛憐他自己的人。這似乎不合乎自然,不過我看這是實情。”他也有愛心,所以他才有動力要把家人也從奴隸制里解放出來。當他回憶自己曾打過女兒,他滿心悔恨。哈克貝利最終得出結論:“吉姆真是個好心腸的黑奴。”這里揭示出作者的信念:沒有任何理由表明白種人高人一等。
當時的社會和人們的思想顯然不夠健全,用吐溫的話說,“人類被習慣和頑固的社會規范所束縛,并進入一個永久的、逃脫不了的自我毀滅的循環”。奴隸制度野蠻而又殘忍,但那個時代的社會卻不允許質疑。至少三名公開質疑奴隸制的漢尼拔(故事發生地)人被逐出城,并不是極端的例子。盡管如此,馬克·吐溫還是用他的筆寫下了他的懷疑和信念。通過一個記敘種族間交流和友誼的故事,他成功地在一個不平等的社會中證明了種族間、人類間的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