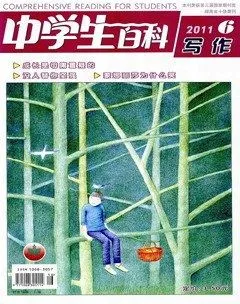抓住那只麻雀
我一直認為他是男性。其實我剛見到他的時候,曾經(jīng)隱晦地問過這個問題,他很爽快地說“喳喳”。我沒有聽懂,又問你在這里做什么,他歪著頭斜著眼說“唧唧”。這句話我懂了,他是說他從樹上掉下來了。我沒有往下問你為什么不飛回去,因為我看見了他的眼神。
另一個讓我肯定他性別的原因是他的沉默,站在草叢中的他毫無聲息,他的安靜讓我不能完全明白他的艱難處境。不過,如果只是他的安靜,我是絕不會碰見他的。碰見他的機緣大概還要歸功于他的姐姐,是她的一蹦一跳吸引了我。她的體形遠比一只成年的麻雀小得多,飛行的高度幾乎等于零,這讓我人類愚蠢的自信心迅速膨脹起來——抓住這只麻雀!
后來我才理解這位姐姐的用意她想把我從她的寶貝弟弟身邊引開,盡管對周圍亳不在意的人類完全沒有注意到她那在草叢中的寶貝弟弟,盡管這樣的行為反而導(dǎo)致了我注意到她的寶貝弟弟。因為她小小的腦袋不明白人類是沒有追逐一個目標太久的恒心的。于是當(dāng)我追倦了蹦跳靈活時而低飛的她時,回過頭,不經(jīng)意望向草叢,居然看見了他。
他安靜地混合在雜草中,眼神倒是很平靜,全然不像是一個從家中分離了出來且回不去的沒長全羽毛的小麻雀,倒像是一個因為輸了比賽和自己賭氣的十歲孩子。姐姐的幫助大概是根本不需要的,所以他歪著頭望著天。顯然,他已經(jīng)撲騰了好一陣子了,所以他倔犟的眼神里有著些委屈和受傷。
對于這樣毫無反抗能力的對象,人類向來是很有興致的。于是我很容易地抓住了他,問了他兩個問題——“你叫什么名字?”“你在這里做什么?”他相當(dāng)直接和坦誠地回答了,不過我只聽懂了一半。他站在我的手上也很安靜,倒是他那個剛學(xué)會飛的姐姐有些吵人,引得周圍的樹上也是一片喧嘩。當(dāng)然這些吵鬧我都沒有聽懂。
忍了一陣之后,我又開始問他打算怎么辦。他沒有開口,只是仍舊用硬硬的眼神斜盯著我,像是在說:要你管!看著我?guī)е絹碓竭h離他熟悉的草叢和樹蔭,他眼神里閃過一絲焦慮。更讓他焦躁的是他那個比母親還吵鬧的姐姐,這個半大還沒學(xué)會恐懼人類的動物一直在離我不遠的前方蹦跳,一邊還發(fā)出尖細的喊叫。她的這些努力,總算是讓她的弟弟有點意識到自己的處境了,同時也讓整個家族慌了神。
我看著麻雀家族的大亂子,我沒心沒肺地微笑,大概是人類強大的自負心在作祟吧。正是這一笑,他眼神中的焦躁沒有了,留下的都是孩子式的倔犟。然后他抬起尾巴,毫不客氣地在我的手中留下了一坨熱乎的稀屎。看見我痛苦的表情,他歪著眼,有些得意。
就這樣,他在我家窗外花盆中安頓了下來。我不是不想把他帶進房子,是因為他的姐姐實在太吵,我只好選擇把他們留在門外,而這似乎合乎他姐姐的意愿,或者是她最低的意愿。當(dāng)我開始逐漸對他失去興趣離開的時候,他的姐姐終于下定決心飛到他的身邊,緊緊地貼到他的身上。他似乎有些不習(xí)慣這樣的親密,拿喙啄在姐姐的翅膀上,姐姐的身體受了力向另一邊微傾,很快又彈了回來,仍舊靠在弟弟身上,似乎飛不回去的是她。這樣啄了幾回,他便乏了,只像姐姐貼著他一樣貼著姐姐。
我打開窗戶看他們,他們也懶得回頭,就算是我的手碰到他們,姐姐也毫不介意,并不躲開。就這樣,他那個煩人的姐姐也安靜下來了。不過這并不意味著鳥群平靜,總有那么三五只麻雀輪流站在我家窗臺二樓的護欄上商量計劃,然后盡可能的飛得低,靠近兩個幼小的孩子,并最終沖破那道本能的恐懼,把晚飯送到他們的嘴里。大鳥的小心謹慎,使得我只能靠著他們碩大尾羽的搖擺來看清那被玻璃擋住了的哺育被人類囚禁的孩子的感人一幕。直到夜幕完全降臨,所有的鳥都安靜下來,飛回巢睡去,只留他一個在我的窗臺下
第二天早晨,我把他們送回了他熟悉的草叢。中午回來,我找遍了所有的草叢也沒有找到他,然后我聽見一個嶄新的聲音,稚嫩卻滿是底氣。我抬手擋住從樹葉中擠出的耀眼的陽光,順著聲音,從光暈的環(huán)繞中看見一雙倔犟的眼睛,之后一坨熱氣騰騰的屎準確地落在我的腦門上。那雙眼睛露出一絲惡作劇的喜悅。我看見他飛向天空。
結(jié)尾二:我找遍了草叢,都沒找到他,也沒有見他飛向天空,我只是想象了他在陽光中飛走的樣子。我問過在院子草地上玩耍的孩子,他們的確曾經(jīng)把他戲弄了一番,但他們確實沒能把他從草地上趕走,孩子們回去吃中飯時他還在草地上望著天空。孩子還說臨走的時候看見一只肥碩的貓躡手躡腳走過,不過他們一再說,回家吃中飯的時候,他們確實看見那只小麻雀一直倔犟地望著天空……
編輯/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