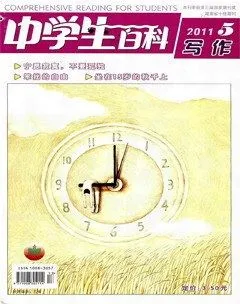像陽光一樣寂寞
在櫻庭鎮的十八年里總有那么些故事無法遺忘,而那些人至今已不知身在何方。也許我可以將他們寫下來,紀念那些已經逝去的歲月,那些萌動的青春與激情。
A
我的高中在櫻庭中學,一個不算大的示范中學。它對外號稱“創省重點的櫻庭中學”,進來后我才知道,那個“創”字代表這所學校正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爭取成為省重點”的狀態。我知道的時候已經沒有后悔的余地了,所以只能安心地在這所學校混下去。說“混”也不太準確,我沒有像個混混一樣閑來無事吸煙曠課打架,我只是不務正業——對于理科生來說,看課外書和寫小說絕對是不務正業,況且,我的大部分時間都花在這些事上面。所謂課外書,也并非女生熱衷的言情或其他男生喜歡的玄幻,而是很正常的文學作品。當然,對于這所學校,這是很不正常的,所以我的處境異常艱難。
我唯一的同盟者就是阿寂。我們在高一的第一次期末考試時認識。考試當天,我正為一篇難產的小說苦惱,所以胡亂地做了考卷,然后提前出了考場。
出去之后我依然苦惱,決定出校采風,卻又看到門衛異常兇猛的眼神,只好退而求其次去學校天臺吹風。天臺很安靜,只有兩個人,一個在練街舞,狀似抽風,另一個趴在圍欄上向外看,似乎是在看著外面的世界,想著未完的故事。
有人拍了下我的肩膀,我轉過身,看到一個陌生人。他一邊說這什么鬼題啊這么難,一邊隨著校外車子移動的方向轉動腦袋,然后說,這車也敢開這路,他不怕把底盤磨沒了啊iJruLi4bGXY2ZkLOUyTpPnSKQBN4g15qYVe2yPQ1L0I=?這于我很突兀,如果可以的話,我想把百度搜索軟件安裝在大腦里來想起此人,以避免現在的尷尬。他也注意到了,撓撓頭,尷尬地說,你好像還不認識我,我叫袁寂,叫我阿寂就行了。我看著這個叫“圓寂”的小子,以及那個頻頻往地上撞的家伙,突然很想笑。
B
上課時老師們總愛說,你們是高中生了,學習要靠自覺,自習課要知道自己該干什么。于是我在自習課上奮發圖強,爭取年內從魯迅看到余秋雨。后來知道那是不可能的。中國的文人多,拋開沒名氣的,著名作家就有幾火車:中國人又好以輩分來排次序,要做著名作家,就得寫到老,因此作品無數,而真正好的作品卻不多。問題在于,書的好壞要一本本看過去;結果是:之前的任務就成了大海撈針。
我撈了一學期,自我感覺頗豐,就開始寫稿子,然后投稿。稿子大部分都是泥牛入海。后來我知道阿寂是個詩人,這讓我驚詫無比。他說,其實也沒啥,就是看那特別美的散文,然后自行仿造,再把仿造品拆散了隨機組合就行了。我說,這樣都行啊?他說,那當然,很多人說我的詩好。我說,那倒也是,這說明你找到了詩的真諦。
有一次我看雜志居然看到阿寂的詩,內容就不轉述了,免得負文責。詩的后面有他的段話:我覺得寫詩就是要認真,要把自己真正融進詩里,讓詩成為自己更真實的面,至于那些不懂詩的人,就讓他們不懂好了,好的詩是不需要人懂的。
我覺得“是不需要人懂的”太寫實了,因為如果有人看懂了,那這個詩人就混不下去了。所幸沒有人能看得懂,包括詩人自己。那些吵著“好詩好詩”的人估計就是因為沒看明白才叫好:如果明白了,就像知道大名鼎鼎的蘆薈或龍舌蘭就是油蔥樣,沒有美感了。
為這個事我沒少嘲笑他,不過他說,就是鬧著玩玩而已,好歹我也進行了深加工啊,比那些直接搬別人的書說是自己作品的人強多了吧。我說,那也是。不過還有更次的,就是自己寫了東西,說是名家的,拿到書市去渾水摸魚,具體情況你逛一下書店就可以了。
C
高一下學期開始的時候天出奇的冷。我搬出了寢室,和阿寂一起租了房子。除了他寫詩這事外,他是個挺不錯的人,尤其是需要掏錢的時候比較豪放。至于他寫的那些詩,我沒資格說他,我畢竟只是個發表過一些豆腐塊的、俗稱“豆腐干文人”的外圍人士,而他好歹還小有名氣,雖然手法比較低劣。倘若我看不起他,就有些像五十步笑百步。不過話說回來,這中間還差著五十步,那是我的底線。寫詩可以投機取巧,是因為寫詩的人大多數都在投機取巧,但寫文章不行,太容易暴露了。
當初想著住校沒什么,后來發現這是個極不明智的決定。所以當阿寂提出合租房子時,我毫不猶豫地答應了。另一個讓我毫不猶豫的原因是,他提出承擔三分之二的房租。
搬東西的當天,我發現自己上了這小子的當。他出三分之二的房租是沒錯,可其中一半的錢是另一個租客出的。在我和那人溝通后,我知道阿寂對他也是這么說的。我暗自感嘆這家伙真是不簡單,城府估計都扎根馬里亞那海溝了。另一個租客暫且叫他“學者”吧,他的名字太大眾了,說出來我怕引起公憤。
基本上我們能看到他的時間里他都在看書,那是相當正規的教科書。他架了一副高度數的眼鏡。阿寂曾經試圖通過親自實踐來搞清楚具體度數,沒成功的原因是他剛戴上就莫名其妙地從床上滾下去了。“學者”震驚我們的另一大特點是他的呼嚕聲。他的呼嚕聲能與海浪聲比分貝,搞得我感覺住在海邊。而且他不睡則已,只要倒在床上,立馬打呼嚕,這很討厭。以前我總是在夢里看草原,后來就只能夢到大海了。看海的心情和在大海上漂泊的心情是截然不同的。
我想反正也就那么回事,也沒怎么計較。其實這和住寢室差別沒多大。阿寂搞了個電飯煲,下晚自習后就在鍋里煮大雜燴,什么玩意兒他都敢往里扔,讓人意外的是煮出來的東西味道都還不錯。這導致我和“學者”經常趁他上廁所的空當把鍋里的東西掃蕩干凈。他發現后氣得跺腳,然后又往鍋里扔東西。我們懷疑他是東北人,因為聽說東北人擅長這個。
此外,我搞了些瓶瓶罐罐和花草種子,一個多月后把房子搞出了生氣或者說妖氣。“學者”從家里拿了吉他來,我們以為這家伙是高手,經他的手在弦上一點撥,我們就明白了,他和吉他生生世世都沒可能的。然后我們禁止他碰吉他。不過,我們常常會趁他不在的時候拿來弄一會兒,收獲是周圍鄰居的伴奏:“誰家在裝修啊?小聲點也不會死吧!”
D
高一下學期的第一次月考后我突然很想轉去讀文科,沒有什么正式的理由,屬于腦子一時“燒”了,第二天就“燒”進了文科班。晚上回租房,阿寂看到我,說,你小子腦子有毛病是吧?學得好好的怎么說溜就溜,溜也不打個招呼,好歹我還能給你參謀參謀吧?
我說,你就當我有病吧,我自己也不清楚。
我躺下后竟然沒有聽到熟悉的“海浪”聲,一時不習慣,折騰著爬起來。我問阿寂,怎么沒看到“學者”,他去哪兒了阿寂說,參加個什么競賽了,說是拿了獎就能保送個什么大學,具體的我也不清楚。我說,那我怎么辦啊!沒有他的呼嚕聲我還真睡不著,恨當初沒有給他錄下來以備不時之需。阿寂轉身提起了吉他,我一看他這架勢立馬沖過去把吉他搶了下來,跟他說,你想死也別拉我陪葬,白天拉都像挖了別人祖墳似的,這半夜三更的你不怕別人扔倆手雷過來啊?
轉到文科班后的生活依舊無聊,投出去的稿子像扔在沙漠上的種子,天知道地球發生多大的變化才有機會萌芽。阿寂的詩倒是持續不斷地發表,我每次看到他的詩就會猜原材料是誰的文章,竟能夠猜得八九不離十。這讓我更加相信現在的文學只是表面的景氣。
有一天阿寂說,你可以把詩又整回散文嘛,這叫回歸自然。我說,算了吧,那不是自投羅網嗎?況且我現在還沒混出名,這么早把名聲毀了多不劃算。
然后阿寂說,我以前也挺熱愛文學的,后來我知道文學不愛我,這沒辦法,我只好愛稿費。熱愛文學的人要么移情別戀要么悲壯殉情,真正幸運的沒幾個。
我不置可否。其實我不是熱愛文學,只是有傾訴欲望而已,無奈編輯們大多不喜歡聽我喋喋不休。我很無奈,我覺得寫作是個人的事,可編輯們回信說你應該寫寫光明面歌頌一下嘛。我只好說,不好意思我另投高明吧。可我至今沒有投到高明。
E
日子過得像流水,這是阿寂說的。我說日子過得像流水賬。我在文科班混得很勉強,估計勉強上個二本,所以我決定繼續讀下去,畢竟現在也沒事干。阿寂說他畢業后絕對不寫詩了,受不了文友們的酸話。最沒疑問的是“學者”,他已經拿到了保送名額,現在在學校裝個樣子,時間一到就去南方某個溫暖的城市。
我開始為以后的路擔心。人就是這樣,在時間充裕的時候不會擔心以后,能居安思危的只是極少數的人。高中的前兩年大家都肆意揮霍時間,想著反正以后時間還長,可這高三冷不丁就要結束了,于是不得不想條退路。我想如果考個二本就去讀,再混個三四年,然后混個工作再去混日子;考不上就去打工。總能有條路吧。
阿寂說我沒有追求,怎么就沒想過當個作家,寫字養活自己。我說,你以為我不想啊,可那是天路不是退路。更何況我現在只是個路人甲,只在些雜志上跑過龍套。不過就算有一天成了作家,還是小有名氣的,我也不能把寫作當作職業,我怕把激情耗空,再也寫不出像樣的東西。
高考前兩個月,阿寂在雜志上寫了絕筆——不,封筆之作,據他說這首詩真是自己原創的,算是報答文學的,兼和稿費分手。阿寂此后勤奮了不少,后來那本雜志還專門給他做了期告別專題,還說“我們不會將你遺忘,你永遠在我們心里”,看得我快要含笑九泉。
考試前幾天,我和阿寂約定一起去云南旅游,算是對青春的告別。這個時候“學者”已經消失了,不知道是不是已經去參觀他的大學了。他走的時候把吉他留下了,說想他了就撥弄兩下。
考試的時候我所在的考場暈倒了個,另外沒什么可說的。以前總是聽別人說高考有多恐怖,考完后我發現真正恐怖的是不知道考完后還能做什么,好像這輩子就剩個高考似的。
考完后我在學校發了很久的呆,回到租房,阿寂的行李已經搬走了。他留了張字條:本來想等你回來跟你告別的,現在沒時間了。小子你要給我活得好好的啊,要是哪天再碰到你一定試試你的抗擊打能力。我也不知道要去哪里,先胡亂走走吧。還有,那把吉他留給你獨享了,要是真不想活了就拉著玩玩兒。
我自言自語,阿寂你個笨蛋,吉他是拉的嗎?
F
我去云南旅游了一趟,一個人。行李之類的被我留在了租房里,房東說九月份之前必須搬出去。路上我想了很多,其實青春就這么樣,有的人能活得光芒萬丈,有的人始終是灰灰暗暗的。但這些其實也不是很重要了,以后的路長得無法估計,誰知道能不能一路開心地走下去。反正擁有過就好了,起碼已經夠本了。
這一趟我走了很多不是旅游區的地方,一個人背著背包,走在別人的大街小巷。在一個不知道是哪兒的街頭,我碰到一個彈吉他的年輕人。他彈得很起勁,然后弦斷了,他停下來嘆口氣,收拾東西準備離開。我攔住了他,遞給他紙和筆,讓他把地址寫下來。他疑惑著寫了。
第二天我走到了玉龍雪山下,準備了些東西,然后往上爬。由于上山時已是傍晚,就在半山的旅館住了一夜。半夜睡不著,又爬起來翻書。凌晨時我退了房,背上東西借著微光繼續走,走了一會兒停下來準備看日出。
山上的空氣還不算稀薄,可是冷,尤其是周圍很遠都看不到人的時候。一會兒,太陽慢慢從地平線上扎出來,有些刺眼。我掏出手機打算告訴誰我現在在玉龍雪山看日出。手機顯示沒有信號。
從云南回來,打開租房的瞬間,我錯覺自己打開了被封閉很久的時間,就想這房間里的時間一直停留在我離開的時刻。這種感覺令人莫名其妙地感到有些悲傷。我把“學者”的吉他寄給了在云南碰見的那個樂手。那些已經快枯死的花花草草被我一一搬到了外面,任其自生自滅。
現在我在北方的一所大學,寫著無法出口只好內銷的小說。有些事情早已結束,可另外一些才剛剛開始,一如每日清晨升起的寒冷的寂日。
編輯/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