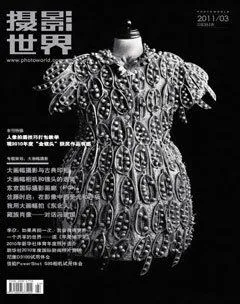一個攝影愛好者的大畫幅情結
2011-12-29 00:00:00喬小兵
攝影世界 2011年3期





我是一名地道的業余攝影愛好者。我的攝影經歷與許多影友相同,也是從“照相機愛好者”開始。最早的“攝影”是用父親的佐爾基相機拍照后,用飯碗沖洗膠片,再用紅領巾包上電燈泡做暗房燈開始的。改革開放后,從美能達X-700、尼康FM-2、FA、F-3,佳能的AE-1、A-1、新F-1到瑪米亞RB67等等,都是我的珍愛。而后來我又被大畫幅相機所吸引的主要原因,也是它那一眼可以看到底的精密之美。
雖然我開始學習安塞爾·亞當斯的攝影技法是上個世紀80年代的事情,但真正擁有自己的第一臺大畫幅相機,還是在大約10年前。那是一臺騎士的FA雙軌4×5相機。盡管有一段時間我更鐘愛8×10相機,不過后者的分量之重,迫使我又回到了4×5。
我還清楚地記得第一次用大畫幅相機拍攝,是在西部長城腳下。一大早用了兩個多小時,只拍了一張膠片。回京后當看到自己用大畫幅相機拍的照片小樣印出來時,第一感覺就是“相見恨晚”。看到畫面中伸向遠方的大峽谷,從自己腳下到畫面盡頭都是那么清晰時,才真正明白這是135、120相機所不容易做到的。
認真搞攝影20多年來,拍得多了,想得也就多了。慢慢地我也從“照相機愛好者”變成了攝影愛好者了。前些日子和《攝影世界》主編李根興談起大畫幅攝影時,才讓我覺得是不是應當細細想想大畫幅攝影和自己到底是怎樣的關系。
在數字攝影已經成為了絕對主流的今天,重新審視大畫幅攝影的確會有不少新的體會。
大畫幅攝影的最大魅力還是“大”。如果想得到精美的畫面,恐怕大畫幅相機拍攝在今天仍為首選。這一點,杉本博司和邁克·肯納就是最典型的例子。無論后期制作是傳統的暗房放大、數字負片直印還是數字打印輸出,膠片尺寸與畫面的精細效果總是成正比的。
我也經常被影友們問到,數字相機接片拍攝是不是可以取代大畫幅膠片。我的回答是肯定的。只要后期不拘于用傳統放大工藝制作圖片,而可以考慮數字負片直印或數字打印的話,單從畫質方面判斷,數字相機接片拍攝已經完全可以取代大畫幅膠片了。但是,另有一個“隱情”是不可忽視的,那就是用大畫幅相機拍攝時特有的感覺。
用大畫幅相機拍攝的感覺,也可以說是一種攝影習慣,是必須在大畫幅相機上養成的。除了沙姆定律、移動光軸和調整變形等技術的運用外,對景物透視關系的理解和對整個畫面的掌控能力,是在小型相機上不太容易練就的。從另一個角度說,畢竟攝影是從大畫幅相機上發展過來的。如果自己想體驗一下攝影老前輩們的拍攝感覺,恐怕還是離不開大畫幅相機。
前幾天,一家雜志的編輯問我現主要用什么相機拍攝。我回答道:“日常主要是用數字相機,而只有必要時,才會用大畫幅相機拍攝膠片。”我的回答引起了他的極大興趣,他追問:“你認為什么情況下有必要用大畫幅相機呢?”我坦白地告訴他:“現在只有給我自己的家人拍照時,我才會用大畫幅相機。”
給自己家人拍照,是為了留住一個“念想”。用大畫幅相機認真地拍,通過自己最大努力留下來的畫面,我認為是最具“紀念”意義的。而在日常的攝影活動中,前期利用數字相機拍攝、中期數字化調整并制作數字負片、后期選用銀鹽、藍曬或鉑金等方式制作的圖片,已經完全可以滿足我個人和國際藝術品市場的要求了。
實話實說,大畫幅攝影在今天對我來說已經成為了一種“純粹的情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