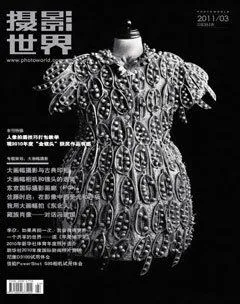攝影人要先從藍領干起
無論是什么樣的新聞稿件,都應該以“內容為王,落地才是硬道理”為檢驗標準。“三貼近”也好“精準快”也罷,說來說去都是為這一目標服務的。無論是文字消息,還是圖片報道,只有在新聞內容上搶占先機,生動鮮活,精致深入,感人有趣,采用率才能提高。尤其是當代的新聞攝影記者,在巨變的現實面前,想在業內站住腳需要付出更多的辛勤與汗水,承受更多磨練與險境的考驗,否則,就只能蒙上好照片,造不出好照片。面對新聞記者,特別是攝影記者生存與生產環境的復雜化和危險化,從業者必須具備先當藍領甚至是“黑領”的心理準備。
作為新聞作品的生產者,無論是攝影的,還是寫文字的,30年前都算是文化人,至今大街上隨便問個人都不會擅自將文化人納入藍領行列,以至于有些文化人自覺高人一等,心里特美。其實現在許多所謂白領是身輕心累,舉步維艱,他們仍慣于在公眾面前昂著高貴的頭,好像與藍領工作天生無緣,但實際上體力的付出和精神上的壓力日甚。比藍領還倒霉的是,他們還有口難開,特要面子。搞文字的這里不提了,如今從事攝影或其他視覺藝術的專業人士,起步階段就是個藍領工作,講好聽點兒充其量也就是個高級藍領。心高氣盛、自尊心特強的攝影人即便不這么認為,至少也應該有這個心理準備。如今各色各樣的攝影人,不論拍新聞的,拍商業風光的;不論專業的,還是高發(高級發燒友)的;狗仔隊就更甭提了,要想拍好照片,首先是體力上的付出,還要承擔一定的風險,尤其是戰地和災難攝影。新華社歷史上就有許多在采訪過程中獻出自己生命的攝影記者,他們的勇敢和艱辛與戰場上的戰士無異。說現代攝影記者的活是帶傷(病)、超時、負重、高碳這八個字不過分,當今吃攝影記者這碗飯的不把這八個字都用足了,拍出好照片的概率極低。
遠了不說,30年前,人們大街上見到一個肩背相機的人(那時相機金貴,普通人舍不得露在外面招土)都會投去羨慕的眼光;而現在,一看到拿相機的就躲,生拍被“曝光”或侵犯隱私權;有時候,攝影記者為了搶張好新聞照片,挨打受罵被砸相機的事時有發生。簡而言之,這就是攝影記者所面臨的職業生態環境,真的很“藍”,夸張說帶“黑”也不過分。
就視覺藝術而言,攝影之前還有雕塑和繪畫。攝影借助現代化工具可以多快好省(指的是一般攝影),繪畫雕塑卻不行;攝影可以碰運氣,繪畫雕塑更不行;攝影工具的不斷進步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攝影人原創和艱辛的不足,但繪畫雕塑從將近兩萬年前的巖洞壁畫至今,所用工具和基本技法都沒有發生本質變化。無論從那個角度,這兩種技能都要比攝影更難、更吃力,能給千百萬人帶來精神享受,但最初把它們帶到世上來的人,許多是地位卑微,窮困潦倒。搞音樂的也強不到哪兒去,莫扎特和史提芬·福斯特(后者為名曲《美麗的夢中人》作者)死的時候兜里都不超過一塊錢。雕塑方面最典型的就是文藝復興時期的藝術大師米開朗琪羅。米開朗基羅于1475年3月6日出生在佛羅倫薩附近的卡普勒斯鎮,母親早喪,父親是鎮長之類的小官,倒算是個白領。米開朗琪羅8歲時就被托給一個石匠的妻子撫養,受到啟蒙,立志長大搞繪畫,后來又想當個雕刻師。他父親對此極不贊成,認為雕刻師等同于石匠,是藍領工作,最沒出息,還不如個烤面包的:一身面粉,總比一身碎石頭渣子強。事實好像也果真如此,有這么一個真實的故事流傳至今:當米開朗琪羅他的著名石雕作品《大衛》在佛羅倫薩市中心廣場剛豎立起來的時候,市長大人過來參觀,指出雕像的鼻子有些問題,米開朗琪羅二話沒說當即叫人找來梯子登上4米高的雕像,一通猛鑿,只見石頭渣紛紛落下,之后他閃開讓市長大人再看,大人深表滿意。其實米開朗琪羅只是將兜里預先準備的石頭碎渣借機灑下,于是蒙混過關。米開朗琪羅一輩子與鑿子畫筆打交道,身上不是粉末就是油彩,終身未娶,卒于畫室,一直干的是準藍領工作。死后多少年他才被人們公認為世界頂級藝術大師,文化巨匠——中文里這最后一個“匠”字,其實就包含有動手工人的意思。所以要想在藝術領域有所成就,不艱苦勞動、不支出一定的體力,都是不現實的,尤其是當下。
根據攝影的職業特點,先要甘當藍領是不可或缺的一步,如今坐在大班臺后面有資格指揮攝影的人,當年大多是干藍領起家的業內佼佼者。不是所有經歷過戰爭的士兵都能當上軍官,必須是苦干愛學再加智慧,才能有資格指揮別人,從古到今歷來如此。有的藍領一直干到退休,領子也沒變白,就是這個道理。初入道的攝影記者只要用心用力去拍總會有收獲。如果你從來不把攝影當回事兒,只想坐在屋子里當小白領,不經辛苦就想成為大師,幾乎是不可能的。攝影這東西之所以被一些人認為“好玩”,就因為它相對容易掌握,而繪畫、雕塑一來出作品慢,二來更累、更艱辛。難怪做繪畫雕塑的物質條件比攝影低得多,卻沒見更多的人去從事。
攝影師過去“快門一響,黃金萬兩”的時代已一去不返,取而代之的是比以往加倍的努力和更多的汗水,此外沒有捷徑可言。表面上看好像攝影比以前更容易了,其實不然,正因為現在是個人就會照相,所以要想區別于你的級別到底是會照相還是會攝影,就更具難度了。再說許多事情會干與干得好乃天壤之別。不能吃苦,又缺乏學習和鉆研的精神,一輩子也別想“從藍轉白”,這和文化程度高低沒有必然聯系,短視的人做事才最講“大躍進”般的立竿見影。巴黎圣母院蓋了160年,科隆大教堂是600年,所以在地面上才能呆得長。后來興起大干快上,比學趕幫超,誰還等得及?現如今天上掉餡兒餅都不行了,最好掉下一塊金隕石,只要不砸死,立即成為大富翁,那才過癮。寧肯在床上過寄生蟲般的生活,也不愿在現實生活中吃苦受累,一個人的墮落就由此開始。
一個生活在現代環境中的攝影記者,除了要在善于運用日趨成熟的現代攝影和網絡技術,還應該有吃苦受累,干藍領工作的思想準備和體力支出;好的記者,不論是寫稿子的還是搞攝影的,想掙大錢的沒有,想出人頭地的沒有,想只在屋里指手畫腳、不在世上經風雨見世面的沒有。簡而言之,時代將賦予攝影記者新的職業定位,想“玩著干”的人今后不好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