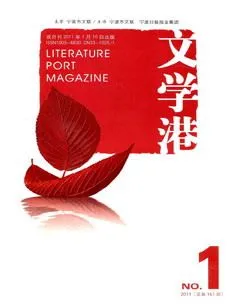敘述者孤獨的聲音
對我們這些生活在底層的人來說,角色的改變是幸運的,也是可怕的。生活,給我們帶來了過多的茫然與困頓。我們時不時地在天南用手機撥到地北,然后不斷擴散信息,然后聚在一起,以慶祝我們共同的節日,以懷念昨日茫然的時光。我們打開酒瓶子,整碗整碗地喝著酒;打開話匣子,一件一件談著昨日細小的事。一直喝到恍恍惚惚,還是不肯離去。整個過程,就像詩歌,從向外到向內聲音的延伸、穿透,在我們生命中,捍衛著一種品質,彌補我們精神的缺失。
低著頭走路、低著頭做事,低著頭寫一些文字。一年又一年,我一直生活在我的文字世界里,并樂此不疲地演繹著。從一所鄉村學校,到一個機關單位。從一個機關單位,到另一個機關單位。不斷地盤旋著。身份確定了,根扎下來了。從手執教鞭用一張嘴在學生之間講破嗓子,到用十個手指頭在鍵盤上杜撰著大量的公文。就像我的寫作,一直肯定著自己的敘述方式,并進行不斷地重復,不斷地加強與凝固。
每次乘著汽車回到老家時,我總是朝著車窗外,很專注地注視著我所熱愛的一切——每一個勞作的背影、每一滴咸澀的汗水、每一個豐收的笑臉和每一片茁壯生長的莊稼。熟悉的勞動場景與逐漸陌生化的鄉親面孔,就像一條打結的繩子,不斷鞭打著我的心口。我說不出一位農民的兒子,一位老家的過客,離開泥土、離開農作物后,其中的孤獨滋味。我就像一顆微塵在飄浮,老家只能拉出一段時光的余暉——不論過去是酸楚的,還是溫暖的感覺。那種情景不是兩雙對視的瞳孔所能映照出的。
我的聲音極其低下。就像我的沉默,詩歌對我而言,只是一種向內的聲音,一種對生命的虔誠聲音。肉體與心靈的感受是不同的,劇烈的內心沖突只有在詞語與詞語之間,才能找到自愈的帖子。一位真正的詩人,現實中的任何物體,在他的眼里都是異乎尋常地揪心。生活見證詩人。卑微的,向下的,瑣碎的,詩人用她來捍衛詩歌品質。
敘述者的聲音,是孤獨的。甚至,敘述者也是孤獨的,在發聲之前或之后,都是孤獨的。一個敘述者,如何在自己的敘述空間里,發出另類的聲音,另類愛的呼號,這是敘述者常會遇到的問題。很多寫作者其實是被自己的內心所擠壓,而非工作。詩歌是屬于內心需要的那種聲音,只要內心是強大的,聲音就不會消失。在這中間,我學會與自己說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