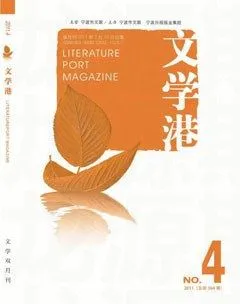謁王充墓
一個風和日麗的上午,我獨自走進了位于浙江省上虞市章鎮鎮內的“上虞茶場”,前去拜謁王充墓。
被偌大的茶園,一片綠油油的茶海所包圍,王充的墓多少顯得有些孤寂,有些突兀。然而,每一個清晨,當太陽緩緩躍出地平線的一剎那,你能不聯想到,這圓頂的王充墓不就是千百年來人們心目中那輪冉冉升起的“太陽”嗎?
走近王充的墓,那不足幾十平方的占地,那滿地蓬蒿的墳塋,也多少讓人覺得簡陋了些,或者說顯得有些許寒磣。想起歷史上無數統治者,都希望身后被供奉在高堂大殿,享受蕓蕓眾生的歌功頌德,享受子孫萬代的頂禮膜拜。他們幾乎毫無例外地預見到謝世之際的哀榮,包括葬禮之盛、陵墓之華。王充不是統治者,更何況他的叛逆行為也不允許他享受這種榮華。事實上,他也絕沒有這樣的奢望,作為一個堅定的唯物主義思想家和偉大的無神論者,他只要家鄉的一抔黃土,一座契合他淳樸風格的墓寢就夠滿足的了。
微風過處,綠波粼粼。剎那間,我的思緒隨波逐流而穿越時空。要確切還原王充的全部,似乎已經難有可能,然而,歷史的雪泥鴻爪到底讓我們能夠真切地觸摸和感受王充那永遠活著的不朽的靈魂。
公元27年,也就是東漢建武三年,王充出生在上虞章鎮林岙村的一個農民家庭。天資聰穎的王充,6歲讀書,就識9000字。要知道,那時候識3000字,《論語》、《尚書》都可以讀下來了。識得9000字的功夫,自讓王充涉獵書林如虎添翼。也正是從少年始,王充身上便滋生出一種氣象。氣象之于人何等重要!一個有氣象的人,必定有信仰、有追求、有原則,抗俗而不為俗遷,游乎廣博天地間。
由于他學業優秀和孝聞鄉里,于是便成全了青年時期的王充一段赴京城洛陽讀太學,又師從班彪的求學經歷。然而,也恰恰是這一段游學生活,讓他有了“博通眾流百家之言而不拘一家之說”的學識和胸懷。可不是?王充一方面是博覽群書,一方面則對當時處于統治地位的經典學說和普遍認識,都以“考論虛實”的態度,獨自研討,決不盲從。而這便意味著王充對有些已然的命題,哪怕是皇帝老子的圣旨,他也照樣手持真理之劍,一一予以戳穿。
有人說,我們在考察古代文人的品格時,自不能專門注意于個人因素,同時亦要顧及他們的生存條件。因為在古代封建社會里,文人根本就沒有自己獨立的社會地位。“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無論是文人或武人,都不過是帝王的家奴而已。他們的最終目的,是為帝王服務。討好帝王及其權臣,是勢所必然之事。有時,所謂忠直之臣,犯顏諍諫,也只不過是為主子好,恨只恨其不爭氣而已。從這個意義上說,王充張揚個性,追求獨立人格,尤其是宣揚“異端邪說”,當是一個異數。魯迅先生曾經說過:“中國一向就少有失敗的英雄,少有韌性的反抗,少有敢單身鏖戰的武人……”王充是不是那少得可憐中的一個呢?要知道,王充的叛逆行為,幾乎是孤身一人的戰斗。
“天能譴告人君,則亦能故命圣君,擇才若堯舜,受以王命,委以王事,勿復與知。今則不然,生庸庸之君,失道廢德,隨譴告之,何天下之憚勞也!”社會政治不好,天就會使自然界發生災異現象以譴告人君,對于這一統治者利用“譴告說”欺騙百姓的做法,王充自給予了“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痛擊。一些儒者,總以為圣人前知千歲,后知萬世,然而,王充以為“如無聞見,則無所狀”,“知物由學,學之乃知,不問不識”,“不學自知,不問自曉,古今行事,未之有也”。王充對唯心主義先驗論,給予了無情的抨擊。“人之所以生者,精氣也,死而精氣滅,能為精氣者,血脈也,人死血脈竭,竭而精氣滅,滅而形體朽,朽而成灰土,何用為鬼?”“天地開辟,人皇以來,隨壽而死。若中年夭亡,以億萬數。計今人之數不若死者多,如人死輒為鬼,則道路上,一步一鬼也。人且死見鬼,宜見數百千萬,滿堂盈庭,填塞巷陌,不宜徒見一兩人也。”對于鬼論的批判,王充自是有板有眼、一針見血。“如實論之,卜筮不問天地,蓍龜未必神靈。”俗人篤信卜筮,王充怎會相信?“天不言,則亦不聽人之言。天道稱自然無為,今人問天地,天地報應,是自然之有以應人也。”王充鑿鑿之言,自將卜筮駁得體無完膚。
王充的才氣,確乎“非學所加,前世孟軻、孫卿,近世揚雄、劉白、司馬遷,不能過也。”按理說,恃才的王充自可一展抱負。然而,對于一個家貧而又不能與時茍合的王充,在短暫擔任郡功曹、揚州治中等職期間,因政見不合,其后當然只能將一去了之作為唯一的選項,這莫不讓人愴然于懷!其同中國千萬文人知識分子一樣,一生風雨波濤中為國家為社會嘔心瀝血作出自己杰出貢獻的同時,也與多災多難的民族同命運,特殊時世幾乎都難以逃脫坎坷顛躓的遭遇。“處尊居顯,未必賢”,“位卑在下,未必愚”,這既暗合了王充孤傲耿直的秉性,也昭示著王充從此將告別官場返歸鄉里。
60歲那年,王充從洛陽徑自徒步回到了生于斯養于斯的故鄉——林岙村。可以想象,在經歷了仕途坎坷、世態炎涼、學術虛妄之后的王充,又怎按捺得住憤世嫉俗之心呢?回到故鄉的他,絕不會憑顯赫的聲名去私塾教書要一份安穩的工資,更不會去享受悠然閑適的鄉紳生活。他“閉門潛思,考論虛實,絕慶吊之禮,置乃筆于墻垣戶牖”,繼續完成他思想的結晶——《論衡》。
《論衡》,斷斷續續地至少花了王充30多年的時間,且最后竟在故鄉擱筆完成,這似乎是冥冥之中的定數。故鄉,對于王充實在是太偉大、太溫馨了。偉大得可以給一個別處別人難以容納的游子提供精神的庇護;溫馨得可以讓一個傷痕累累的游子在母親的懷抱靜靜療傷。于是,只要心不苦,王充自可以承受繩床瓦灶、布衣荊食的清苦生活。畢竟,他可以在故鄉的“港灣”,盡情地完成他思想的吞吐和飛升。是啊,當王充在青燈黃卷下,讓那些目光如炬的文字、睿智似泉的思想汩汩流淌、奔騰直瀉的時候,其就像一道道橫空的霹靂,也正是讓有的人靈魂瑟瑟發抖的時候。盡管被統治者誣為“異端邪說”,抑或為俗人譏諷不容,王充對其只是“像蛛絲一樣輕輕抹去”,因為他不屑。他依然故我,特立獨行,他始終相信真理之舟尚在暗河里行駛,一旦駛往海洋,必見曙光。
英國著名科學史家李約瑟說:“公元一世紀,像王充那樣極為強烈地提倡科學自然主義世界觀,即使在歐洲也要來得晚得多。從科學思想史的角度看,王充是他那個時代最偉大的人物之一。”林岙村,一個地圖上找不到任何標記之地,從此走向全國,走向世界,只是因為王充,因為王充的精神及其《論衡》。
正要離開王充墓,一位王充的同鄉領著一群家鄉人前來掃墓。他告訴我,這只是王充的衣冠冢。其實,墳塋內葬的究竟是遺體還是衣冠,這并不重要,這都是留給后人祭奠與緬懷的儀征和表象,真正令人景仰的并不是王充埋在地下的枯骨或衣冠,而是他留給世人的不朽文化遺產,是那顆平凡的頭顱升華而出的高貴靈魂。山川無言,滿園嘉木無言,最經久的綠蔭、最不朽的意志以及最輝煌的榮耀,往往就會蘊于無言。王充,就這樣長眠在茶園中間,長眠在鄉人和民眾的心坎。
責編 李全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