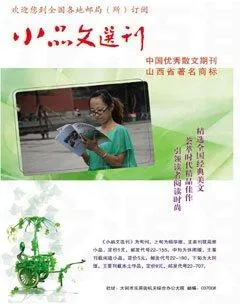暗香如故
北宋的林君復為梅所動,一生未娶,以“梅妻鶴子”自詡;他的“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14個字清絕出世,艷絕古今。詠梅的,無人出其上。王十朋更贊道:“暗香和月入佳句,壓盡千古無詩才。”
卻有一個女子,愛梅不在林逋之下,清絕也不在他之下。出身在福建的莆田,入大明宮后,在宮前遍植梅花,建賞梅亭,作梅花賦,愛得癡絕,她的男人稱她為“梅妃”、“梅精”。也曾三千寵愛在一身,也曾在宮宴上舞做凌波,有人乘醉踩了她的繡鞋,便惱了,拂袖而去。
清冷疏淡的人兒,連皇帝的面子也不給,像這梅,春風一到,萬花獻媚的時候,她不理,冬風蕭瑟,驀然回首,她或許在墻角候君多時了。
她整個人,正是白梅如雪,不染塵埃。可惜清幽的梅,似乎從根本上不屬于繁盛的大明宮,她是被命運帶進來的旁觀冷眼人。楊玉環進宮她漸漸失寵,遷居上陽宮。沉香亭的梅花改成了牡丹,作《樓東賦》改變不了愛情偏離的軌跡。他惻然了一下,惻然而已!愛情是霸道的,獨一無二的愛。他不能,也沒有能力同時愛著兩個女人,只能送去一斛珍珠。
君王也一樣,一樣遭遇了愛情。面對真正的愛情,不能夠三心二意。
可惜他不知道豐裕的物質溫暖不了被愛情遺忘的心。滿足不了這個孤獨清高的女人,她說,長門自是無梳洗,何必珍珠慰寂寥!意思也是明確,要么就是你的人來,清心寡欲的來,哪怕只是來見我一面。我也承恩不忘,而一斛珠,我是不稀罕的。
一個失寵的妃子能絕然地將皇帝御賜的禮品退回去,并問一句,何必珍珠慰寂寥!該是多么清潔自詡自尊自重的人,我總覺得林君復筆下暗香疏影、冷花淡萼的梅仙便像是梅妃江采萍。她幽謐柔弱的外表下隱藏了一顆寧折不彎的心。可惜太出塵離俗便更不為世所容,怎經得住人事變化?“安史之亂”中,她成了戰火里的一樹枯梅,將清冷疏瘦的影子留在溫泉池里,等著這個宮殿的主人回來。
多年后,當李隆基在梅樹下挖出梅妃的遺骨時,已然垂垂老矣的太上皇淚濕長衫涕淚橫流,將滿園子的梅花撒在她的身上。
他回望前生舊事,夜涼如水,長生殿上依舊燈火通明,暗香浮動間,依稀是她在梅林中笑語翩遷。楊妃仙去,梅妃也化成了墻角數枝梅。所愛的兩個女人都找到了生命的歸宿。當真是一抔凈土掩風流也好,勝過他一人寥落地活在這個世上。繁花如錦到頭來是長恨一夢。
梅花開似雪,紅塵如一夢。到了生命的歸宿。
她,更像是錯了朝代,早生了數百年,唐愛牡丹,宋愛梅。江采萍似乎更應該出現在宋代。成為一撥文人意淫寄托的對象,獨獨地占盡風流,不要和楊玉環那株洛陽牡丹爭艷,不應該落的個“柳葉雙眉久不描,殘妝和淚濕紅綃。”的下場。周瑜在死前問蒼天:“既生瑜何生亮?”對梅妃來說亦是如此。有了一個江采萍,何必再來一個楊玉環,若是悲劇,毀滅一個也就夠了,何必要兩個絕代的佳人,一起葬送在開元盛世的余燼里。盛世高唐這把火,燒得人心涸如死。
宋愛梅,蔚然成風。看似雅然。卻有它的不得已在,民眾審美情趣的變化,折射的是歷史的變化——唐的輝煌與宋的貧弱。宋是一個積弱積貧的王朝,開國伊始就處在外強的凌辱之下,南渡以后,國勢更是江河日下,風雨飄搖。不比大唐國富民強,從骨子里就滲出富貴的風韻來。
積弱的國勢,使長期生活在內憂外患中敏感的文化人,對頂風傲雪、孤傲自潔的梅花有日趨濃烈的欽佩感,把她視為抒懷詠志的最佳對象。陸游走在沈園里慨嘆:“何方可化身千億,一樹梅花一放翁”。他寫“無意苦爭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塵,只有香如故”。是以梅花的勁節自比。陳亮寫“墻外紅塵飛不到,徹骨清寒”之句,則以梅花的清高自比。辛棄疾喟嘆“更無花態度,全是雪精神。”更以梅花冰肌玉骨的儀態自詡。
如果說生活在南宋中前期的陸游、陳亮、辛棄疾等人,他們以梅花的標格比擬自己,意在表現無論多么艱難的情況下也不放棄自己的抗金救國的愛國之志的話;那么到了南宋末年,宋亡已成定局的情勢下,大多正直文人的詠梅之作,則是表明他們學梅花潔身自好,寧當亡宋遺民也不愿委身事元的悲苦無奈的心態。
很多文人都是愛梅成癡之人,這些人當中不乏才智高絕的,卻再也沒有人能寫的出“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的絕唱并不奇怪,愛是真愛,只是對梅的愛有太多潔凈剛硬的味道在,于是更像是在顧影自憐。誰分得清是愛水仙,還是愛著像水仙的自己。
再也沒有人如林逋愛梅愛得純粹。梅似女子,芳魂有知也只寄知音一人。
有一個女子,她在自殺之前,寫的絕命詞是陸游的《卜算子·詠梅》——驛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