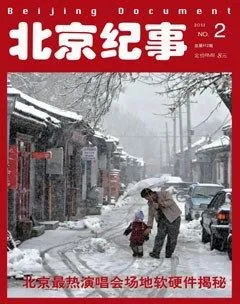和電影一起慢慢地變老
張開濟老先生的一句口頭禪“沒文化”,意指那年頭北京城的大拆大卸。他年輕時進京,火車開到東便門,見了城墻就特震撼。可惜后來沒了,眼看的只有老照片,只能讀讀侯仁之先生的文章,或自己憶憶舊。幸運的是東便門和一段城墻還在,當年崇文門往東三角地的破爛房子挽救了它。墻角里能看出歷史的機會不多,琉璃廠附近有一處,北京第一實驗小學旁邊的墻有京劇武生的浮雕,黑黑的落滿塵土。中國自己的第一部電影《定軍山》的百年紀念地,不仔細看就走過了,真該見見新。
北京的南城,當今的潮男潮女誰會相信中國的民族電影文化從這里開始?從這往東兩三里地大柵欄的大觀樓電影院,北京最早的看電影的園子,是70年代初宣武崇文少年的圣地。往南的珠市口電影院,荒廢后只剩下前臉,變成了環保公廁。再往南的中華電影院還在,記得周邊還有幾家。當年看得最多的是《列寧在1918》《列寧在十月》,動畫片《半夜雞叫》周扒皮。后來有名聲的是《閃閃的紅星》祝新運,受到紅都人人羨慕的革命童星,可惜那時真沒神馬追星族,往事如浮云。
外國片那年代也有,遙遠阿爾巴尼亞的《勇敢的人們》,鄰居朝鮮的《鮮花盛開的村莊》,都有樂子,羅馬尼亞的《多瑙河之波》最浪漫。看的都是露天場,喜歡去陶然亭公園的露天電影院,要提前買票,寬大的水泥座,不對號,開演以天黑為準。最愛看的是抗美援朝的片子,《奇襲》《打擊侵略者》,純正的紅片,培養了我們這一代的愛國情懷。看露天電影也是北京一些大院的特權。到了70年代末有了解禁的《紅樓夢》,有了南斯拉夫的《瓦爾特保衛薩拉熱窩》。有時兩個大院比著演“內部片”,忙壞趕著看的人,擠門爬墻頭有點鬧。后來在食堂看電影,一放就連著兩部,人多密不透風,也沒覺得憋和醬油酸菜味。老覺馮導的電影是從這里啟的蒙,要不咋就那么生活。
原始共產主義般的電影消費忽然有一天就消失了,像迅速消失的青春年華。
市場化有些舒適度的電影院如東城的“大華”、西城的“首都”成了戀人們的聚集地,就如大上海的外灘。單位最大的就是人民大會堂,看電影最有氣場,幾千人,印象深刻的《苔絲》,看完了不明白又去看哈代的小說。早一些時候,看最有爭議的《創業》“左傾”、《苦戀》“右傾”,是在公安部禮堂和中央警衛局禮堂,戒備嚴,座椅好。后來,在市委常常去看受教育的片子,市委對面臺基廠二條經貿部宿舍禮堂,簡陋但方便,看完一拐彎就到家了。北池子電影公司小廳,看《離開雷鋒的日子》。在密云水庫中的別墅體檢休養看電影的好日子,一部《瘋狂的石頭》,有些另類的電影。別墅也另類,是給我們開國最高領導人建的,總理的房子小一點,主席的大,可他老人家一次沒去過。
不能不提的80年代中期的法國、意大利電影回顧展,法國片最吸引國人的《火之戰》,有票讓我給送人了,后來再也沒看過。據說有點色,但在現在應該屬于見怪不怪,在那時是驚天動地,沒辦法,我們都還沒見過世面。法國的“新浪潮”看不懂,意大利政治電影的故事又有點老。美國電影《金色池塘》感染人,在首都劇場看的。《克萊默夫婦》家庭倫理片,有一個一閃而過的裸體鏡頭。還值得一提的是我國土生土長的一位電影理論家,鄭雪來。他的一本《電影學論稿》1986年由中國電影出版社出版,精裝3.35元。“有較高的學術價值,適合于專業和業余的電影工作者,電影愛好者及大專院校師生學習參考。”鄭先生是我的鄉黨,抄一段算植入廣告,可惜北京的舊書店不好找。
看這書讓我想起上面這些零碎事。一句話,電影是大工業時代的文化,是現代城市文明的寵兒。
90年代的影碟機讓很多人遠離了電影院,電視成就了一波又一波明星,以為電影院就這樣子衰敗下去了,沒想到在新世紀的第10個年頭復興。從第5代導演開始,堅持總要有回報,《紅高粱》《黃土地》《甲方乙方》《霸王別姬》。看今年三部片子葛大爺輪番登場,本山大哥走江湖,終于完成了北京2010年總票房11.8億。影院破百家,銀幕破500塊。
吃電影飯,發電影財,故事天天都有。最新消息《讓子彈飛》票房過6億,姜文可以高高昂起頭,咱也有錢了。繼續奮斗吧,為了《陽光燦爛的日子》,為了《鬼子來了》,為了永遠的《本命年》。
編輯/麻 雯mawen214@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