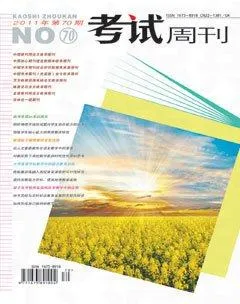中國土壤中的生態女性主義之花
摘 要: 本文探析了《大地》中生態女性主義思想。賽珍珠意識到了男性對女性和自然的雙重壓迫,以及女性和自然復雜而緊密的聯系:大地與女性共同具有的母性和孕育功能,大地與女性之于人類的重要意義,以及大地與女性在父權制社會的地位,使二者建立起了親密又特殊的關系。同時反映了賽珍珠早期的生態女性主義思想。
關鍵詞: 小說《大地》 女權主義 生態女性
一、引言
賽珍珠(Pearl S.Buck或Pearl Buck)(1892—1973),直譯珀爾·巴克,美國作家。1932年憑借小說《大地》(The Good Earth)獲得普利策小說獎;1938年獲諾貝爾文學獎。她也是唯一同時獲得普利策獎和諾貝爾獎的女作家,作品流傳語種最多的美國作家。諾貝爾文學獎獲獎作品是中國題材的《大地三部曲》、《異邦客》和《東風·西風》;諾貝爾頒獎委員會對她的評語是:“對中國農民生活進行了豐富與真實的史詩般描述,且在傳記方面有杰出作品。”[1]《大地》講的是發生在上世紀三十年代中國皖北鄉村的故事,農民生于土地,死于土地,從土地里刨食發家致富,世世代代循環不已。故事的男主人公王龍,他的生活方式與他的先輩們在數不清的世紀里所過得生活并無二致。小說從王龍的婚姻和他的人丁興旺之夢開始。他娶恭順、能干而沉默寡言的地主家丫鬟阿蘭為妻。阿蘭與他一起起早摸黑、節衣縮食地過著苦日子,機靈地在城里搶大戶的過程中獲得珠寶,終于幫助王龍把一塊塊地從黃地主家買來,如愿返回故里,置田地,雇長工,篤定做起地主來。王龍對土地懷著深深的眷戀,有著執著的追求,阿蘭夫唱婦隨。王龍的巨大渴望,首先是做一名父親,其次就是得到更多的土地來耕種,一切預示著幸福和興旺。在王龍發家后的第七年,村里鬧起水災,饑荒來臨,但擁有充足錢糧的王龍沒有絲毫的惶恐,麻煩的是他變得無所事事。他造了庭院,買了仆人,納了小妄,日夜陪她吃喝玩樂,并冷落了阿蘭。小說通過刻畫阿蘭這一形象,突出了中國婦女的賢良、寬容、勤勞和睿智——她是王龍一家人精神上賴以生存的大地。同時大地對于舊中國農民而言,寓意深刻。大地承載著中國農民的歡樂和痛苦,與他們的命運休戚相關。最終,王龍意識到決定他命運的不僅僅是賴以生存的大地,還有他一直視而不見的阿蘭,她像大地母親一樣寬厚堅強地支持著他。《大地》突出表現了土地與女性的同等重要性和相同特質,把對生態自然的關注與女性思想結合起來,關注父權制社會中生態問題與女性的生活狀態。
二、土地與女性身體的內在聯系
麥茜特(CarolynMerchant)認為:“有機理論的核心是將自然,尤其是地球與一位養育眾生的母親相等同:她是一位仁慈、善良的女性……”[2](P2)生態女性主義相信女人與自然有極大的親近性,在生理上女性如月經、懷孕和生產過程的經驗類似自然生態的循環,有其周期性存在。在發展的過程中,人類在女性與自然之間建立了某種相連性,一方面,大地孕育萬物的自然現象被類比為母親哺育子女的天性,另一方面,在文明與自然的二元對立里,女性如同自然,代表的是原始、被動、情感、柔弱和神秘,需要由進步、主動、理性和強壯的男性來引導和開發。[3]
在《大地》中,土地對于舊中國農民來說就是命根子,土地使他們有希望、有盼頭、有收獲,使他們富裕。王龍發家的過程就是不斷收獲的過程。小說中有這樣一個情節巧妙地把女性的孕育功能與大地的生息繁衍結合起來:正值秋收季節,地里的稻粒飽滿,稻穗熟透,阿蘭和王龍正忙著秋收,恰逢阿蘭生下了兒子。豐收的喜悅和初為人父的喜悅交織在一起,大地與母親的角色被象征性地結合在了一起。對男人而言,女人的生育也就意味著一種收獲。所以這種收獲既有大地的豐收,又有人丁興旺的寓意。
女性如同大自然一樣承擔著孕育和繁衍生命的偉大使命,男人永遠不會像女人那樣與自然融合在一起。這是女性在生理、心理方面更接近自然的特性決定的,只有女性才能做到與自然息息相通。
三、大地與女性同為“他者”的地位——自然災害與婦女歧視
在男權文化統治的社會中,女性與自然在地位和遭遇上有著相似之處,都處于被壓迫和被統治的地位。在《大地》中王龍一家的命運隨著土地的收成起起落落,臉朝黃土背朝天的中國農民世世代代靠種地為生,在以人類為中心的封建社會中,由于人們不懂保護環境、維持生態平衡,自然災害頻發。人類只是一味地最大化自己的收成,自身也受到懲罰。在王龍發家第七年,由于西北的雪過量,從那里發源的北邊大河河水暴漲,沖破了堤岸,淹沒了整個地區的田地。人類在自然面前顯得如此渺小和無力,只能看著洪水淹沒自己的莊稼,卻束手無策。
在封建社會的舊中國,存在著嚴重的男尊女卑思想,婦女的地位極為低下。對于娶妻生子,王龍也是聽從父輩的觀點,正如他父親和黃老太太的建議,女人無所謂年輕好看,“要好看的女人干什么?我們要的女人得會管家,會生孩子,會干田里的活,好看的女人會干這些事?她會想著穿什么樣的衣服來配她的臉蛋兒!在我們家可不行,我們是莊稼人”。[4](P7)他們從狹隘的實用主義角度出發來衡量人的價值,就像王龍對待自己的田地一樣,他認為阿蘭不是“漂亮”而是強壯,只是一個生育工具和干活的好幫手。因為對農夫來說,一位強壯的妻子更能操持家務。這是對女性的歧視,也是對女性的價值的巨大傷害和徹底否認。盡管《大地》中的阿蘭恪守中國傳統道德觀念對婦女的種種約束和定位,服從、勤勞而堅韌地幫王龍打理這個家,但她的顯著話語特征卻是沉默。她沒有經濟地位,處于“他者”地位,只能把自己變成男人的附屬品來取悅男人。王龍的虛榮心日益膨脹,荷花的到來滿足了他原始的性的欲望和沖動。他開始嫌棄阿蘭的容貌,劣根性暴露的王龍覺得阿蘭渾身上下都不好看,“尤其是她穿著松松寬寬的大鞋……她乳房松弛了,像油瓶一樣吊著,再沒有一點魅力”。[4](P151)但荷花終究只是男人的玩物,最終也被拋棄。處于“他者”地位的女性,注定了其人生的悲劇。
四、大地之于人類等同于女性之于家庭——女性與大地的融合
在小說《大地》中盡管自然和女性同為他者,但土地對于農民、女性對于家庭起著決定作用。世代以種地為生的農民,“土地情結維系著他們和土地的情感。小說以《大地》為名,強烈突出了作品的主題意義,勤勞的中國農民‘生于斯,長于斯’的熱土上揮灑汗水,生息繁衍,演繹著悲歡離合的故事,土地承載著夢想。即便在最困難的時候,他們仍留著土地。無論是顛沛流離,還是命懸一線,只要土地還在,他們就能拼死活下去。土地是他們生存的最大動力。‘至少我還有田——我還有地。’土地是王龍一生中最重要的財富,當王龍的叔叔領著城里的投機商來趁火打劫廉價買地時,王龍憤怒地叫道:‘我絕不賣地,我要把地一點一點地挖起來,把泥土喂給孩子們吃,等他們死了,我就把他們埋在田里,我和老婆,甚至我的老爹,我們都要死在這塊給我們生命的田地上。’”[4](P52)在他們眼中,土地就是他們的命,尤其是當阿蘭病倒,醫生說要五百塊銀元才能醫好阿蘭的病時,昏睡中醒來的阿蘭卻說自己的命不值那么多錢,這些錢能買好大一塊地。她把土地和自己的命相比較,竟然認為命不如土地值錢。
王龍日漸走上富裕的道路后忘乎所以,生活奢華,終日沉溺女色,冷落結發之妻阿蘭,視她不存在。阿蘭忍辱負重,孝敬公公,照料全家,維護丈夫的尊嚴。直到阿蘭病倒,在床上躺了好幾個月時,王龍和孩子們才第一次感覺到了她在這個家庭中的重要性。因為以前阿蘭會打理好家里的一切,人人過得舒舒服服,他們對此毫無感覺。現在家里一下子沒人生火做飯,沒人照顧老人,所有的事都向王龍壓來。他不知所措,他第一次把臉轉向黑墻像小孩子一樣嗚嗚地哭了起來。他深深地感覺到阿蘭就是他的精神大地,一直伴他左右,阿蘭的倒下讓他精神崩潰。在此,以阿蘭為代表的女性形象就和大地融合在了一起,作為中國傳統女性的品質和精神也在中國大地上生生不息。
《大地》通過描寫王龍一家在中國這塊土地上平凡而動人的故事,突出反映了土地之于農民的意義。同時通過刻畫阿蘭這一傳統的中國婦女的形象,深刻地指出了阿蘭是王龍一家精神上賴以生存的大地。
參考文獻:
[1]Buck, Pearl S. The Good Earth [M].New York: Harper & Row,Publishers,1931.
[2][美]麥茜特.自然之死:婦女、生態學與科學革命[M].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
[3]羅婷,謝鵬.生態女性主義與文學批評[J].求索,2004,(4).
[4][美]賽珍珠著.王逢振等譯.大地[M].桂林:漓江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