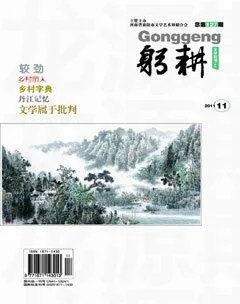河灣的記憶
故鄉源潭地處唐河縣城上游幾十公里的地方,是一個三面環水的古鎮。鎮子西面是奔流不息的唐河,東面是蜿蜒曲折的毗河,南面是自東向西而流的泌陽河,三條河水在小鎮南面三岔河口交匯后,一路向南奔流而去,在缺水的北方,像這樣豐水的地方并不多見。源潭可稱得上是名符其實的水鄉了。
每次回老家總是忍不住要到河邊棲坐、漫步,總想找回童年那些美好快樂的記憶。童年是什么?是清澈的河水,是綠色的田野,是茂密的樹林,是河邊青青的水草,是鄰居家那個清爽的女孩。小時候故鄉的河水是那么的清瑩、甘甜。河里面水草豐美、魚蝦成群,依河而居的農家大多是在河里挑水吃,用河水洗菜、燒水、做飯。即便是夏天,河里漲渾水,人們也要把河水挑回家倒進水缸內,再放入些明礬打點幾下,震清后便又可飲用了。奶奶在世的時候常說:用河水熬的綠豆湯、炒米茶才好喝。那一灣碧水就像慈母的臂膀把小鎮攬入懷中,她用甘甜的乳汁養育著兩岸成千上萬的兒女們,使他們在她的哺育下世代繁衍生息、耕讀勞作。
我是在小鎮西邊的唐河邊上長大的。在兒時生活的所有記憶里,唯獨那條河讓我難以忘懷,河水岸邊散落著我童年快樂的印記,就這樣一直溫暖著我的人生旅程。當年,鎮上街道兩旁還有許多木板結構的透雕樓閣、飛檐翹角,古樸雅致。街面上散落著幾家茶館,茶館大約有十幾平米,屋子里擺著七八張桌子,放幾條長凳,供人們在那里休閑、聊天、品茶。那時河水是清澈的,有人專門挑河水往各個茶館里送,每擔收取兩三毛的力氣錢。老人們說用河水沏出來的茶,入口光滑、茶香溢鼻,好喝有滋味。茶館當然是民間藝人們常常光顧的場所,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在尚存的幾家茶館里還能看到各色藝人出現的影子,藝人們在那里彈三弦、打蓮花落、唱大調曲、說評書。名氣最大的要數一位侯姓評書藝人,他說的評書大多是俠肝義膽的英雄豪杰,情節曲折,人物生動,一部《明清八義三俠劍》一說就是幾個月,場場爆滿,令人如癡如醉,蕩氣回腸。如此,東家賣茶,藝人賣藝,休閑的人娛樂,悠然恬淡相得益彰,一塊醒木一杯清茶造就了小鎮特有的地域風情,多少給小鎮增添了些許煙雨江南的人文風韻。
我家西邊不遠處的河邊,有一個被洪水沖壞的磯頭,當地人習慣叫它爛磯頭,那里是我小時候同玩伴們常去的地方。每當夏季來臨榴花綻放,河邊便開始熱鬧起來,暮色下,三五成群的少年聚在河邊,在水里嬉戲,比扎猛子,看誰在水里扎的時間長。勞作了一天的大人們也會融進這暖暖的河水里,洗去全身的疲憊。這河水也不完全屬于男人們,在磯頭下邊不遠處,還有一處女人洗澡的地方,夜色中總能聽到她們喃喃的細語,歡快的笑聲……。
兒時的記憶中總能覓到淘氣的影子,在綠柳低垂的對岸,遠處有一大片竹子林,我同伙伴們常去那兒砍竹竿用來釣魚。有一次剛進竹林還沒有來得及下手,就被看竹子的人發現了,我撒腿就往河邊跑,他在后邊追,跳進水里后那人也不放過,撿起地上的坷垃往河里砸,我一個猛子扎了好遠,他才罷休。還有一次是去對岸偷西瓜,中午最熱的時候同幾個小伙伴游過河,上岸后往身上抹些泥巴,編個柳枝帽往頭上一戴,鬼鬼祟祟地往一塊西瓜地爬去,也不懂瓜的生熟,專挑個大的摘,等把瓜抱到一處草溝里打開一看,全是白籽,瓜不熟,幾個人只好作罷。順著河道往回游,上岸后發現我和伙伴們的衣服全不見了,正著急,看見種瓜的老頭領著我爺爺,手里拿著我們幾個人的衣服向河邊走來。原來,我們幾個一到瓜地邊,種瓜的老頭就發現了,他氣壞了,就從河邊的另一處游到對岸把我們的衣服全收走了,找到家里告狀、不依。后來才知道他是心疼瓜不熟吃不成,被我們幾個小孩子給糟蹋了,因為這種事情之前發生過好幾回了。
家鄉的河是慷慨的,住在河邊的人家中有許多逮魚人。印象中,河里的魚似乎總也逮不完,逮魚人織些各種各樣的網,如撒網、拖底撈網、沾網等,他們一年四季在河里忙活著,把逮到的魚拿到魚市上賣。依稀記得,上年紀的漁人常常會把逮到的小魚重新放回河里,讓它們繼續生長,這樣,河里的魚才能保持連續的生長鏈條,人們一年四季總能吃到新鮮的魚。現在想來,老漁人們當時的做法也算是網開一面了。
家鄉冬天有一種特殊的捕魚方法,當地人把這種方法叫做下“漚子”。秋末時節,在河道邊打幾個木樁子,再砍些樹枝堆在水里,然后在上面蓋些苞谷桿,棉花柴之類的東西。冬天來臨,河水溫度驟降,誘使魚兒在“漚子”里越冬,等到三九天用深網把“漚子”圍起來,拉走水里的樹枝,用撒網把里面的魚逮起來,收成好的“漚子”一次能捕到上千斤的魚呢。
不知道從何時起,故鄉這條盛著我全部童年歡樂的河流,開始變得不再豐潤,眼簾中似要干涸的河道,淺可見底,水面上長滿了綠藻、浮萍,哪里還能看到白鵝紅掌撥清波,魚蝦成群伴水游的場景?藍天依舊,碧水卻難覓了。感慨中我想到了兒時的伙伴——舟子,如今,不知道他還能否逮到幾斤重的大魚了?
記憶在歲月的長河中悄悄流淌,順著河畔尋找,想找回童年點點滴滴的童真,想找回少年朦朧的愛戀,只怕這深情的回望只能珍藏在記憶深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