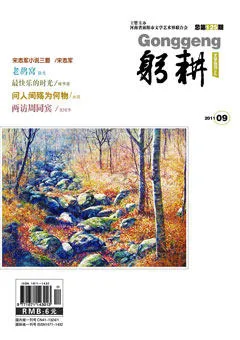一本書的重量
其實我這幾年里,一直都想以文字的形式,來寫一篇文章,哪怕是一章讀者感,來表達我對孫老師的感激之情。但幾次提筆,卻終不能成行。正如一個作者說的,太過厚重,以至于筆力不能及了。
記得剛認識孫老師的時候,我正年少輕狂。那時我正興致勃勃地寫一些風花雪月的文字,有不著邊際的詩歌,還有我自己都不知道究竟想表達什么意思的散文詩。也有情感之類的散文,但決不是現在我寫的這樣子。正如一個呀呀學語的孩子,卻還總想模仿著別人的模樣而舞蹈。我拿著幾篇自以為得意的文字,讓孫老師看。之前我對孫老師并不了解,只是從剛刊發的南陽《躬耕》雜志上看到他寫的散文《駐隊筆記》,其中記錄那個年代下隊勞動的幾個片段,許多年過去,那篇文字中的場景在我的記憶里卻依然清晰,比如遺留在歲月深處的門板宴,還有我們當地的一種勞動工具叫箢子,箢子后面的系著的一個“絆兒”,擔著青青的秧苗,如潑水節一樣生動活潑的打秧把。這些情節被他土香土色的文字描繪著,其中人物有可親可近的白大叔,和有著一副熱心腸的隊長……
只是這些語言的表達方式跟我當時的寫作不大一致,用旁人的話說應該不是一路人。但那些生動的敘述,與文字的穿透力卻是頗具魅力的,那一刻我忽然感覺自己的寫作路子在某些地方出現了偏差,因為真正的文字是具有感染力的,讓讀者無形之中就能感受到文字存在的價值與分量。也正是那篇《駐隊筆記》,讓我對老師印象很深,后經朋友介紹,終于認識了這位至今令我說起來就有說不完的話題的孫老師。記得當時老師看著我的遞過去的草稿,指出許多的不足,說起文字的寫作方法。他說:文章是改出來的,千錘百煉才是精品。
雖說孫老師的的文字已經達到爐火純青的地步,但他不喜張揚,為人也很低調。記得與他還不相熟之前,我曾被文友們慫恿著出書,因為在文化人的意識里,出了書,就標志著你就是作家了。為了成為大家心目中的作家,我迫切希望展示自己,甚至開始著手整理出書的詩稿。后來認識孫老師,我興沖沖地將這想法告訴他,他淡淡的一句話,頓時讓我興致銳減:你剛開始寫作,就忙著出書?我說孫叔你也該出書了吧。他說還早著呢,文字是要經得起時間的考驗。我有些納悶,作為國家二級作家的前輩,許多稿件都在各種刊物上發表,面對當前的出書熱,他竟然無動于衷,這讓我頃刻之間感覺到自己的浮躁,越來越覺得,跟著這樣的前輩學習,一定錯不了。
在后來的日子,我的許多不成文的稿子,大多都經孫老師過目。回過頭去看看之前被孫老師指導過的文字,字字推敲句句用心,這些都與老師的為文嚴謹有關。可以這樣說,沒有孫老師的指導,我的寫作就堅持不到今天。有一陣子,為了生計,我曾對寫作處于漠然狀態,覺得文字這東西太枯燥,寫了那么多,能走出去的卻很少。一向低調的老師卻鼓勵我說:有些雜志是不講關系的,比如你曾投過稿的洛陽《牡丹》,就很講究純文學。想想是了,我曾在《牡丹》投過幾篇稿子,不久就采用了我的一篇短篇小說《俚歌》(這章文字的標題就是孫老師給幫著起的),且得了一百四十多塊錢的稿費。這次文學上的肯定,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可謂為我文字路上的無形動力,對我今后的寫作影響很大。
先做人,再做文!這是老師送給我的座右銘。此句經常在我的文章里引用,也成為我結交人際關系時衡量一個人的標準。看慣了太多的爾虞我詐,領略了太多的口是心非。與孫老師交往的這些年,他的厚道,他的清高,他的倔強與任性,都讓我從不同角度地去欣賞,并愈發地讓我尊重。他對如我這樣的后輩的無限關愛,是無法用有限的文字去衡量的。我只能懷著感激之情,除了關注他生活中的小細節,再就是仔細品讀他的文字,正如品讀他樸實厚重的人生。幾年前他出的三本書,我一直精心保存著,故事集《千年等一回》通俗易懂,自以為聰明的我卻是怎么也不能模仿;小說集《走出雪谷》讀來平易近人,閑下來的時候,時不時地從書架上抽出來翻看學習。散文集《與山對話》這本書里記錄下的大多都是家鄉桐柏的風物與人情,成為我們這個時代的年輕人最值得牢記與珍藏的精神財富,至今還擺放在我目力能及的書桌前,以便于寫作時的參考與引用。
他說,將自己還算滿意的文字整理成冊,留給后人就知足了。
最近老師又出了一本長篇小說《御賜劍》,高山流水的語言,扣人心弦的故事情節,千轉百回之處令人擊節叫好。正是盛夏時節,窗外的蟬此起彼伏揚喉高歌,將這個火燒的季節渲染得淋漓盡致。我沉醉在書案前,在風扇吱吱嚀嚀的搖擺中,從散發著墨香的書頁里徜徉的那刻,忽一陣感慨襲上心頭:這樣一本厚重的書藉,要耗費他老人家多少的時間與精力,其間又蘊含著多少年的知識積累,與幾經磨練的豐富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