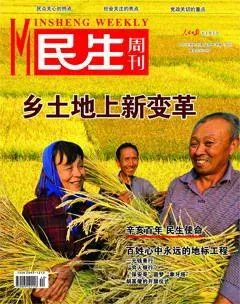“窮人銀行”
“面向窮人,只需要很少的資金,就可以改變一個家庭的命運。這正是扶貧社成立的初衷和一直不曾改變的定位。”
河北省易縣南百泉村的鄭慶霞是個高大結實的中年女人,因為丈夫跛腳,還有3個孩子,家里的日子一直過得苦辣辣的。原本以為要過一輩子的窮日子,卻由一塊地毯開始轉變。
1998年,鄭慶霞看到縣城有人賣手工編織的真絲地毯,銷路很好,就跑到熟人那里學了這門手藝。可即使織一塊最小規格的毯子,也需要1千多元成本,她拿不出這筆錢。
就在她一籌莫展之時,從別人口中得知的“扶貧社”成為她唯一的希望。她找到貸款員,試探著問:“我家就兩間房子。全押給你,給我貸點錢行不?”
“就你那兩間破房,賣了也值不了幾百塊。”貸款員開玩笑說。
鄭慶霞做夢也想不到,一個星期后,沒有抵押擔保,也沒有請客送禮,“賣了也不值幾百元的破房”居然貸了2000元。用這筆錢,她買了各色絲線和織毯工具。 3個月后,一塊花草圖案的手工真絲毯完成了。她拿到縣城的地毯市場上,賣了1800塊錢。此后,一塊塊地毯相繼織成,賺的錢也早已超過了當初的2000元。
如今鄭慶霞已經是遠近聞名的富裕戶,經手資金動輒百萬。但對于她來說,多少錢也沒有她當初從扶貧社貸到的2000元起動資金金貴。
“面向窮人,只需要很少的資金,就可以改變一個家庭的命運。這正是扶貧社成立的初衷和一直不曾改變的定位。”易縣扶貧社負責人周學仁說。
截止到2010年12月底,扶貧社在易縣境內20個鄉鎮累計發展中心227個,累計發展小組3733個。先后累計扶持農戶20424家,直接受益人口達到78370人,累計發放貸款10855萬元,其中婦女受扶持率占80%。像鄭慶霞家一樣的6500戶貧困農戶得到了穩定性脫貧,走上了致富路。
復制來的“銀行”
1997年,易縣石井村楊翠蘭的丈夫突發重病,手術費需要兩萬多元。她找遍所有的親戚“攤錢”,仍然不夠。情急之下,她托熟人幫忙,到信用社貸了4000元,才算湊夠了手術費。
因為很少有人能從信用社貸到款,這事兒成了當時村里的大新聞,人人羨慕楊翠蘭能耐大。“他們不知道,我給辦事的人花了幾百塊錢,買了幾條好煙呢。”她撇撇嘴。
“如果不是‘走后門’,像楊翠蘭這樣的貧困農戶,絕對屬于被金融機構排斥在外的人群。”在易縣扶貧社當了13年主任的周學仁,一語道破基層信用社的潛規則。
為什么越是需要錢的窮人越是貸不到款?在金融世界里,“義”與“利”果真就沒有調和的空間?很久以來,中國社會科學院扶貧領域專家杜曉山一直在思考這樣的問題。
在研究中杜曉山發現,國家的貼息扶貧貸款從始到終伴隨著權力尋租:或者被政府官員層層截留、挪作他用,或者優先貸給了富裕戶。而真正的窮人如果想獲得貸款,往往不得不付出額外的“灰色支出”。
一次“邂逅”,讓杜曉山豁然開朗。上世紀80年代中后期的一個國際研討會上,杜曉山第一次接觸到了孟加拉人尤努斯。他吃驚地發現,尤努斯一手創辦的孟加拉鄉村銀行,堅持只給窮人中的窮人貸款,完全借貸給無抵押擔保能力的窮人,而還款率卻高達98%以上。數年下來,尤努斯的鄉村銀行已經幫助240萬個赤貧的孟加拉家庭得到貸款,其中3/5的家庭因此走出貧困線。
一直困惑于此的杜曉山,隱隱感到,或許孟加拉模式是解決中國扶貧貸款的一個“好招兒”。
在經過數年的醞釀與籌備之后,杜曉山決定在中國也成立一個像孟加拉鄉村銀行那樣的幫助窮人的銀行。
河北易縣成為第一塊試驗田。因為它是離北京最近的國家級貧困縣,便于管理和節省資金。從地形上講,易縣地處太行山東麓,地形有山地、平原、丘陵,和中國絕大部分貧困地區地形地貌相近。而且,杜曉山一位同事的大學同學恰巧是易縣的副縣長,溝通起來比較順暢。
“當時縣里正在引資上項目,大家并不太理解小額信貸是什么,只是作為一個招商引資項目吸收的。”當年與杜曉山一起籌辦易縣扶貧社的周學仁笑著回憶說。
窮人的信用
扶貧社幾乎原封不動地把孟加拉全套操作模式拷貝過來:以婦女為主體,5人小組聯保,每周分期還錢,按照貸款額的5%收取小組基金和強制儲蓄作為風險基金,按期還款以后還可以接著貸款并可以提高借款金額,可以無限期地循環貸款……
出乎意料的是,這種小額信貸推行得格外順利。“開始我們還怕農戶不響應。結果,村里在喇叭上一廣播,就有70多戶人家跑來交了申請。那個村當時的主要經濟來源是搞種養業,也有擺小攤的,很多人急需錢,又借貸無門。”易縣扶貧社主任周學仁回憶說。
1994年5月,身患小兒麻痹癥的易縣西陵鎮五道河村村民朱秋菊從扶貧社得到一筆1000元的貸款。同時收到錢的,還有另外20個農戶。這是扶貧社成立后發放的第一批貸款。
“初期幾乎順利得匪夷所思,”杜曉山說,“老百姓不僅沒有抵制這套做法,而且非常配合地遵守規則。尤其是頭3年,還貸率達到100%。”
在周學仁的印象中,故意賴賬不還的農戶微乎其微。“越是貧窮、閉塞的地方,大家信用就越好。”他說。
對于村民的純樸和信用度,易縣扶貧社信貸員劉惠深有感觸。這個短發,圓臉的姑娘,從1998年開始做信貸員,每天騎摩托車穿行在鄉下,在貸款戶中特別有“人緣”。
“有一次我負責的貸款戶手里真的沒錢還,”她架起雙臂比劃著,“那老太太給我幾十斤玉米,讓我替她賣了還錢。”
2001年夏天,城關頭道河村的一條小河因為下大雨變寬了,河水淹沒了小橋。到還款的日子,信貸員過不去,在河對岸著急上火。借貸的農戶們便想出個辦法,把錢綁在石頭上,從河對岸扔了過來。
中國式的創新
不同于一開始完全照搬孟加拉鄉村銀行的制度,現在的扶貧社已經在原有的孟加拉模式上有所突破。比如連續放貸,如果你經營項目收益好,需要擴張規模,他們都會放貸。而且,放款額度也進行適度放寬,升到了5000元。即便是對一些聯保小組采取大家申請、一家使用的做法,他們也在保證貸款安全的前提下,采取了“默認”的態度。
現在扶貧社已經走出易縣,在多地建立扶貧社的試點。“每個試點必須要與當地情況充分結合,在基本制度不變的情況下,一定要進行適合當地的創新。”周學仁表示。
據了解,易縣扶貧經濟合作社現有工作人員29名,員工們的福利保障比較充分,除了養老、醫療保險外,還有合作社為他們買的人身意外傷害保險。周學仁算過一筆賬,如果還貸率低于95%,合作社的運行就會成問題。
扶貧社只有一輛普通桑塔納車,平時很少有人用,連周學仁下村走訪調查,也騎自行車。汽車大部分時間被合作社放出去搞創收了。周學仁說,扶貧社還需要過精細的日子,況且,他們還資助著上百名貧困生上學呢。
周學仁在工作之余便四處化緣,他希望能有更多的錢充實到扶貧社來,給更多窮人致富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