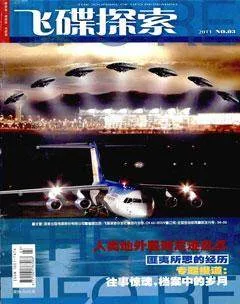遙遠的達爾文演化論
2009年是達爾文誕生200周年,也是他發(fā)表《物種起源》150周年,達爾文提出的演化論學說,對作為西方文化重心的基督教信仰,產生了思想上的挑戰(zhàn)和啟示,西方學術思想界視為歷史大事,也就有許多的活動,來彰顯達爾文提出演化論對人類的影響。
達爾文自幼就對知識堅持追求,也因生命里一個難得的機緣,參加了1831年的一次遠航探險,“小獵犬”號的5年之旅成就了后來舉世著名的達爾文演化思想。
達爾文雖是在大量的動植物化石及地質觀察記錄中,逐漸產生了他物種演化的想法,但是思想學術發(fā)展與社會結構的變化,也確實影響了達爾文從這些觀察數據歸納出物種演化的想法,甚至以一個最適者生存的角度來詮釋。歷史發(fā)展的偶然,是當時提出人口論的馬爾薩斯思想,在那個社會經濟思想大爆發(fā)的潮流中,達爾文自己也承認受到影響,從而以一個適者生存的角度入手,看到隱伏在紛雜物種背后的一個演化原則。
如果以更廣的角度來看,達爾文出生在19世紀初英國維多利亞時代,雖然近代科學已然成形,但是英國還是以宗教信仰為主要社會氛圍,在當時那個基督宗教思想的禁錮中,一種對宗教專制的反抗氣氛,給達爾文的演化論提供了一個契機。達爾文雖然沒有立即成為時代英雄,但是到1882年逝世之時,他的演化思想已經在生物學中占有一席地位,也使他得以葬在牛頓之側。
其實在達爾文去世迄今的120多年時間中,他的演化論在生物科學中的地位亦起落浮沉。在20世紀初,遺傳學和染色體的發(fā)現,使得遺傳實驗學者認為,如果靠改變生物內在遺傳物質便可以改變生物特性,那么天擇和適存的演化便失去了詮釋地位。
如果再看更早50年,《物種起源》發(fā)表100周年的時候,分子生物學的強大攻勢使博物學家的田野工作被實驗室工作所取代,冷戰(zhàn)時期蘇聯(lián)“李森科主義”也使當時的生物學界喊出了“再造現代達爾文主義”的口號。
由這過去100多年達爾文演化理論所面對的歷史場景,便可以看出歷史背景造就了科學思想的社會文化意義,客觀的證據數據,還是要由主觀價值決定其最后意義何在。由這角度來看,也就可以知道,為什么達爾文的演化論,在我們的文化中激不起什么漣漪的道理所在。
其實我們記誦由達爾文演化思想而來的“物競天擇,優(yōu)勝劣汰”,主要是出自史賓塞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思想,而這個思想之所以在我們文化中烙下印記,主要還是與我們20世紀初期身處一個屈辱衰敗的境遇有關,“優(yōu)勝劣汰”正好滿足了我們自19世紀因拒斥西方新科學而遭擊潰羞辱的心理需要。
而今日西方學界,尤其是在美國,達爾文的演化論又被置于一個社會文化的場景中,以達爾文演化論的真知灼見,去對抗近年在美國知識界引起爭議的神創(chuàng)論浪潮。
如果回顧過去,我們是如何毫不費力地就接受了達爾文的演化論,也從來不感到文化基本信仰價值受到任何挑戰(zhàn),便可以知道,面對這一場由西方學界而來的紀念達爾文演化論的文化慶典,還需要有文化價值的思辨,才能夠避免成為又一場疏離文化根源的表面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