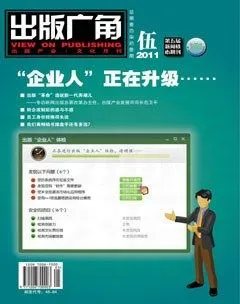現代出版人精神境界細品
總之,當我們從編輯、發行人的精神境界著手去細品現代出版人的時候,會發現還有很多缺陷,有些方面甚至可能還沒有起步,比如全行業對官本位思想危害的習焉不察,甚至在普遍的圖書發行、銷售體系中沒有著意的制度設計,有的人甚至以為體制改革就是讓圖書出版業賺錢,但堅冰的熔化就是在一絲一絲春風的吹拂下悄然進行的,希望就在眼前!
中國出版業,積多年非市場化、半市場化的運行進程,全行業遺留著濃厚的非市場化特征,這些都極大地阻礙著中國圖書出版業的發展步伐。然而,無論是學界還是出版人自身,都對這種非市場化的影響研究和關注極其不夠,更談不上出版人自身的反省。
編輯的精神境界
現代出版人需要什么樣的精神境界?筆者以為,獨立自主、理性創新才是當代中國出版人的精神風貌。一個獨立自主、理性創新的時代品格,意味著它有一個自成一體的文化體系。知識本身形成了自我傳承的內在衍生機制,它本身就具有久遠的生命力,所有動力都自于一個貫穿始終的文化思想目標——傳播文明、創新思想,而這非得具有獨立、自主、理性、創新這樣精神品格不可,這是被中外文化發展歷史所一再證明了的。
而今,我們經常看到,一些圖書扉頁上除主編、副主編、參編者等一大堆的人名之外,還有編委會主任、副主任、委員,有的圖書還居然設有顧問委員會,自然也就有顧問委員會主任、副主任和顧問委員。一本不足200頁的圖書,印上人名竟然有幾十個。當然,這些大名有的是某個學科、專業的權威,有的擔任聲名顯赫的要職,總之都是按照官職大小、社會地位高低的名次排列。有時遇到官員與學術權威之間無法安排名次時,還會想出一個“主審”、“副主審”的名頭,至于這些顯赫的名字,是否對本系列叢書、某本書、某一章有過貢獻,只有天知道。可能筆者孤陋寡聞,中國圖書出版界這種疊床架屋的主編、編委會、顧問“叢生”現象,堪稱世界出版的“奇觀”。沒有哪一個國家出版界有這么多主編,這么多編委會,需要有這么多顧問!
大部分編輯出版人都沒有意識到這與出版人沒有形成獨立的精神品格相關。其實,圖書寫作是一種高度個人化的精神活動,完全依賴個體的文化底蘊和生活積淀,與外在具有的官職大小、已經獲得的社會地位無關。而一本圖書的生命力所依賴的根本是圖書本身所具有思想、精神價值,其他外在因素起不到決定作用。
筆者在2009年北京國際圖書博覽會的前夕,有幸見到兩個年輕的80后出版人。他們就在一個居民樓里辦公,一番交談之后,在逼仄的居民樓辦公的兩個年輕人形象,在我眼中頓時高大起來。他們選擇圖書作者,從來都不是看頭銜,而是到各大網站博客上去瀏覽,通常閱讀了一百個甚至更多作者的博客之后,會發現兩到三個中意的,然后簽約、下定金。這些作者有的是中學教員,有的是醫生,有的甚至是偏遠縣城的小職員。圖書寫作有時是命題作文,有時原創加命題兼而有之。但總之經過他們包裝推出的圖書,差不多都在排行榜前十名以內,而且一年之內印量均在5萬以上。
這兩個年輕人雖身在居民樓里辦公,但正在進行著與國字頭的部委出版社完全不一樣的出版實踐,不唯作者的身份、地位、權勢,僅憑作者的思想、寫作風格以及圖書內容本身就確定是否值得投資、編輯、發行、傳播。這才是真正體現了人類精神活動的獨立、自主、理性、創新的特性!
發行的文化境界
按照現代出版產業鏈分工,發行承擔著圖書產品實現利潤回報的最重要一環,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中國出版業的最早改革就是直接從發行這一環節開始的。先是新華書店統一發行,到后來出版社自辦發行,再到民營發行大軍的介入,與國營新華書店形成分庭抗禮的 “二渠道”。同樣,發行界已經成為具備多家上市公司為主體,并具備影響圖書編輯出版上游的一個不可小覷的出版力量。
但是,圖書發行僅僅是賣書嗎?發行人需要什么樣的文化境界?
如今,大部分出版社的發行員工都要求是大學畢業,甚至是專業學習圖書發行的,按理完全能勝任圖書推廣工作。但往往發行部門會安排編輯部門的人出差各地配合圖書宣傳工作,如此安排往往有三個考慮:一是出版社產品線非常長,發行部門雖然也安排產品培訓,但并非是每本書都像編輯那樣做到心中有數,所以一般發行部門只做具體的組織工作;二是為哪個編輯部門安排推廣會議,會議推廣費就要分擔一半;第三,教材圖書推廣會一般和下一步教材編寫或者學術圖書出版、文章刊發等勾連在一起,而涉及這些發行部門的人是無法參與的。
由此聯系到目前大部分出版社發行部門的行政設置,大都是業務經理、大區主管、發行部主任再到主管發行的社級領導,一層一層地上來,當然也有分省、地區設立獨立法人公司的,但總之是把圖書發行當作一個純粹的生意在經營。
這樣設置固然沒有錯,但是否應該反省一下:圖書發行人的培養如果與啤酒、化妝品的銷售設置一樣,如何體現圖書發行人的知識與思想傳播的本質呢?毫無疑問發行最為重要的是知識與思想的傳播,而不僅僅是獲得金錢,金錢利益的追逐不應是圖書發行人的唯一目的。就像那個已經做若干年發行工作的同事一樣,如果不再經過深入的行業提升,就會成為一個慣于與書店、書商打交道,精于在推杯換盞之間討要書款、算計批銷折扣的商人,而不會成為一個思想、學術等精神產品有造詣的文化人。一個時代獨立、理性的文化品格即意味著擁有大量不會因為任何外在的勢力,包括金錢誘惑而迷失自己本身目標的文化人,知識人。這些文化人、知識人不僅僅是編輯,更包括圖書發行人。
好在市場化程度較高的出版社,已經意識到這個問題,一般采取輪換制:即一個優秀的發行經理,往往在做幾年發行后去輪換到編輯部門,這樣的人往往成為市場意識最強的出版人。但這還遠遠不夠,無論是在具體制度設計上還是出版人培養目標上,都應該更上一層樓,傳播一種思想,塑造一個時代。
出版人的精神之源
現代出版人,從哪里吸收營養,從而塑造21世紀中國出版人獨立、自由、理性、創新的精神境界呢?
中國幾千年的圖書歷史中孕育著無比豐富的思想文化遺產,其中有許多可供今人借鑒的道德倫理觀念。比如那些視金錢、財富如浮云,而堅持麋田刻書、立言不朽的圖書價值觀,把圖書的傳播與人生價值緊密聯系在一起,它在中國漫長的圖書發展歷史中形成了獨具特色的圖書著述觀、圖書價值觀、圖書歷史觀。它們約束、規范甚至塑造著參與圖書著述、編撰、刊刻和銷售等各個環節人們的行為、心靈和情操。因為它作用于人的內心,并能夠使人自覺遵從,不僅比任何時代的法律、制度等剛性制約更有力量,更具有恒久性,而且構成一個民族區別于世界其他民族的思想文化特質。因此我們強調出版人的精神境界,其意義就在于當中國出版業在大步走向現代化的同時,更應該復興悠久的歷史中那些豐富心靈的一系列傳統,汲取中華民族最偉大的文化精髓,獲得圖書出版源源不絕的文化動力,進而塑造出獨立、理性、創新、自足的現代文化品格。
可喜的是,中國出版界已經開始有了一些極為有價值的出版實踐。比如近百家大學出版社,因為得天獨厚的學術背景,加上市場化程度較高,對形成和穩定以大學教師隊伍為核心的職業知識群體,起到了重要的中介作用。據筆者的初步調查,100多家大學出版社,在出版物作者隊伍的來源上,本校教師與外來作者之比大約為7:3,即以所屬大學為主的作者隊伍構成,兼顧其他大學或社會專業機構作者,大體上形成了以我國高校教師正、副教授和中級講師為核心,再輔之少量專業科研機構的作者群體;在出版物的構成上,學術與教材出版相互支撐,教材與學術之比為6:4,個別為7:3,教材利潤補貼學術出版,形成良性互補。而愈是社會化程度高的大學出版社,反哺主辦大學的比例愈高,有些大學甚至以大學出版社為一個重要的辦學經費來源。
這是一種重要的出版文化實踐,體現的是大學出版社步入現代企業之后文化利潤最為合理的走向,同時也是大學職業出版人對知識出版的自覺追求。它與改革開放之初第一批暴發戶取得第一桶金之后,所產生的夸耀性消費、沉迷于賭博、嫖娼等精神萎靡有著天壤之別。最為重要的是,大學教師隊伍通過大學出版社這個知識商業化的中介環節,獲得了初步受益。優厚的經濟基礎能夠做到學以自養的同時,為實現更為遠大的學術理想創造了經濟基礎,還會促使這個群體獲得健全的學術品格和知識倫理的形成和塑造。最為主要的意義在于,這個群體的受益不是來自于知識之外的政府補貼或者其他資本的贊助,而是來自于知識群體知識本身的再生產過程,通過知識的生產獲得收益,實現了學以自養的根本目標,這是職業知識群體的形成、穩定和我國現代出版企業發展最為穩定的基石。
總之,當我們從編輯、發行人的精神境界著手去細品現代出版人的時候,會發現還有很多缺陷,有些方面甚至可能還沒有起步,比如全行業對官本位思想危害的習焉不察,甚至在普遍的圖書發行、銷售體系中沒有著意的制度設計,有的人甚至以為體制改革就是讓圖書出版業賺錢,但堅冰的融化就是在一絲一絲春風的吹拂下悄然進行的,希望就在眼前!
(作者單位:高等教育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