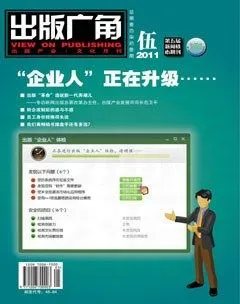為中國圖書找準理想的婆家
在版權輸出的鏈條上,有兩個最主要的問題:輸出什么,輸出給誰。
在版權輸出的鏈條上,有兩個最主要的問題:輸出什么,輸出給誰。本文專談“輸出給誰”。我把輸出對象分成三個層次,一是國外出版社,二是具體的人,三是輸出到哪些國家。
一、國外出版社
版權輸出必須要學會借力,借國外出版社的力。最有可能購買版權的國外出版社,往往是那些對中國主題最感興趣的出版社;專注于出版中國主題的圖書的出版社;最希望擴大在中國的社會影響和市場份額的出版社;在中國已經跟某些國內出版社合作過、特別是確立了合作框架的出版社;在中國買過(同類圖書)版權的出版社;與在你輸出圖書所屬出版領域有精深造詣的專業出版社。只有找準這些出版社,才能在版權輸出方面取得事半功倍的成績。
比如,某國際知名科技出版集團就有一個大型計劃,找中國最有影響的科技社、大學社,在全球合作出版發行英文版科技著作,雙方共同論證選題,國內社負責組稿、編輯、印制和在中國境內發行,該國外社以某個折扣從國內社購買一定數量的圖書在中國境外發行。如果你為國內某個比較著名的理工大學出版社工作,可以精挑細選幾部好稿子,敲開該國外社北京辦事處的大門,與他們一起繼續在這個項目上添磚加瓦。如此,你可能很容易就可以促成合作。究其原因在于類似的合作可能根本不需要總部大老板作決定,中國區領導就可以作決定。他們吃了別地方的螃蟹,你可以跟他們說你的不一樣,是大閘蟹;你就容易在你不是第一個被吃的螃蟹。他吃了第一個,就有可能想吃第二個。
比如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出版了路甬祥院士主編的《走進殿堂的中國古代科技史》,該書獲得了第三屆中華優秀出版物獎、上海圖書獎一等獎。我一看是好書啊,這版權輸不出去可太遺憾了。我就立刻上網搜,結果搜到新加坡國立大學出版社(NUS Publishing)即將出版一部英文版《韓國科技史》(History of Science in Korea)。韓國科技史在很多方面算是中國科技在韓國的本地化史,結果一封郵件發給新加坡國立大學出版社的社長后,不久就收到了熱情的回復,一樁版權貿易合作就此展開。
對于必須拿下的項目,要有不達目的誓不罷休的氣勢,必要的時候要竭澤而漁,就是凡是跟這個項目有關的外國社,一個一個用最可能、最有效的方式,像發小廣告那樣鍥而不舍地聯系、推介。如果真這樣干起來的話,就算665次都失敗了,但是可能不用再敲第666扇門,因為很可能前面那665家里頭就有一家來吃后悔藥。
二、國外出版社相關職員
1. 版權經理
一定要記住,找外國出版社的版權部、版權經理,談版權輸出有時候是緣木求魚。他們一般只負責賣版權給你,沒有幫你賣版權的義務。即便你先跟他購買過幾本,大家混個臉熟,他答應幫你推薦給他們社的編輯,也大多不過是禮貌地應付你罷了,因為這體現不出他本人的工作業績。也有大家真的關系好的,竭力幫你推薦,竟然做成了一筆兩筆,不過也不要高興太早,這絕對不是可持續的版權輸出方式。
2. 策劃、組稿編輯
我的體會是,要找外國社的策劃、組稿編輯(acquisition editor)。畢竟中國經濟和文化在世界上的影響力還沒有大到足以讓源源不斷的外國編輯找你買版權的程度,因此我們現在在中國做版權輸出的,很大程度上與抱著自己的稿子挨個兒出版社去投稿的作者差不多,我們不過是這些作者的版權代理人罷了。你在中國投稿,也絕對不會找版權部,而是找策劃、組稿編輯。當然,策劃、組稿編輯也有各自專注的領域,你要做的是找到專注你這本書所涉及領域的策劃、組稿編輯。這是一條常規的路。
3. 大老板
找領導就不一樣了。領導一旦拍板,事情就順暢多了。雖然即使領導同意了,有時候也得經歷選題論證(各類、各個出版社不一樣)。但是有時候就算是賠錢他們也會做,因為領導站得高、看得遠。如果按單本書來核算利潤,可能市場部門要哇哇叫了;但是如果這書出了能夠擴大該外國社在中國的品牌影響力,拉動在中國的多品種的銷售(原版書、數據庫),把這書當做公共關系維護或者市場推廣的工具的話,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那就不是論證這書能不能賺錢的問題,而是成了論證這筆錢如何花才最有效的問題了。這可以理解為,閻王好見,小鬼難纏。這也難怪,因為賠錢的權力永遠掌握在領導的手里,策劃、組稿編輯在這方面是沒有發言權的。
4. 中國員工
這里要特別強調一下外國出版社設在中國的分公司、代表處的員工。他們由于長期橫跨兩個國家、兩個話語系統,像是一座橋梁,連接起了國內外的好社、好書、好人。我們跟他們溝通起來,可能會更容易,因為有些背景信息,大家都心知肚明。
與外國出版社具體的工作人員打交道的時候,要充分利用一切可能的方式與之交流。一是參加北京書展、法蘭克福書展等大型國際圖書博覽會,這些書展會聚了各國大量專業人士,能夠在短時間內與最多的合作伙伴見面。也未必計劃好實實在在的事情再去辦,就算和潛在合作伙伴寒暄寒暄,也是有益的。說到底,見了面,才有信任感。否則,一封冒昧的電子郵件,很容易就被人當做垃圾郵件刪除了,可能連被看的機會都得不到。雙方的產品結構、新書,聊聊可能就聊出來生意了。二是探索國際出版交流,可以組一個小型工作代表團,一周走訪十來家出版社,拜訪高層領導,克服書展上見面時間短、環境嘈雜等不利因素,效率更高,成效更大。三是善于利用網絡等新興搜索、聯系方式,如LinkedIn上可以聯系到很多國際出版同仁。
三、輸出國家
英國、美國等英語國家在翻譯出版方面太傲慢自大,一年也別指望賣給他們幾本版權。相比而言,法國、意大利等歐洲國家,中國圖書還是有相當的市場的。過去,一方面由于英語國家影響太大,一想到外國,第一想到是英語國家,另一方面也由于我們的版權工作人員,第一外語為英語的也占了絕大多數,所以我們對向非英語國家輸出版權,開發得相當不夠。這是一個很可努力的方向。另外,先輸出非英語語種版權再轉而輸出英語版權,也是常有的事。
還有就是東南亞國家和地區,這是中國經濟和文化在相當程度上可以影響和覆蓋到的地域。文化往往從經濟發達的地區向經濟落后的地區流動,這也是歷史的必然。
在版權輸出洽談中,要真心實意地為外方合作伙伴著想。針對你們討論中的這本書,在所謂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中,他們追求哪一個?通俗點說就是,他們是想賺錢呢,還是想釣譽?輸出到歐美的專著,很少有能盈利多少的。一些外國出版社之所以還想做,可能是因為介紹中國學者的研究成果,不論如何是對既有產品結構的有益補充;另外多多少少可以促進版權、數據庫和實物圖書等的銷售業務在中國的發展;另外,對于有些大社名社,獲得中國出版行政管理部門和中國讀者的信任和好感,是他們在中國開展業務的重要保障,俗話說是“染紅”了。當然,東南亞等地區的出版社來中國購買英語學習、中小學教輔等圖書的版權,應該是可以獲得相當的利潤的。
綜上所述,只有找準適合國家的對口出版社的能夠作決定的人,才能為我們手中的優秀圖書的版權找到理想的婆家,才能最終敲定一宗版權輸出合同!
(作者單位: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