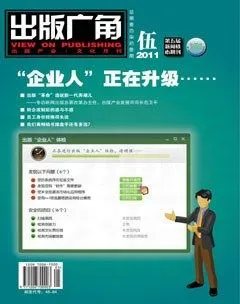在出世與入世之間
《許多風(fēng)景》張蒙 著北岳文藝出版社2011 年3 月版定價(jià):29.80 元
蘇軾是用儒家思想來(lái)做官,用道家思想來(lái)修身養(yǎng)性,用佛家思想來(lái)對(duì)付人生的苦難。張蒙是用軍人品格來(lái)入世,用詩(shī)人性情來(lái)出世,他的人生因此達(dá)到了入乎其中又出乎其外的境界。
有一些人會(huì)去寫詩(shī),我感到特別能理解,甚至覺(jué)得:他們活著,只能去寫詩(shī),比如李白、顧城。有一些人會(huì)去寫詩(shī),我感到特別不能理解,因?yàn)樗麄兊囊磺兴坪醵寂c詩(shī)毫不相干,比如我將要寫到的這個(gè)人,張蒙。這樣的一名軍人,與我概念中的詩(shī)人實(shí)在相去甚遠(yuǎn),我覺(jué)得他應(yīng)該屬于最不可能去寫詩(shī)的那一類人。因此,理解“他為什么會(huì)寫詩(shī)”,就成為我讀他的詩(shī)的原動(dòng)力。如果說(shuō)此前讀他的詩(shī)集《守望寂靜》,我的理解還不十分明晰的話,這次讀他的詩(shī)集《許多風(fēng)景》,則有了更多更深的感悟。
《干事》這首詩(shī),透示著一名干事出身的軍人的精神密碼,是內(nèi)心的偶露崢嶸,驚鴻一瞥,如閃電撕開(kāi)夜幕的一角:“一些顆粒 反復(fù)練習(xí)溶解/在一種叫做單位的液體里/被日夜攪拌/從一個(gè)容器倒進(jìn)另一個(gè)容器/搖勻/博士碩士學(xué)士戰(zhàn)士 混合后/都成為干事。”作為一名軍隊(duì)政工干部,張蒙的工作總是與干事有關(guān),不是在當(dāng)干事,就是在管干事,《干事》這首詩(shī)里面,有他很深的生活體驗(yàn)和內(nèi)心感悟。這種難言的體驗(yàn)和感悟,也許只有借助于詩(shī)歌,才能表達(dá)得最充分最到位而又最含蓄最富有美感。
如果一個(gè)人所從事的工作對(duì)心靈缺少潤(rùn)澤,他最好能在工作之外找到一個(gè)有益的潤(rùn)滑和補(bǔ)償。如果這個(gè)潤(rùn)滑和補(bǔ)償恰好是詩(shī)歌,我認(rèn)為是詩(shī)之幸,人之幸。撇開(kāi)更高的精神意義不談,寫詩(shī)畢竟是環(huán)保、干凈且有助于和諧的事情。詩(shī)歌最初就是從勞動(dòng)人民中產(chǎn)生的,它對(duì)于那些不以寫詩(shī)為業(yè)的普通人的意義,恰恰是詩(shī)歌最大的意義,是回到詩(shī)歌的本源。我想,大多數(shù)寫詩(shī)者是不必執(zhí)著的,用隨遇而安的心態(tài)對(duì)待詩(shī)最好。不想做詩(shī)人,但想做一個(gè)保持性情的人,這是許多人寫詩(shī)的內(nèi)在緣由。朝著詩(shī)的方向努力,但不朝著一個(gè)詩(shī)人的方向努力,讓詩(shī)歌作為堅(jiān)固的精神坐標(biāo)豎立于人生一側(cè),我覺(jué)得這是非常可取的詩(shī)歌態(tài)度。
《海風(fēng)如此親切》這組詩(shī),是張蒙去海南出差的收獲之一。“一綹綹白云擦肩而過(guò)/是老子的拂塵輕輕掠過(guò)”(《撥動(dòng)明亮的天際線》),在天空中,他想象著與老子、莊子、列子一起逍遙游,一起御風(fēng)而行,心中掛滿叮咚作響的喜悅的音符。“海之秀口——海口/飛機(jī)急速降落/我以急遽的抵近/置身于這秀口之前。我心對(duì)我口/我口對(duì)海口/一切 從突突的心跳開(kāi)始”(《海的口》),急遽的抵近,是美的抵近,是詩(shī)意的抵近,是自由之境的抵近。與生活拉開(kāi)一點(diǎn)距離,才可能擁有這樣一個(gè)內(nèi)心的空間,才可能擁有這樣一雙發(fā)現(xiàn)的眼睛。張蒙還是一位詩(shī)國(guó)的圣徒。《昆侖山的身影》這組詩(shī)中充溢著的神圣情感,足以使人低眉斂首,為詩(shī)歌靈魂的肅穆和偉大所震懾。張蒙在昆侖山的一切膜拜,似乎都化成了對(duì)已故詩(shī)人昌耀的膜拜;而他對(duì)于昌耀的一切膜拜,又同時(shí)是對(duì)詩(shī)歌精神的膜拜。“不妨猜想 昆侖山原名叫昌耀山……他/躺著都是一座高峰”(《山神》),“在塔爾寺 昌耀是一炷香/他把自己獻(xiàn)在佛前/燃燒許多純潔的想象……”(《塔爾寺的一炷香》)這一組詩(shī)具有令人傾倒的神圣之美。
張蒙是一位貼著地面行走的理想主義軍人。他對(duì)軍隊(duì)不僅懷有很深的感情,而且有著極強(qiáng)的責(zé)任感。這種責(zé)任感,就是位卑未敢忘憂國(guó),依稀可以見(jiàn)出陸游精神的影子。和平年代,“養(yǎng)兵”遠(yuǎn)遠(yuǎn)大于“用兵”,軍人的理想似乎處于一種無(wú)為狀態(tài)。張蒙在寫刺刀、槍、坦克、榴彈炮和軍車的一組詩(shī)中,替武器們沒(méi)有用武之地而感到著急。張蒙是典型的禮儀之邦走出來(lái)的人,恪守著修身齊家治國(guó)平天下的儒家傳統(tǒng),對(duì)于中國(guó)歷史上那些精忠報(bào)國(guó)的名臣總是給予深切的關(guān)注,如《千年不散的會(huì)議》、《精神與遺體的重量》等。精神具有反射性,一個(gè)人所敬重的精神,可能正是對(duì)這個(gè)人靈魂的最好的說(shuō)明。
《一浪一浪的時(shí)光》這組詩(shī)看似寫河,實(shí)則通過(guò)寫河來(lái)寫歷史。“有些事 就得把水?dāng)嚋?才能辦成……從渾水中取勝/在渾河邊立國(guó)/建立的卻是清朝/此后二百多年 國(guó)是朝政/果然有清有渾//一條河 一個(gè)朝代/一個(gè)渾 一個(gè)清/矛盾地依偎在一起”(《渾河》),清和渾糾結(jié)在一起,透示出歷史的吊詭,又似乎符合歷史的辯證。不唯歷史,現(xiàn)實(shí)又何嘗不是如此呢?欲清先渾,渾中求清,清中有渾,渾中有清,這何嘗不是一個(gè)若隱若現(xiàn)的現(xiàn)實(shí)規(guī)律呢?
蘇軾是用儒家思想來(lái)做官,用道家思想來(lái)修身養(yǎng)性,用佛家思想來(lái)對(duì)付人生的苦難。張蒙是用軍人品格來(lái)入世,用詩(shī)人性情來(lái)出世,他的人生因此達(dá)到了入乎其中又出乎其外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