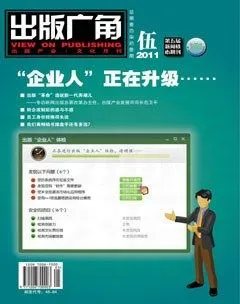《非常識》:無趣中的殉道
《非常識》謝勇 著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2011 年1 月版定價:25.00 元
我以為,一本書,只要是誠實的表達,它的靈魂必然是和作者的經歷和處境相關。一本書最核心的價值可能不在于它告訴了讀者什么有用的信息、深奧的道理,而在于它傳達的作者的困惑、作者基于經驗的思考的印跡。我以為解讀這本書最隱秘的部分離不開作者這樣的經歷和處境:從校園到校園卻不安心于校園,曾經向往學術現在卻在學術體制內承受種種切膚之痛。
其實,無論體制內體制外、媒體人還是學者,他們具體的經驗雖有不同,卻都是中國經驗的一種,那些困擾著大家的問題是一樣的。這類似于作者在《我們都是藝術家》那篇文章里說的核心思想:只要是進入中國現場,我們都得是藝術家,也都成了藝術家。
在《十年之前》這篇文章中,作者回顧了二十出頭時初生學術理想的那個年代,其中有一段這樣的話:“回顧十年前的學術風氣,凸顯文藝的“審美”價值,似乎已經成為“共識”,而所謂“審美價值”,實際上是與某種具體的審美經驗相關,不同的理論家對于“審美經驗”各有理解卻極少明言。理論只在理論的維度上進行,不少學者對于藝術的理解截止于20世紀前半葉,更糟糕的是,對于中國社會現實的認識,更是缺乏常識和第一手體認。”后面這句話,我想作者在很大程度上是說給某個時期的自己“學術理想”的反思和質疑。恰恰是在這種困惑和反思中,作者完成了從理論到現實的轉變,這個經驗是思考的載體也是思考本身,是作者對于現實的“元體驗”。如果說《十年之前》是在進行思路的清理,那么在《學術的金手指》、《學術正業》等文章里,作者則已經開始尋找操作的方法:“……與公眾媒體合作,翻譯作品,撰寫自己認為有價值的文章,放到網絡觀其慢慢流傳,在媒體與學者挑剔的眼光中展示才華獲得認可。這簡直是為中國當下人文學科青年知識分子開拓出另一種生存與致學的道路。只是這條道路,在中國高校和學術研究領域的評價體系中,很難得到承認。”
上面我所理出的這條思路目前的終點就是本書作者現在的行動,當然,這本書的出版本身也屬于這種行動。